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秦朔
要理解今天中國商業的很多深層次復雜問題,有一把鑰匙,那就是讀懂王健林的2017。

回望
時光永在流淌,但有時平緩,有時激昂,有時迂回,有時掀起滔天巨浪。
回望最近30多年的中國商業文明史,我最偏愛的是這樣一些年份:
1984,聯想、萬科誕生,張瑞敏走進了青島電冰箱廠;
1988,平安、華為生于深圳;
1992,關于有限責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的暫行條例出臺,以泰康陳東升為代表的“92派”應運而生;
1999,阿里、攜程誕生,騰訊、新浪、百度都在這年之前或之后的一兩個月內誕生;
2010,移動互聯網萌動,小米、美團出生。
寫下這些名字也是在表達一種商業價值觀——我更偏愛企業家的企業,那些在陽光下看得清清楚楚、主要依靠創新和管理創造價值、高度重視公司治理和可持續發展的現代企業。
企業家不是一種身家(富豪不等于企業家),不是一種身份(某某董事長或總經理),而是一種永遠追求更高的資源配置效率和更好的顧客體驗的精神狀態。企業家是一種精神。
套利的機敏,把握資產升值的眼光,敢于下注的冒險精神,穿梭于官員前后的資源整合能力——這些素質也會在一些特定條件和特定環境中造就火箭般的財富奇跡;但誰能走得長遠?是那些追求永續經營的企業家,那些在創新進取的同時,總是有著對規則和法度的敬畏、對風險的控制、對無所不能的擴張欲望的節制、對團隊、機制和文化都重視的企業家。他們知道自己有“做什么的自由”,也時刻不忘自己還有“不做什么的約束”。
這些企業家,有的在富豪榜上,有的和富豪榜沒有關系。但他們創造的企業,卻構成了中國現代公司中最閃亮的那些名字。
在新鮮出爐的2017年財富500強中,平安、華為、萬科、騰訊都來自深圳。按照凈資產收益率排名,115家中國公司中排位最高的是華為、美的、騰訊、吉利和萬科,深圳占了3家。
我在2006年所寫的《20世紀看外商,21世紀看華商》一文中預言,深圳企業將在未來的全球商業競爭中占有一席之地。當時的判斷是:“以20年為一個尺度,以公司競爭力為評價標準的話,深圳群落才更是我們環視中國后最應該關注的。……它們基本上都是公眾公司,財富不集于個人或家族,也不是產權不明晰的傳統國企;它們的文化背景是移民文化,是開放文化;它們毗鄰海外,喜歡和全球標準相對照,有很強的學習能力;它們有優秀的企業家才能,同時兼具良好的團隊和公司文化;它們生于深圳,但是疆域在全國乃至全球;它們的創始人對于技術的樂趣和事業的熱愛,勝過對個人財富積累的欲望;它們大都堅持專業化的戰略,不斷提高管理能力、創新能力和企業核心競爭力。……在深圳群落中,傳統華商身上一些不良的基因——財富最大化、思維貿易化、在商不言商、人治化與短期化行為流行——得到了相當程度的清除,而誠信踏實、在商言商、價值創新的新基因則深深扎根。這些新的基因,包含著中國企業在21世紀成為世界級企業的希望。”
11年前深圳還沒有一家世界500強,但我堅信深圳這批現代企業代表著中國企業的前進方向。以30年為一個尺度——萬科33年,平安和華為明年30年,事實是最好的說明,那些堅持商業文明道路的企業總是能夠不辜負社會期待,令人放心和尊重。
四個公司四種局
現在來說說2017年,它會以獨特的內涵載入中國商業史冊。
這一年,阿里和騰訊的市值或許會沖擊4000億美元,它們都已成為世界十大市值的公司。
這一年,中國商界更關心的是——萬科大結局,萬達大變局,樂視大困局,安邦大險局!多少個頭條啊!
萬科大結局
長達兩年的萬科股權和控制權之爭結束,6月30日,新一屆董事會產生,11名董事中的7名非獨立董事,深圳地鐵和萬科管理層各占3名,形成主導。王石告別董事會,郁亮接棒。王石最后說,我給萬科選擇了一個行業,房地產;確定了一個制度,就是規范,就是透明,就是依靠團隊;我說過我成功的時候就是萬科不再需要王石的時候,我很欣慰,萬科真正穩定的黃金發展期才開始。
萬達大變局
7月19日,萬達商業、融創集團、富力地產簽訂戰略合作協議,萬達將77個酒店轉讓給富力,將13個文旅項目轉讓給融創。在637.5億的資產大出讓之后,王健林表態,要積極響應國家號召,把主要投資放在國內。他說,企業發展總要順勢而為,去杠桿、降負債不僅是國家政策,企業尤其是大企業更應該積極行動起來。
安邦大險局
6月13日,安邦集團公告稱,集團董事長兼總經理吳小暉先生因個人原因暫不能履職,已授權集團相關高管代為履行職務。僅僅一年前,主要依靠萬能險的狂飆突進,安邦人壽的總保費規模甚至超越平安人壽,位居壽險行業第二。短短一年后,安邦的原保險合同保費收入,從1月的852.58億元狂跌至5600多萬元。
樂視大困局
樂視體系的財務危機和信用危機不斷深化,賈躍亭辭去樂視網一切職務。7月21日,在以電話會議形式召開的樂視網董事會上,孫宏斌當選為樂視網董事長。樂視網發布的上半年度業績預告,預虧約6.4億元,而去年同期還盈利2.84億元,2010年上市后更一直給市場“畫”出一條近乎美妙的持續增長曲線。無論未來如何給這家“網紅型公司”定性,樂視危機已經給“顛覆”、“夢想”、“生態”這些詞語蒙上了陰影,新的創業者再這么講PPT,收獲的更多是質疑。用概念創造高估值,這個時代結束了。
每個企業都會遇到挑戰,但性質并不相同。今天,萬科的挑戰是,如何在保持過去優勢和無形資產的基礎上做得更好;萬達的挑戰是,如何盡快與一部分的過去進行切割,然后重新出發;樂視的挑戰是,瘋狂編織的夢想無人埋單后,還能不能重建信用;安邦的挑戰是,不知道公司創始人何時能再次站在自由的藍天下。
請商學院研究一下2017年夏天的這四個案例吧。為什么萬科管理層的聲音政府愿意知道?為什么萬達廉價處置資產的心痛只有自己知道?為什么安邦的神秘無人知道?為什么賈躍亭因屢屢失信已讓人不想再知道?
有的企業,像平安、華為、萬科,企業家為了企業而存在;有的企業,富豪型的企業,企業為了富豪而存在;有人覺得,只要有夢想企業就應該存在;有人認為,某些政策就應該因我的特殊背景而存在。
有什么因,結什么果。是什么因,現什么形。
萬達變局解析
接下來,重點說一下曾雄踞中國首富榜多年的王健林。
在人們心目中,從1989年下海經商起,28年間王健林主要在買,在全國乃至全球買土地等資產,或開發銷售,或持有運營,或作為長期投資。有失敗的,但總體是大贏家。這一次他是大賣家,賣的規模如此之大,速度如此之快,談判如此快刀斬亂麻,給人一種不得不做、又堅決要做的印象。
不得不做,似乎是短期的急迫壓力所致。堅決要做,則是長期戰略選擇使然。
先說短期壓力。最近一周搜索公開報道,壓力從三個地方浮現出來:
一是,監管部門突然要求對萬達境外投資所涉及的并購貸款、內保外貸等業務進行核查分析,嚴控一些境外投資項目的融資。(注:內保外貸是指境內銀行為境內企業在境外注冊的附屬企業或參股投資企業提供擔保,由境外銀行給境外投資企業發放相應貸款)
二是,萬達商業私有化時募資的對賭壓力。萬達商業2014年12月在香港上市,因估值低和融資能力受限,2016年9月退市,退市總代價為345億港元左右,由9家機構完成。根據協議,如果退市滿2年或2018年8月31日前未能實現在境內主板市場上市的目標,萬達集團以每年12%的單利向A類(境外)投資人回購全部股權,以每年10%的單利向B類(境內)投資人回購全部股權。目前看,預期的目標要實現存在壓力,那就意味著要支付一大筆資金回購萬達商業股權。
三是,馬來西亞大馬城項目的復雜性。大馬城原址是吉隆坡市中心一座占地200萬平方米、閑置了20年的空軍機場,2015年全球競標,要建設總建筑面積約840萬平方米的吉隆坡交通樞紐和國際經濟中心。中國中鐵股份有限公司和馬來西亞依海控股集團組成的聯營體中標。但2017年5月3日,馬來西亞財政部下屬企業發表聲明,稱聯營體未能滿足2015年所達成協議項下的標準,大馬城的股權銷售協議失效。按原協議,聯營體占大馬城權益的60%。該聲明還稱,馬來西亞財政部現將保留所涉地塊的所有權,并開始尋找其他有意向的潛在開發商。而中馬聯營體隨后發布的公告則表示,馬方公司單方面的宣布違反了雙方協議條件,他們對此保留一切權利,并稱聯營體公司擁有足夠的資金和能力確保大馬城發展順利。
5月9日,媒體傳出消息,萬達集團正與馬來西亞當局洽談開發大馬城,馬來西亞總理納吉布希望在5月14-15日訪問北京出席“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期間與萬達完成簽約。但到了6月23日,馬來西亞財政部再次公開招標“馬來西亞城發展計劃”(即大馬城),聲明說,參與投標的公司或聯營企業必須符合財政部三項標準——《財富》世界500強公司、過去三年在房地產和相關業務累積的生產收入不少于500億林吉特(1林吉特相當于1.58人民幣元),以及擁有開發國際房地產項目的經驗。
大馬城重新招標,而不是和萬達簽約,說明雙方合作已經擱淺。王健林的最新表態“把主要投資放在國內”,也意味著他不會再投資此類大項目。萬達為何介入又退出,和中鐵之間是何關系(中鐵也是萬達商業私有化的9家機構之一),不得而知。至于中鐵參加的聯營體能否重啟大馬城,既取決于中鐵的意愿,也取決于政府的態度。
如所周知,萬達最近出讓資產是為救急。急從何來?我認為,“急病”是過去數年很多因素疊加、積累到一定程度突然爆發的。這些因素既包括萬達在境外投資擴張力度太猛、指標性太強、杠桿較高,也包括“中國首富”不斷上頭條的效應,最后,很可能是圍繞大馬城的博弈,成了形勢急轉直下的導火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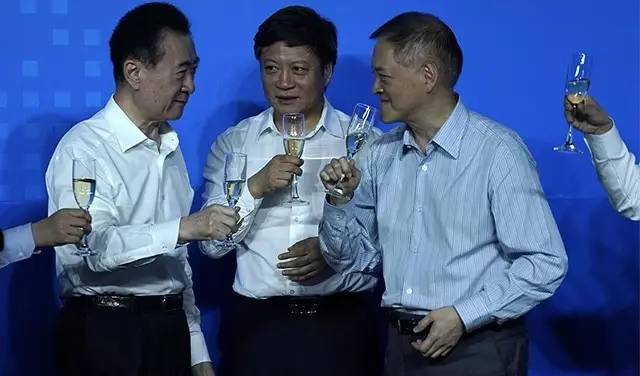
要理解今天中國商業的很多深層次復雜問題,有一把鑰匙,那就是讀懂王健林的2017。
大環境變了
從我遠遠的觀察看,雖然遭遇了強往肚里吞的巨大壓力,但這種短期的陣發性的壓力,反而加快、加強了王健林更徹底地推進長期戰略轉型的堅定性。
斬倉,切換,快轉,軍人出身的他沒有一點拖泥帶水。他一定看到了某些大趨勢的深刻變化,才義無反顧。
這種大趨勢是什么呢?就是從新常態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國經濟要從粗放向集約、從簡單分工向復雜分工演進。
粗放增長和簡單的外延擴張是中國經濟的老問題,1995年中央就強調“實現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增長到集約增長”,20年后,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了“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五大發展理念。最近的中央金融工作會議強調,加快轉變金融發展方式。
在中國,過去對增長最有效也最粗放的拉動模式就是投資,圈地,大興土木。我們三年可以用掉美國一百年所用的水泥,中國開發商兩周能建起一座羅馬城的面積。而土地作為基礎資產,在地方政府的眷顧下,價格一直處于主升浪,也讓開發商形成了對外延擴張的強烈依賴。
大規模儲備土地,項目開發利潤和土地重估利潤兩頭吃,這是中國房地產的基本商業模式。在這個大結構中,的確是“清華北大,不如膽子大”,尤其是有銀行壯膽之后。沒有銀行支持,房地產首富們造就不了。
但當中國人均住房面積已高于大部分歐洲國家(2016年全國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積為40.8平方米);當高房價引發的社會和經濟矛盾越來越深、房地產的資產繁榮和實體經濟的艱苦形成了鮮明對比;當房地產相關行業貸款占全部貸款比例的1/3以上、發行的信用債存量占非金融信用債總量的近1/2、龐大的“影子銀行”體系也存在大量房地產相關融資的時候,“中國經濟的房地產化”必須結束,“漲漲漲、買買買、貸貸貸、炒炒炒”的上半場必須結束。在下半場,從國家層面,會考慮通過長效機制,通過租售并舉等多個層次化解中低收入者和年輕人的居住難題,提供更多“可支付住宅”,并力除房地產的投機屬性。從開發商角度,在行業集中度大大提高的同時,則要想方設法進行結構調整。
去泡沫、去杠桿,釋放一些小風險,防止其繼續累積,聚成無法承受的大風險,這是時之所至,勢所必然。
最近和一位國際投資家交流,他說中國的投資讓他有三個看不懂:
第一個,是看不懂中國的銀行為什么要給中國企業在海外的投資項目放那么高的杠桿?國外銀行一般按企業稅息折舊及攤銷前利潤(EBITDA)的3到4倍發放貸款,中國的銀行可以給到6到7倍乃至更高。這意味著海外并購的企業要有非常高的利潤成長性,而在成熟市場這很難做到。“中國的銀行在改變游戲規則,完全看不懂。”
第二個,是看不懂中國的資本市場為什么對一些明顯存在業績美化傾向的公司給那么高的估值?樂視為例,“樂視剛上市的時候,一個視頻網站有幾千萬利潤,已經很讓人吃驚,但由于有運營商支持,故事還能基本成立。后來用那么多的關聯交易支持利潤扶搖直上,只要有學過財務知識的人都應該會質疑。為什么中國的監管部門看不出來?”
第三個,是看不懂中國的地方政府,對一些在債券市場上明明還不了錢的企業,為什么一定要幫助它們進行“剛性兌付”,從而拖累更多企業和政府信用進來,讓問題越滾越大?
這些問題不應該解決嗎?這些繁榮能持續嗎?
泡沫化的資產估值體系,頭腦發熱的企業,推波助瀾的銀行,脫實向虛的大資管的支持,這一切造就了許多地基不穩的“傳奇”,如火箭般騰飛,好像都要飛出地心引力了,結果仿佛一夜之間,重歸大地。監管從嚴了,空轉套利很難了,帶病上市要嚴防了,民營金融機構要完善法人治理了,風險內控機制要加強了,等等等等。

這個炎熱的7月,對不少企業是嚴冬。如果習慣了高杠桿支持下的野蠻粗放生長,那么可能今后永遠都是冬天。
企業要變,從做大優先到做強優先,從做快優先到做穩優先,而更重要的,是進行結構性的變遷。
結構性變遷
以萬科和萬達為例,來看看結構性變遷的含義是什么。
萬科在從住宅開發商向城市配套服務提供商轉型,從相對單一的快速開發周轉模式,向增加自持比例、豐富物業類型(如商業、物流、軌道、養老)、通過存量改造實現長線升值(如廣州花地灣)等方向變遷。萬科在朝更重的方向走。
萬達希望向更輕的方向走,選擇“去地產化”,向服務業、輕資產、新興行業方向轉型。
王健林在2016年度工作報告中說,萬達從地產開發退出不是對中國房地產看空,主要在于房地產開發的周期性太強,基本上三年左右來一回調控,造成現金流不穩定,預期也容易經常發生變化。而萬達已經可以靠品牌掙錢了,過去靠賣住宅、商鋪的錢來建萬達廣場,現在別人拿錢下訂單,我們負責找地、建設、招商和運營,或者對方出地又出錢,萬達負責設計、建設指導、招商運營,凈租金雙方7比3分成。不出錢,靠設計運營就能分很大一杯羹,何樂而不為?他說萬達商業要用實際行動來證明,不當地產商,這個公司更值錢,“在資本市場上,地產的PE(注:市盈率)是10倍左右,商業租金的PE是30甚至40倍。”
萬科和萬達,一個更重,一個更輕;一個更注重大類資產的綜合配置,一個更在乎凈利潤結構中的租金占比;一個要掙更持久的錢,一個要掙更值錢的錢。郁亮用資本工具頻頻出擊,他押注的是中國在高速城市化后還有一輪“深度城市化”,他背后是資源強大的深圳地鐵集團。王健林押注的是中國的消費及其升級,房價漲跌不是他太關心的事,他相信萬達廣場所代表的城市消費、服務消費會穩中有升,而品牌化的萬達商業管理、萬達院線、影視和體育,就在風口之上。
在整個政策環境、金融環境、產業環境發生深刻變化的時候,考驗一個企業的素質,其關鍵已經不是如何通過管理創新來提升效率,尋求邊際改善,而是能不能洞察結構性變遷的大趨勢,推動結構變革,并與自身的資源稟賦和能力相匹配。
談到中國的房地產龍頭,不少人關心未來幾年誰是“王者”?萬科,恒大,碧桂園,綠地,保利還是融創?這都是以外延式擴張為特征的上半場思維。下半場的新思維框架可能是,如何在給定的資源和資產條件下,創造出可持續性的價值。規模擴張當然還是一個主旋律,但價值創新將越來越重要。
只是真的要告別過去的路徑依賴,并不容易,特別是要放棄掙快錢、掙easy money的路徑依賴。
大變遷需要更理性的氛圍
大變遷也是大洗牌,注定有痛苦、矛盾和淘汰。從政府到社會,在落實去杠桿、去泡沫、防風險總體戰略部署的同時,也需要以更加淡定和理性的態度看待問題,處理問題。過去我們在推動某些戰略的時候,在具體實施時,往往不夠平衡。今天同樣要避免用力過度、過猶不及。
以最近頗受爭議的對外投資為例,研究近年來出臺的文件會發現一個問題,當初推動對外投資蒸蒸日上的時候,對本應提醒、平衡的方面,有一定忽略。中央高層曾說,“我國對外開放從早期引進來為主轉為大進大出新格局,但與之相應的法律、咨詢、金融、人才、風險管控、安全保障等都難以滿足現實需要,支撐高水平開放和大規模走出去。”這是非常準確的判斷,條件不完備,盲目地、一窩蜂地走出去,必定教訓累累。

2012年,13個政府部門聯合發出《關于鼓勵和引導民營企業積極開展境外投資的實施意見》,提出“當前我國正處于民營企業境外投資加快發展的重要階段”,“充分發揮民營企業在境外投資中的重要作用”。文件中有“做好境外投資的投向引導”一段,提到了一些引導方向,如境外能源資源開發、境外高新技術和先進制造業、境外基礎設施、農業和服務業投資合作,等等。但缺乏限制性行業的規定。服務業投資具體指什么?文化、體育、俱樂部算不算?不清楚。
2014年發布的《境外投資項目核準和備案管理辦法》,對境外投資項目基本上實行備案管理,只是“中方投資額10億美元及以上的境外投資項目”,“涉及敏感國家和地區、敏感行業的境外投資項目不分限額”,由國家發改委核準。這里的敏感行業包括:基礎電信運營,跨境水資源開發利用,大規模土地開發,輸電干線、電網,新聞傳媒等行業。體育、俱樂部、影視等屬不屬于核準范圍,規定中也看不出來。
鼓勵企業走出去投資,這符合中國的利益,但過快、過猛、虛火過旺,利用中外市場的估值不同進行套利,就把正道走偏走歪了。日本在1990年前后對美國大舉投資就交了慘痛的學費,那還是在日元升值的背景下。
同時,對外投資和任何投資一樣,本身就存在風險。國家審計署近日稱,通過審計中國石油、中化集團、中船集團等20戶中央企業發現,部分企業投資經營風險管控比較薄弱,具體抽查155項境外業務發現,因投資決策和管理制度不完善、調研論證不充分、風險應對不到位等,有61項形成風險384.91億元人民幣。可見,對外投資中的風險防控,是帶有普遍性的問題。
但是,我們也不能因為對外投資中的問題,就貶損“走出去”的意義,甚至妖魔化“走出去”。中國追求資金流入和流出的總體平衡,不是進來的越多越好,出去的越少越好。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六次會議指出,加快對外開放步伐,加快建設開放型經濟新體制,這主要是針對外商投資來說的,但新常態下“高水平引進來,大規模走出去”的戰略方針并沒有改變,中國對外投資的大趨勢也沒有改變。
目前對外投資中的一些“非理性”,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不宜先扣帽子。比如,在國外購買一些“軟實力”資產,這種探索本身是有意義的,美國商品行銷全世界,附加值很高,一個原因是靠好萊塢、NBA等軟實力的“支援”,美國的文化娛樂產業、體育產業在全球放大了美國產品的影響力。“軟實力”在國際競爭中是很重要的。但是,爭購國外的內容制作公司和體育俱樂部,問題往往很大,因為文體內容的競爭很激烈,變幻莫測,投資者也會遭遇很多內容防火墻,無法影響內容的走向,這方面就不如版權合作和項目合作來的穩妥。而有些文體產業公司是渠道型和平臺型的,比如院線或重要賽事的運營商,這些投資會更有價值,因為會對產業有更多掌控力,院線一旦形成,重要賽事一旦成熟,就有很高壁壘,難以被替代。
中國經濟和對外投資出現一些問題不可怕,只要能及時糾正。問題導向往往是進步的動力。釋放更多善意,在分析問題的時候更加理性、全面和客觀,這對整個中國的結構性改革只有好處沒有壞處。現在有一部分輿論充滿極化的猜測,充斥著“逃跑”、“轉移”、“騙局”之聲,這樣的假想和似是而非的邏輯,往往把沒有那么復雜的問題搞的更復雜,更不可測。舉例來說,商業主體間往往是相互依存的,銀行防風險是對的,但要是企業搶著還你的錢、和你越走越遠,對銀行真是利好嗎?

每個人有更多理性,在狂熱時勇于反思,在低迷時力求客觀,中國經濟就會有更多理性。對話永遠好過對立。平等的溝通機制和法治化的途徑永遠是解決問題的正途。當我們釋放出更多善意,中國經濟就能更接近善經濟。這不是放松警惕,而是對大時代負責,對中國經濟的未來負責,對彼此負責。
人工智能讓我們明白深度學習的重要性。希望我們在看待、理解和處理中國經濟與中國公司的問題時,也能不斷提高深度學習的能力。也許,我們在很多方面都需要一場深度學習的革命,而不是一出現問題,就回到簡單化的、非此即彼、帽子橫飛的話語框架里。
商業文明的車輪永遠向前。有的公司堅守初心,慎終如始,因而卓越;有的公司勇于自省,因而超越;有的公司迷途知返,因而重生;有的公司執迷不悟,因而毀滅。而萬千企業家、創業者、經理人、投資者,將從這樣的活生生的現實觀察中,思考自己的命運,改善學習的曲線,不斷向前,不斷出發。
(本文作者介紹:商業文明聯盟創始人、秦朔朋友圈發起人、原《第一財經日報》總編輯。)
責任編輯:賈韻航 SF174
歡迎關注官方微信“意見領袖”,閱讀更多精彩文章。點擊微信界面右上角的+號,選擇“添加朋友”,輸入意見領袖的微信號“kopleader”即可,也可以掃描下方二維碼添加關注。意見領袖將為您提供財經專業領域的專業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