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馮明
儲蓄過剩和投資需求相對不足、社會財富規模龐大和財富所能附著的媒介投資品相對不足成為中國金融行業面臨的基本矛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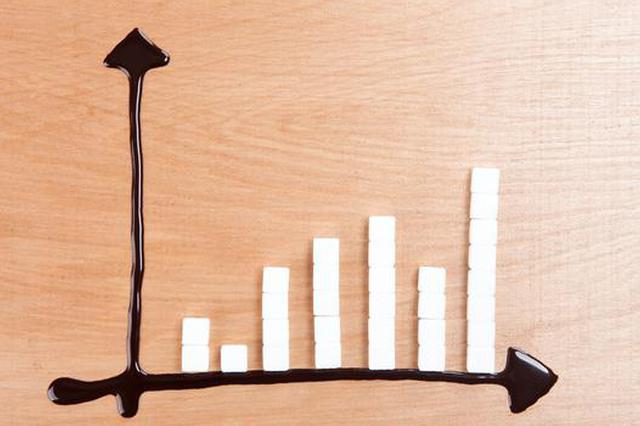 馮明:如何管理大規模的社會財富
馮明:如何管理大規模的社會財富中國金融行業面臨的基本矛盾正在發生重大變化:過去,中國曾經長期是一個儲蓄不足的經濟體,但是經過改革開放之后數十年的發展,目前中國已經變成一個儲蓄相對過剩的經濟體。儲蓄過剩和投資需求相對不足、社會財富規模龐大和財富所能附著的媒介投資品相對不足成為中國金融行業面臨的基本矛盾。特別是“四萬億”之后,這種格局性變化更為凸顯。
金融是連接儲蓄決策和投資決策之間的橋梁。基本矛盾的演變導致實體經濟對金融業的需求也在發生轉型。原有的金融服務供給與新經濟環境、新經濟結構之間出現了一定程度的錯位。中國金融業正在面臨一個前所未有的挑戰——如何管理和分配如此巨大規模的社會儲蓄和社會財富。這既是中國金融業的挑戰,也是中國經濟的挑戰。該挑戰既是歷史性的,也是世界性的。
金融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在2015年和2016年高達8.35%和8.5%,超過美國、日本等通常意義上金融業先進的發達國家。有人據此認為中國的金融業發展過度了,提出應當抑制金融發展。但實際上,8.5%的高占比只是金融業“虛火”旺盛的表現。中國金融業不是發展過度了,而是發展不足、發展不良。“大而不強”這一曾經對中國制造業的批評同樣適用于今天的金融業。當前真正應當擔心的問題不是金融業占比過高、金融業過度發展,而是金融能力不足。中國應當大力加強金融能力建設,將其作為現代國家能力建設的一部分。只有加強供給側的金融業能力建設,才能使得金融業適應于新經濟環境和新經濟結構,才能讓金融更好地服務于實體經濟,從根本上解決資金脫實向虛的問題。
(一)中國金融業面臨的基本矛盾在發生變化
從增量層面來看,我國國民經濟核算意義下的儲蓄率曾經一度超過50%,現在仍在47%以上,高于世界上絕大部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年儲蓄規模在35萬億元人民幣以上。這些儲蓄無非流向兩個用途:一是凈出口,也可以理解為對外儲蓄。但是中國目前占全球出口總額的比例已經高達14%,未來繼續進一步增長的空間有限。二是國內投資,而國內很多傳統行業面臨著產能過剩的問題,投資需求也有限。這是基本矛盾在增量層面的體現,簡言之,可以概括為儲蓄過剩和投資需求相對不足的矛盾。
從存量層面來看,截止2016年底,全國儲蓄存款余額高到59.8萬億元,銀行理財產品余額將近30萬億元。根據招行與貝恩公司聯合發布的《2017中國私人財富報告》,2016年中國個人持有的可投資資產總量達到165萬億元之巨,是當年GDP的兩倍多。另有測算顯示房地產市值更是高達約300萬億元,約為當年GDP的四倍。如此巨大規模的社會財富都要找到相對應、可附著的媒介資產;但是,我們的金融體系中缺乏足夠的媒介資產可供這些財富去附著。所以在過去幾年中可以看到一些非常有意思的現象,大量的資金苦于找不到投資機會、找不到可附著的媒介投資品,追著投資機會和產品“東奔西跑”,除了造成房價快速攀升、股票債券價格大牛大熊之外,大蒜、生姜、糖等傳統意義上的消費品也被當成投資品去“炒”。這是基本矛盾在存量層面的表現,簡言之,可以概括為巨大財富規模與財富所能附著的媒介投資品不足的矛盾。
(二)實體經濟對金融的需求結構在轉型
在微觀層面,金融的本質是風險條件下的資源跨時空配置。在宏觀經濟學意義下,金融的本質是連接儲蓄和投資的橋梁。在儲蓄和投資決策不分家的時代是不需要金融的。比如在小農經濟自己自足的情況下,一個家庭的儲蓄決策同時也就是他的投資決策——今年打了1000斤糧食,當年吃掉950斤,留下50斤種到地里明年吃,那50斤既是這個家庭的儲蓄,也是他的投資。但進入現代經濟之后,儲蓄決策和投資決策越來越分離,所以對金融需求也越來越大。
儲蓄決策的本質是居民對消費進行跨期平滑。所有的儲蓄都一定要附著在某種媒介之上,以便未來能兌現為消費。被附著的媒介可能是紙幣、存款、股票、債券,也可能是房產、黃金、白銀、煤炭,抑或是比特幣、大蒜、紅酒、字畫等等。問題在于,當儲蓄規模過大時,經濟中就會缺乏足夠多的媒介可供附著。盡管理論上貨幣和存款可以無限增加,但是,貨幣過多會導致通貨膨脹,存款過多了銀行不一定能找到相應的優質貸款投向,房子建多了房價可能會跌,“蒜你狠”曾經一地雞毛,紅酒字畫等另類投資品畢竟規模有限,金銀等貴金屬的價值在現代經濟中越來越受到挑戰……
在宏觀經濟學意義下,投資是企業和家庭增加生產性資本存量的過程。例如企業擴建廠房、更新機器設備,目的是生產更多或者更新的產品。再比如家庭購買房產,因為房子在未來可以“產出”住房服務。投資行為取決于邊際資本產出、需求、以及資本折舊率等因素。需要澄清的是,人們在日常生活中說的“投資股票”或“投資理財產品”在宏觀經濟學意義下實際上是儲蓄行為,而非投資行為。
既然金融是連接儲蓄決策和投資決策之間的橋梁,那么金融業務可以自然而然地分為兩類:一類是服務于儲蓄行為的金融業務,一類是服務于投資行為的金融業務。
在計劃經濟年代和改革開放初期,面臨儲蓄不足、投資需求旺盛的基本矛盾,中國經濟對金融的核心需求是:最大限度地動員社會儲蓄、集中社會資源,然后利用這些儲蓄資源去搞建設。而當前,在基本矛盾轉化為儲蓄過剩、投資需求相對不足的時候,中國經濟對金融行業的需求則更多轉向如何管理巨量社會財富,如何高效地配置儲蓄資源,轉化為實體經濟中的投資。以前是項目等錢,資金來源是制約,為項目融資是金融業的關鍵著力之處;現在是錢追著項目跑,優質項目和投資機會是制約,理財成為邊際激增的金融需求。
換言之,中國金融業正在面臨一個前所未有的挑戰——如何管理和分配如此巨大規模的社會儲蓄和社會財富。這既是中國金融業的挑戰,也是中國經濟的挑戰。不論橫向來看,還是縱向來看,該挑戰都是艱巨的。縱向來比,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中國經濟中都沒有如此大規模的儲蓄和社會財富需要被管理過;橫向來比,我國現在的儲蓄規模也明顯大于其他國家。所以說,這個挑戰既是歷史性的,也是世界性的。
(三)中國金融業發展不足,而非發展過度
2017年3月中旬以來,一行三會監管新政密集出臺。中國人民銀行將表外理財納入廣義信貸增速考核。銀監會連發7份文件,部署針對商業銀行“三違反”、“三套利”、“四不當”的全行業大檢查。證監會收緊基金子公司設立門檻,提出資管業務的“八條底線”,完善保本基金風控指標和監管要求。保監會發文要求各保險公司清理規范通道類業務,防范監管套利,嚴格保險資金運用,并對組合類保險資產管理產品提出八大禁止情形。
金融監管風暴成為今年二季度中國經濟和金融市場的一大主題詞。與此同時,金融監管引發廣譜利率上行,短期內對金融市場帶來緊縮效應,也導致實體企業融資成本出現了一定程度的抬升。一時間,對金融行業的批評聲音不絕于耳,如金融空轉、資金脫實向虛、金融支持實體經濟的效率等。
毋庸諱言,這些批評并非空穴來風,存在一定的現象作為基礎。但是,面對這些批評,我們首先需要思考:這些問題真的是金融創新和金融業發展過度造成的嗎?還是金融背后或者金融之外的其他原因造成的?
不妨試想,如果沒有2011年之后私募、理財、信托等影子銀行體系的興起,中國經濟的儲蓄-投資傳導機制會更順暢嗎?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效率會更高嗎?如果今天商業銀行貸款仍像過去一樣占到社會融資規模的80%以上,那樣的金融體系能夠適應2013年之后宏觀經濟“三期疊加”的新常態嗎?能夠服務于新經濟動能的成長嗎?答案顯而易見是否定的。如果沒有金融創新,恐怕只會造成更嚴重的資源錯配,導致更多的儲蓄資源被浪費。
打個不盡恰當的比方。一個人每天吃過多的食物、又不運動,但并沒有轉化為肌肉、身高也沒有長得更高,而是脂肪不斷堆積、虛胖。看到這種現象,我們當然批評新陳代謝系統,職責它為什么不把食物轉化為身高和肌肉,而是堆積成了脂肪、積聚高血壓風險。但是這種批評意義不大,因為根本原因在于入口上吃得過多、而出口上不運動需求不足。事實上,他的新陳代謝系統比一般人負荷更大,更努力工作。就像中國的金融業一樣。
當中國經濟在進行劇烈結構轉型的時候,實體經濟結構在發生變化,相應地對金融服務的需求結構也提出了更多的挑戰。拋開這一歷史背景來批判金融業并不合理,容易造成舍本逐末的錯位,甚至在政策制定上樹錯靶子。
金融創新過程中滋生了不少問題,比如通過加杠桿和期限錯配積聚金融風險等。但金融永遠是跟不確定性和風險相伴而生的,沒有不確定性和風險,就沒有金融。真正應該擔心的不是金融風險,而是金融業缺乏對風險定價的能力。
況且,沒有金融創新,結果會更好嗎?如何有效管理和配置海量社會儲蓄和財富、將其轉化為實體經濟投資,這是上述諸多批評的根源所在,但這一問題并非金融業造成的。恰恰相反,金融創新的過程整體上就是應對這一挑戰的過程。如果沒有金融創新,風險并不見得會下降,因為儲蓄-投資轉化效率只會更低。我們不應當把金融發展不足的結果當成是批評金融業、限制金融發展的理由。
2015年,金融業增加值在GDP中的占比已經高達8.5%,2016年為8.35%;比美國、日本等通常意義上金融業先進的發達國家還要高。這一數字觸動了很多人的神經。有人據此認為中國的金融業發展過度了,提出應當抑制金融發展。
但事實恰恰相反。中國金融業不是發展過度,而是發展不足、發展不良。8.5%的高占比只是“虛火”旺盛的表現。“大而不強”這一曾經對中國制造業的批評同樣適用于今天的金融業。當前真正應當擔心的問題不是金融業占比過高、金融業過度發展,而是金融能力不足。中國應當大力加強金融能力建設,將其作為現代國家能力建設的一部分。
(四)加強金融能力建設,適應新經濟環境和新經濟結構
基本矛盾的變化導致中國經濟對金融業的需求結構在發生轉型,原有的金融服務供給與新經濟環境、新經濟結構之間出現了一定程度的錯位。這意味著,金融業必須進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加強適用于新經濟環境和新經濟結構的金融能力建設,才能更好地服務于實體經濟,從根本上解決資金脫實向虛的問題。
關于供給過剩時代亟需加強的金融能力建設,下面舉三個例子。
(1)加強新經濟資本化的能力
一個經濟體中最優質的、成規模的投資品,往往來自于其新興行業。比如說90年代中期房改之后的房地產,以及房地產企業、家電企業的股票;再比如2003年之后互聯網行業和2012年之后的移動互聯網行業。對于前者,房地產的確成為了中國經濟過去二十年里最重要的投資品之一和規模最大的財富附著物;但需要說明的是房子天然具有投資品屬性,其資本化過程對金融服務的需求很低。
而對于后者,盡管互聯網革命如巨浪襲來,帶來生產和生活的根本性變革,中國也幸運地走在互聯網革命浪潮的前列,誕生了很多優質的企業。但遺憾的是,由于中國金融基礎設施的欠缺和金融能力的不足,大量的優質互聯網企業的資本化并非是在中國本土完成的。以中國互聯網行業的“BATJ”四巨頭(百度、阿里巴巴、騰訊、京東)為例,無一例外,都不是在中國本土上市的。其中,騰訊在香港聯交所上市,阿里巴巴、百度和京東分別在美國紐約證券交易所和納斯達克市場上市。以“BATJ”為代表的互聯網企業是中國經濟新動能的代表,也是中國經濟最優質的資產,但卻“肥水流到外人田”,大部分國內居民無緣投資。
雖然理論上資本賬戶開放可以作為金融能力的替代——只要資本賬戶開放,國內居民就可以通過資金跨境流動的形式投資于海外上市的優質中國資產。但對于中國這樣已經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國家而言,寄希望于通過開放資本項目來替代金融能力建設很可能是舍本求末、得不償失。況且,在國內金融市場尚不健全、金融能力不夠發達的情況下,過快開放資本賬戶還容易導致投機資本跨境流動過于頻繁、匯率和資產價格大幅波動、甚至引發金融危機等負面沖擊。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學術界和政策界對于1980年代以來主流的倡導資本賬戶開放的思想提出的深刻反思,目前尚未有定論。
(2)加強國債市場等金融基礎設施建設,重塑宏觀調控能力
在投資需求旺盛、資本相對稀缺的過去,中國政府對經濟進行宏觀調控的能力是較強的。主要依賴于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土地政策等一系列需求側管理工具。但在當前資本相對過剩、投資需求不足的情況下,原有需求側管理工具的有效性受到影響,需要同時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宏觀審慎管理加以配合。另外,在儲蓄和資本相對過剩的情況下,資產價格的波動性會增加,更容易出現暴漲暴跌的情形,更容易發生金融風險。這也對金融市場的風險定價能力和中央銀行監測、管控系統性金融風險的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國債市場是一個國家最基礎的金融市場,是金融基礎設施的核心組成部分之一。而我國目前的國債市場規模還比較小,產品結構不夠全,流動性有待加強,銀行間市場和交易所市場分割。國債市場的這些不足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其他層級金融產品的定價能力,并制約著中央銀行貨幣政策操作和宏觀調控的能力。
主要發達國家中央銀行的基礎貨幣投放大都是以基于國家信用為主導的。美國國債占美聯儲總資產的比例在次貸危機前為85%,盡管次貸危機爆發之后由于三輪量化寬松(QE)期間購買了大量MBS資產有所下降,但是美聯儲總資產始終仍是以國債為主的“內部信用”為主的,“外部信用”所占比例不超過3%。相比之下,中國國債在中國人民銀行資產總規模中的占比僅為4.5%,“外部信用”所占的比例在2014年底高達82.4%,2016年底仍將近67%。考慮到(1)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2)中國政府債務率低于上述幾大經濟體以及國際警戒線、(3)中國的國有經濟和國有資產的占比遠高于一般國家,等因素,基礎貨幣投放依賴于外部信用、國債在中國央行資產總規模中如此低的占比不能不引人反思。
過去兩年間,中國央行的基礎貨幣投放方式已經開始由基于外部信用轉向基于商業銀行信用。2014年底到2016年底,對其他存款性公司債券占央行總資產的比例由7.4%上升至24.7%。但這只是第一步,未來還應推進基礎貨幣投放方式向基于國家信用方向的轉型。盡管除了個別民營銀行之外,我國大部分商業銀行都是國有銀行或者是由國有資本最終控股的銀行,具有“類國家信用”的屬性;但是,商業銀行信用仍然不完全等同于國家信用。商業銀行的本質是公司制法人,理論上存在破產倒閉的風險。況且,基于商業銀行信用的基礎貨幣投放方式會拉長信用傳導鏈條、降低金融體系的效率。一些規模較大的商業銀行以及廣義基金(包括各類基金、企業年金、保險產品、信托產品等)開始扮演類似于中央銀行的職能,向規模較小的商業銀行“發行”基礎貨幣。對于那些規模較小的商業銀行而言,其流動性來源不再單純依賴于中央銀行,而是開始依賴于大型商業銀行和廣義基金。大型商業銀行和廣義基金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中小型商業銀行的“中央銀行”。傳統的“中央銀行+商業銀行”的貨幣創造1.0體系正在轉向“中央銀行+影子央行+商業銀行+影子銀行”的貨幣創造2.0體系。
(3)加強國際大宗商品市場的定價能力和引領國際金融市場預期的能力
在經常項目下,中國已經是一個開放度很高的經濟體,資本項目的漸進開放也已列入中央政策日程、正在有序推進之中。中國每年從國外進口大量的石油、鐵礦石、銅、農產品,是國際市場上最大的買方,但這些大宗商品幾乎都是以美元計價的,且中國在定價博弈中并沒有充分利用好作為最大買方的優勢地位。這當然與具體產品門類的市場結構有關系,但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金融能力不足的制約。
例如,由于國際市場上絕大部分大宗商品是美元定價的,因而不論是大宗商品的買方、賣方、還是金融投資者,都必須關注美元匯率的變化。而市場上受關注最多的美元指數——ICE美元指數[1]——卻是以1973年美國對外貿易情況構建貨幣籃子的,僅在1999年因歐元區貨幣制度轉變做過一次調整。ICE美元指數的籃子貨幣包括歐元、日元、英鎊、加拿大元、瑞典克朗、瑞士法郎6種貨幣,權重分別為歐元57.6%、日元13.6%、英鎊11.9%、加拿大元9.1%、瑞典克朗4.2%、瑞士法郎3.6%,多年以來恒定不變。時至今日,ICE美元指數不僅在籃子幣種選擇上,還是在權重設定上,都已經無法客觀、全面地反映后來美元幣值的動態變化。但遺憾的是,正是這樣一個創立于上世紀70年代初的、早已過時的“闌尾炎”指數,至今依然讓全球金融市場和大宗商品市場參與者不得不時刻密切關注、神經緊繃。究其原因,就在于沒有更合理的、時效性強的指標被推出、作為替代。
隨著中國社會儲蓄和總財富規模的增加、參與國際金融市場和國際大宗商品市場程度的加、以及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的推進,中國應當在這方面有所作為,加快構建能夠反映全球經貿格局動態演變的“新美元指數”或者“人民幣指數”等指標變量,供金融市場參考和使用。例如,可以考慮在上海市場、香港市場或者法蘭克福和倫敦市場,推出相應的以新指數為標的的金融衍生產品。這也是現代國家金融能力建設的一部分。
[1] 又稱“美國洲際交易所美元指數”,ICE是美國洲際交易所(Intercontinental Exchange)的簡稱。
(本文作者介紹:清華大學經濟學博士,現供職于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CF40)青年研究員。曾任哈佛大學經濟系訪問學者。)
責任編輯:賈韻航 SF174
歡迎關注官方微信“意見領袖”,閱讀更多精彩文章。點擊微信界面右上角的+號,選擇“添加朋友”,輸入意見領袖的微信號“kopleader”即可,也可以掃描下方二維碼添加關注。意見領袖將為您提供財經專業領域的專業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