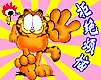| 《財經》雜志:職業金融家階層興起 | ||||||||||||||
|---|---|---|---|---|---|---|---|---|---|---|---|---|---|---|
| http://whmsebhyy.com 2004年08月19日 10:26 《財經》雜志 | ||||||||||||||
|
《財經》雜志8月5日封面文章: □ 本刊特約研究員 陸磊/文
任何一個重大的決定都將產生多重的影響。高盛進入中國,開啟了一條引入外資市場化處置證券公司風險的路徑;與此同時,一家世界一流的投資銀行與一個中國一流的投資銀行家發生了不同尋常的結合。 與以往金融市場對外開放比較,該事件的不同尋常之處在以下三個層面:一是信用主體的轉化;二是所有權與經營權的一致;三是風險鎖定下的激勵合同。而這三個層面所體現的含義絕非僅限于外資在中國資本市場上的準入,更深層次的問題是中國銀行家階層的真正興起。 信用主體的轉化將導致中國金融市場制度發生深刻轉型 已有的外資金融機構參與中國金融市場無非采取以下三種模式:一是“中金公司合資模式”,即摩根與建行合股組建新機構;二是“戰略投資模式”,如國際金融公司(IFC)參股民生銀行和南京市商業銀行;三是“獨資子公司或分支機構模式”,如匯豐、花旗等在中國設立分支機構。我們可以發現,除第三種模式不涉及信用關系外,前兩種模式的信用主體都是單一的——當前中國金融市場的機構存量。 但是,高盛向中國資本市場上的三家公司股東個人貸款,開創了信用主體轉化的新模式。 信用主體的轉型不僅僅是一種投資花招(trick)或新的業務增長點,而是潛移默化的體制變遷。確切地看,從1984年中國工商銀行從中國人民銀行分立從而漸進地展開金融體制改革的20年中,無論境內還是國外投資者普遍持有“國家信用嚴格高于機構信用,機構信用嚴格高于個人信用”的傳遞性(transitivity)觀念。合資和戰略投資模式依然是以上傳統觀念的現實體現,于是,我們可以觀察到三個具有中國特色的典型事實:一是國有金融機構的低效率與安全性的離奇組合;二是我們擁有世界性大銀行但不具備世界性的銀行家;三是存款人、投資者和境外機構對國家信用和國有機構的高度信賴甚至依賴。 我們需要關注的是維持這一體制和觀念所需要的成本是否國家所能承受。金融業值得思考的現象有兩點:一是2004年上半年銀行類機構各項貸款余額為18.1萬億元,增加1.43萬億元,依然是社會融資的絕對主體;二是股票市場流通市值1.26萬億元,半年縮水574億元。銀行類機構的絕對可信賴與證券類機構的不可信賴成為金融市場的主流觀念,這必然阻礙中國的資本形成效率,加大間接融資過度導致的系統性風險。 那么,在資本市場上,什么主體是更可信賴的信用對象? 高盛發現了以方風雷為代表的資深投資銀行家,并選擇了不與現有機構合作,不依賴國家信用,而依賴銀行家個人信用的路徑。直觀地進行判斷,這些銀行家個體的信用市值價值數千萬美元。 需要指出的是,高盛的另辟蹊徑并不意味著中國現有金融市場問題多于成就。恰恰相反,只有在金融業漸進轉型和逐步優化的過程中,銀行家群體才可能突破自身所代表的“機構標識”而浮出水面;同時,只有金融深化到一定程度,外資機構才可能對銀行家個人實施定價并完成信用交易。如此看來,中國的金融轉型畢竟取得了令人鼓舞的進展。 所有權與經營權一致化將以增量改革的方式推動存量重組 高盛在中國的合資公司將采取直接賦予經營者部分所有權的新模式,這在我國的企業改革領域絕非新生事物。但是,基于對個人或小群體控制金融機構并由此引發道德風險的審慎考慮,我國從來就沒有真正允許金融機構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合一。這種思考不是沒有道理的,2000年以前的城市信用社整頓中,大量的案例體現為信用社的實際控制者因“自我融資”導致整個機構陷入支付困境和局部金融風險。在我國金融改革和監管當局對如何設計激勵合同而傷透腦筋之時,高盛率先采取了對經營者貸款,并以此作為經營者持股來源的制度安排,這無疑是值得分析的。 一方面,金融業永遠面臨兩種道德風險的權衡取舍(tradeoff)。一種是始終困擾我國金融業的兩權分離、兩權制衡導致的積極性低下、等靠要政策問題。無論在證券市場還是在銀行改革中,把經營責任推給所有者和監管當局是始終存在的痼疾,于是出現了央行不斷無奈買單的局面。另一種是兩權合一導致的經營者(也同時是部分所有者)與存款人、投資者等無辜第三方的矛盾,即經營者可能濫用吸收的公眾存款或投資。證券公司一度普遍存在的挪用客戶保證金,部分高風險銀行類機構濫貸款以追逐高風險-高回報項目都屬于此類。 因此,理論上,我們只能在兩種道德風險間尋求相對平衡。 但是,這里是存在價值判斷的——哪一種道德風險是可控制的,或者說是成本更低的。我們認為,后者比前者好,這是因為,后者是可以通過激勵合同約束的微觀行為,比如監管的優化、業績考核等。而前者,除了制造低效率金融體系外,我們得到的僅僅是一個貌似安全但需要不斷需要貨幣發行來填補的黑洞。高盛之所以選擇了后者,是因為作為一家世界級的投資銀行,他們顯然對自身的激勵安排和治理結構具備充分信心。 另一方面,管理風險而不是回避風險是銀行家的基本職能。我國還沒有形成一個真正的銀行家階層,一個直觀的判斷依據是,金融機構沒有形成自主風險管理能力。盡管當前經濟存在過熱跡象,但熟悉金融業的人都應該對1997年至2001年間的金融機構高存差(或稱“惜貸”)記憶猶新。這一現象直接阻礙了中國的資本形成和經濟效率,其體制原因就是外部監管約束強化后金融機構發現信貸或投資是一樁“不劃算”的買賣。高盛通過直接賦予經營權和股權,事實上直接賦予了銀行家以風險管理權,發現收益等于發現風險,并有效地管理它。 風險鎖定下的激勵合同將設定新的金融業競爭標尺 當然,任何理性的機構投資者都不愿意過度承擔風險,高盛也不例外。但是,它采取了一種風險鎖定前提下的激勵契約安排——買入期權。對于中國銀行家持有的股權,它采取先安排貸款,后實行期權的方式。一方面,它的風險是鎖定的,無非是數千萬美元資本金。另一方面,它贏得了持續監測中國資本市場運行和這些銀行家績效的時間。 但是,我們關心的不是一家機構的得失,更值得思考的是這一制度安排的樣板效應。在整個事件中,監管當局和機構自身的利益取向是不同的,當局希望此事成為一個樣板,或者成為推動中國資本市場改革的真實起點;而機構自身的目的是盈利,因此希望至少在短期無法被競爭對手復制。 如果就此進行理性的預期,我們可望看到中國機構投資者將在客觀上被置于新的行業標準基礎上:第一,中資金融機構將不得不真正面臨既有外資管理與資金實力,又配比以強力本土銀行家的機構沖擊,由此不得不按新的行業標準競爭,中國投資銀行業的頹風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被清掃;第二,哪個銀行家可能成為方風雷一樣的QDII(qualified domestic invested individuals)——“合格的境內被投資對象”(這是筆者的自創術語)。 20世紀80年代企業改革以來,中國畢竟涌現出了新興企業家階層,并成為推動我國經濟長期、穩定、協調、快速發展的基本動力之一;但是,在金融改革20年來,我國沒有出現真正的金融家階層,這在一定程度上導致金融體制改革始終面臨極高的道德風險,始終無法擺脫機構層面的群起群落(如城市信用社和信托投資公司的整體興起和全行業整頓)。盡管我們不能十分肯定,但是職業金融家階層的興起將有可能造就一個權責對稱、道德風險較低、穩健經營的新型金融組織架構,并由此提高中國的資本形成效率和金融安全。■ 相關報道:
相關專題: 更多精彩評論,更多傳媒視點,更多傳媒人風采,盡在新浪財經新評談頻道,歡迎訪問新浪財經新評談頻道。
| ||||||||||||||
| 新浪首頁 > 財經縱橫 > 經濟時評 > 《財經》2004 > 正文 |
|
| ||||
| 熱 點 專 題 | ||||
| ||||
| |||||||||||||||||
|
|
新浪網財經縱橫網友意見留言板 電話:010-82628888-5173 歡迎批評指正 新浪簡介 | About Sina | 廣告服務 | 聯系我們 | 招聘信息 | 網站律師 | SINA English | 會員注冊 | 產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4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