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視頻背不起“精神鴉片”這口大鍋

歡迎關注“新浪科技”的微信訂閱號:techsina
文/佘宗明
來源:數字力場(ID:shuzilichang)
慎用‘精神鴉片’式大字報語言。
‘精神鴉片’
‘電子癮品’
在當下,沒被扣上過這兩頂帽子的互聯網應用,都不好意思說自己是爆款級產品。
繼游戲行業被‘精神鴉片’指控點了穴后,連日來,短視頻也成了靶子。
有人說,短視頻一刷就停不下來。
有人說,短視頻Low。
而‘娛樂至死’學說和‘奶頭樂’理論又雙叒叕被召喚了出來。
帽子扣上了,大批判就可以安排上了:短視頻‘正在毀掉一代人’,搞它!
還是原來的配方,還是熟悉的味道。
可問題是,循此邏輯,又有多少流行事物不是‘鴉片’?
進一步講,若沒有短視頻,人們的生活會更好嗎?
01
和菜頭說:每一個文盲都喜歡用‘殤’字。
每一個批斗愛好者,都喜歡扣大帽子。
這類帽子一列一大堆,‘精神鴉片’也在其列。
朋友西坡說:‘精神鴉片’不是批評互聯網的好姿勢。
我深以為然。
動輒‘精神鴉片’,不是表達力貧瘠,就是語言腐敗,抑或是兼而有之。
‘大字報’語言用多了,看什么都‘反動’。
蘇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隱喻》里,曾談到用‘戰爭隱喻’描述疾病的弊害:
一,暗示采取壓制措施與暴力的必要性。二,屬于過度描述,極大地助長了對患者的污名化。
這點出了‘以喻代證+亂貼標簽’的弊害。
‘精神鴉片’也一樣。
國人對‘鴉片’二字的敏感度很高,畢竟這連著的是那段屈辱歷史——提及‘鴉片’,很多人腦中自動蹦出的,是‘列強壓迫’‘文化入侵’的意象。
歷史傷疤,增添著人們對鴉片的深惡痛絕意緒。這份深惡痛絕,又會強化‘精神鴉片’等字眼的極端負面性。
把某項事物說成‘精神鴉片’,不異于給它判死刑:看,你禍國殃民,罪大惡極。
這不是要批評,而是要打倒。
不得不說,這口鍋太重了。
重到某些產品扛不動也背不起。
試想一下,若短視頻是精神鴉片,那眾多的up主就是制毒的‘絕命毒師’,別人給你發視頻就是販毒……一個個,都是精神犯罪者。
只不過是上下滑動屏幕的你,莫名其妙就成了精神吸毒者。
你怕不怕?
網游也同理。若網游是精神鴉片,那些打造‘電競之都’的城市,都是‘罪惡之城’。想想就覺得荒誕。
02
倒不是說,網游和短視頻不能批。
當然可以批。
前提是,就問題論問題,而不是只顧著貼大字報。
任何事物都有兩面性,網游和短視頻也不例外。
交通事故會‘尾隨’汽車文明,黑灰產會‘緊跟’互聯網創新,這都是負外部性的彰顯。
但有負外部性,不等于要將其一棒子打死。
該做的,是興利除弊,盡可能將負外部性壓減到可控范圍,降低事故率、打擊黑灰產,都在情理之中。
游戲、短視頻作為殺時間利器,沉浸式體驗、順應嗑瓜子理論的短反饋周期,都是在向用戶的多巴胺招手致意。
防止未成年沉迷,確實很有必要。
但防網游或短視頻沉迷,不是要防網游或短視頻本身,而是要防沉迷。
‘青少年沉迷’是那盆洗澡水,網游或短視頻就是盆中的孩子。該倒掉的,是洗澡水,而不是孩子。
這就需要,此類強體驗感產品拿捏好‘增強用戶黏性’與‘降低成癮性’的平衡。
在這方面,‘青少年模式’就是互聯網公司拿出的對策。
還有破除信息繭房的算法和各類防沉迷的提醒設計。
易上癮之外,Low也是很多人批評的點。
毫無疑問,說短視頻內容Low,往往是精英俯視視角下的‘五環內視障’。但在內容質量提升上,平臺確實大有可為。
短視頻是內容容器,就跟電影、電視劇等長視頻體裁一樣,它本身并無好壞,決定好壞的,是載入的內容品質。
現在各大短視頻平臺紛紛想法子對低俗化、劣質化內容限流降權,對泛知識類內容加大扶持,正是著眼于此。
有問題,那就指出并解決。
只顧著扣泛道德化的大帽子,卻不思考事物生成邏輯,針砭再猛,也只能是有堵無疏,是破壞力拉滿、建設性不足。
03
當很多人用‘精神鴉片’給短視頻生產者、平臺、消費者‘罪化設定’時,這未免對很多人不公。
如《失孤》男主原型郭剛堂。
2021年2月1日,郭剛堂開通抖音,錄視頻尋子,還成了尋人志愿者。其事跡在短視頻平臺上引發廣泛關注。后來,在公安民警的幫助和眾多網友的支持下,郭最終找到了失聯24年的兒子。
誰忍心說郭剛堂是‘精神制毒’?
如科普界的‘頂流’無窮小亮、普法的羅翔。
他們是知識布道者,在‘有梗’的同時讓很多人長了知識。
他們產的,分明是營養品。
比如曾經的那些《百家講壇》主講人,易中天、蒙曼、紀連海,都紛紛入駐抖音。
他們所做的,肯定也不是‘制毒’,而是從一個講堂到另一個講堂。
一句‘精神鴉片’,涵蓋不了這些益處,終究只是極端片面化的臧否。
短視頻作為圖文、語音、長視頻后的主要內容載體,實現的是傳播渠道革新。
用其所長,得其所益。
帶動旅游、助力扶貧、幫助尋人、傳承文化、傳遞知識、記錄日常生活、幫人打開視界……這些都是短視頻加載‘向善基因’后創造的公共價值。
就眼下看,很多農民在短視頻上賣農產品,不少地方通過短視頻宣傳本地景點,這都是對短視頻價值的注解。
更別說,短視頻還能拉動就業,光是抖音,就在2019年8月至2020年8月帶動就業機會3617萬個。
只要不瞎,恐怕都會將這些塞進‘新生產關系’‘新生活方式’的框架下,而不是裝進‘精神鴉片論’的抽象批判筐子中。
語言學家諾曼·費爾克拉夫說:‘當我們通過一個特定的隱喻來表示事物時,我們是以一種特定的方式建構我們的現實。’
很顯然,‘精神鴉片論’建構的現實,跟我們真實生活的世界隔了太多的次元壁。
04
杜駿飛老師說:
‘不可沉迷短視頻,但也不要用一個標簽來簡單否定——請注意,短視頻早已不是一種邊緣應用,而是一種媒介生態,甚至是一種文化生態了。想想看,如果長視頻能成為美食,那短視頻不會因為更短一些就成為‘×食’。反過來說,長也未必就沒有糟粕,譬如電視長而精彩,也有腦殘綜藝,電影長而高級,也有低俗神劇。’
意思很清晰:當短視頻已成國民級文化消費方式和無數人的表達工具時,就是跟大眾生活綁定在一塊了,已沉淀為新生產工具與材料,其利弊都得被看見,而不是只看到B面、看不到A面。
往更深了說,短視頻發展至今,已作為實然的的精神文化實踐嵌入大眾生活櫥窗中,也成了世相百態的觀察切口、社會大眾的情緒出口和現實摩擦的緩沖溝通機制。
它不是賽博空間,不是擬態環境,而是現實投影。
對于此類精神生活方式與載體,與其戴上‘鴉片’或‘毒草’等帽子,進行大批判,不如更客觀、理性、深入地觀察與剖析。
就像電影。電影市場中有不少爛片,但我們該做的,不是想著把整個電影行業都封禁掉,而是給良心創作提供更優渥的環境。
尊重市場規律與合規監管,可以并行不悖。但動輒喊封喊禁,必然與之相斥。
時代車輪隆隆向前,誰也沒法把我們拽回沒有短視頻的那個年代了。
回到‘精神鴉片論’上,鴉片的歸宿是被銷毀。
網游或短視頻,難道也該被不由分說地鏟除?
市場邏輯不會接受,監管理性也不會應承。
否則,依其邏輯,手機行業該被錘死——因為都知道‘想毀掉一個孩子,就給他一部手機’。
白酒行業也該被錘死——因為白酒有害健康,更別說,‘醬香科技’市夢率碾壓互聯網。
銀行業同樣該被錘死——2020年A股上市公司盈利前10都是銀行,這不助長‘脫實向虛’嗎?
而監管就只能有兩個按鈕——‘不管不顧’或‘直接錘死’,沒有‘用其所長,避其所短’的中間狀態。
05
有些道理仍需重申:
批評不是批斗,批評不該用大字報。
說‘××防沉迷機制仍需完善’是批評,說‘××是精神鴉片’則是大批判。
說‘××還需強化未成年人保護’是批評,說‘××正毀掉一代人’就是大字報思維。
不要總想著‘打倒××’。
想想早些年金庸的武俠小說、瓊瑤的言情小說、鄧麗君的歌曲都曾被視作‘毒草’,現在網游和短視頻又被認為是‘精神鴉片’,這難免拋出兩個問題——
還有哪代人沒被‘毀’掉?
‘毒草’‘鴉片’又何其多也?

(聲明: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新浪網立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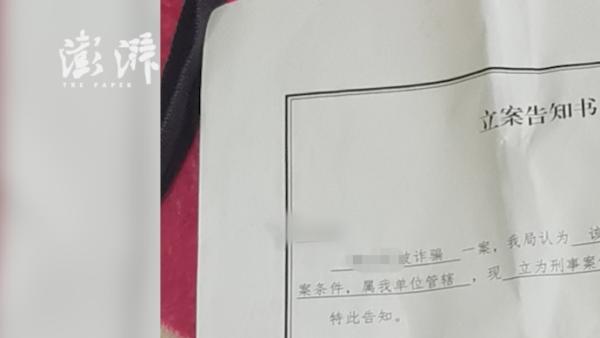 play
pla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