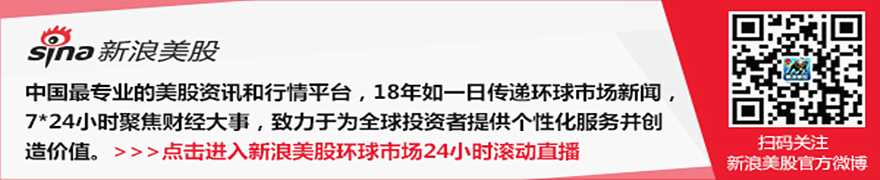@全體股民:《投資研報》巨額特惠,滿3000減1000,滿1500減500!【歷史低價手慢無,速搶>>】
發自華盛頓特區--關于近期金融改革的努力和大型銀行給全世界帶來的危險,有兩種相互矛盾的說法:其中一種是錯的;而另一種則是令人膽寒的。
金融業高管偏愛第一種說法,其核心觀點是銀行已經或者很快會采取所有必要的改革措施。銀行的負債/資產比率已經低于2007年的水平。美國限制銀行活動的新規定已經就位,而英國很快會就此立法--隨后歐洲大陸可能會效仿。這一觀點的支持者還聲稱銀行巨頭的風險管理比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前做得要好得多。
第二種說法是,世界上的銀行巨頭依然龐大得難以駕馭,而且它們有強烈的動機進行那種會搞垮經濟的過度冒險。去年摩根大通的“倫敦鯨”巨額交易損失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而且按照這種說法的主張,幾乎所有大銀行都表現出長期管理不善的病態。
雖然圍繞銀行巨頭的爭論有時聽起來過于專業,實際上卻很簡單。想一想這個問題:如果巨大無比的金融機構陷入危機,那么對經濟增長、失業等情況造成極大影響嗎?或者更直接點說,花旗集團或類似規模的歐洲企業陷入困境并再次面臨破產時,它們有可能不爭取任何形式的政府或央行幫助嗎(不管是用透明還是暗度陳倉的方式)?
隨著多德-法蘭克改革立法第二章在2010年通過,美國在正確的方向邁出了一步,這加強了美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FDIC)的危機解決能力。在與國內金融公司打交道方面,FDIC也已經研究出一些看似不錯的方案。(我在FDIC的系統性解決方案咨詢委員會任職;此處陳述的所有觀點都是本人個人觀點)。
但潛伏在金融業論點核心的則是一切順利的偉大神話。FDIC的危機解決能力對大型而復雜的跨境金融企業并不起作用。原因很簡單:美國法律只能創立在本國境內有效的危機處理機構。要解決像花旗銀行這種跨國公司的潛在破產問題需要一個各國政府和所有相關機構之間的跨國協議。
在華盛頓特區剛剛結束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春季會議的外圍會談中,我有幸能和來自不同國家的高級官員以及他們的顧問交流,也包括來自歐洲的官員。我問了所有人同一個問題:我們什么時候才會有一個針對跨國解決方案并具備約束力的框架?
他們的回答不外乎是“在我們有生之年都不可能”或“永遠不可能”。再次強調一下,原因很簡單:所有國家都不想要妥協其主權或以任何方式被束縛。各國政府都想有能力決定危機爆發時怎樣最好保護所謂的本國利益。沒有人愿意簽署任何條約或以受束縛的方式提前承諾(大多數美國參議員尤其如此,須知只有在他們批準之后條約才能生效)。
正如紐約聯儲主席比爾·達利德(BillDudley)最近所說--他使用了中央銀行家們的精巧語言:“我們仍需充分識別并去除那些妨礙建立有序跨境決議的因素。這對消除所謂的‘太大而不能倒’的問題來說是很有必要的。”
言下之意:針對全球銀行巨頭的有序解決方案是一種幻想。只要我們允許跨境銀行處在或接近它們目前的規模,我們的政治領導人就無法接受它們的破產。而且因為這些大型金融機構無論如何都是“太大而不能倒”的,它們能獲得相對低利率的貸款。更糟糕的是,它們既有動機也有機會變得更大。
這種形式的政府支持相當于對大型銀行的大規模隱性補貼。可以肯定這是一種奇特的補貼形式,但并不意味其對公眾利益的損害減少了。相反,伴隨政府對“太大而不能倒的”銀行的隱性資助會出現相應的風險,因此這可能會是世界上史無前例最危險的補貼。畢竟,更多的債務(相對于資本)意味著一切順利的話會有更高的回報。但如果形勢逆轉,這就會成為納稅人的問題(或是一些外國政府及其本國納稅人的問題)。
企業界還有哪些行業能像銀行業那樣有能力在2008年讓全球經濟陷入衰退?還有誰有動機將發行的債券數量最大化?
這兩種對金融改革的說法有一個共同之處,那就是它們都沒有一個好結局。我們要么限制大金融公司的規模,否則就得防范由債務推動的經濟爆破的降臨。
作者簡介:西蒙·約翰遜,麻省理工大學斯隆管理學院教授,合著有《燃燒的白宮:國父、我們的國債以及這為何與你有關》一書

責任編輯:王永生
VIP課程推薦
APP專享直播
熱門推薦
收起
24小時滾動播報最新的財經資訊和視頻,更多粉絲福利掃描二維碼關注(sinafin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