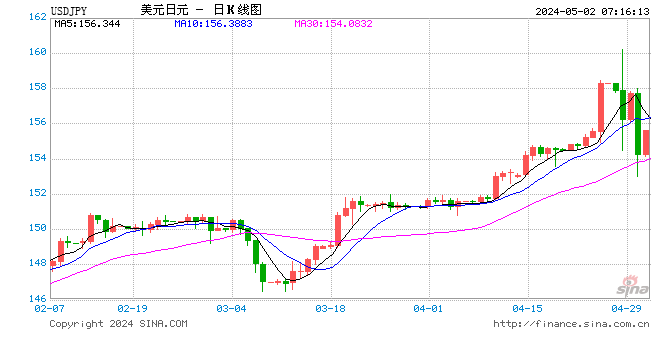作者 | 趙偉 國金證券首席經濟學家、研究所執行所長
| 段小樂 國金證券資深分析師
| 李欣越 國金證券研究助理
來源 |《中國外匯》2022年第11期
要點
浮動匯率制度與資本項目的開放、海外資產的快速積累以及逐漸形成的融資貨幣地位是日元成為避險貨幣的關鍵因素。近期日元避險屬性的弱化并沒有打破支撐其避險地位的核心邏輯,但長期會受到挑戰。
2022年初,俄烏沖突的意外爆發使避險資產再度成為市場關注焦點。根據Dornbusch等(2000)的研究,在危機發生時,各類資產間的聯動往往會被加強,這使投資組合多元化這一策略對沖風險的能力被顯著削弱。此時,如果存在某類資產與其他資產聯動性較差,能夠有效對沖資產價格波動風險,這類資產將會成為危機時期資金的“避風港”。而避險情緒推動下的資金不斷流入,也將最終促成這類資產的升值(Baur和McDermott,2016)。基于這一理論,提供固定回報且違約風險較低的債券以及高流動性的實物資產是典型的避險資產,美債、黃金分別是兩者的代表。在封閉經濟體中,現金與風險資產同樣有著較低的相關性,是規避風險的潛在選擇;但在開放經濟體中,各類貨幣在危機時期的相對表現差異則會帶來匯率的波動,此時,僅有幣值堅挺的貨幣可以被稱為避險貨幣。日元、美元、瑞士法郎即是避險貨幣的典型代表(Todorova,2020)。
日元避險貨幣的由來
為什么風險事件來臨時,各類貨幣中日元的表現會相對突出?首先,我們需要厘清哪些投資者會更偏好日元;其次,這些投資者的避險需求是否足夠且能夠支撐日元幣值。
從投資者角度來看,避險貨幣往往會受到進行套利交易的國際投資者與本國企業、居民的青睞,即存在國際投資者套利平倉渠道和本國居民海外資產回流渠道。一方面,站在跨國投資者角度,Brunnermeier等(2008)發現,當外部沖擊來臨時,風險偏好與資金流動性的下降會導致套利交易者對此前的套利交易進行平倉,而此前交易中被拆入的低息貨幣反而會成為資金的避風港。另一方面,站在本國投資者的視角,投資者存在本地偏好(Seasholes和Zhu,2010),而危機期間出于熟悉性(Flight to familiarity),本地資產會更受追捧(Schoors等,2019)。因而,擁有大量海外資產國家的貨幣,在危機時會出現海外資產回流,其貨幣的表現也會更加突出。
國際投資者的日元套利交易平倉渠道依賴于兩大前提:一是有大量資金以低息日元的形式向國際投資者拆出;二是外匯市場上日元具有高流動性,可自由兌換。前者確保了資金量足夠支撐日元幣值,后者則確保了這類資金能夠及時且低成本地被換回。從日本實際情況看,這兩大前提均得到滿足。一方面,自1998年日本銀行法頒布以來,日本長期實施寬松貨幣政策,無擔保拆借利率始終維持在0.5%;從歷年標準化的兌美元波動率來看,近5年日元是主要外匯中兌美元波動率最低的貨幣,平均波動率僅1.99%(見圖1)。利率低、匯率穩使日元成為了重要的融資貨幣,發達的貨幣市場與銀行業進一步滿足了國際投資者的融資需求。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國際投資頭寸表,截至2021年,海外居民、企業等部門共計以貸款等形式拆入81萬億日元,僅次于美元與歐元。另一方面,自1998年4月《外匯與對外貿易管理法案1998年修正案》實施以來,日本實現了資本項目的自由兌換。根據國際清算銀行(BIS)對外匯市場日均成交量的統計,截至2019年,日元日均成交1.11萬億美元,僅次于美元與歐元,是流動性最高的外匯幣種之一。

本國居民的海外資產回流渠道同樣需要兩大前提:一是日本有大量海外凈資產足以在回流時支撐匯率;二是此類海外資產流動性較高,易于在避險時回流。根據IMF統計,截至2020年,日本持有全球第一的國際投資凈頭寸,體量高達3.46萬億美元。其中,日本在資產端持有的證券投資頭寸高達5.07萬億美元,僅次于美國,位列世界第二。這類資產同時也具有較高的流動性。從持有人結構來看,日本國際投資凈頭寸主要由私人部門持有,相較于公共部門,私人部門的資金使用更為靈活;而資產結構上,截至2021年12月31日,日本國際投資資產端57%均以權益投資、債券投資、現金等形式持有(見圖2),而這類形式的資產均有著較高的流動性。

日元避險能力的練就
區別于天然的避險資產黃金和作為世界貨幣的美元,日元的避險能力并非與生俱來,而是逐步發展產生的。日本自1973年3月開始實施浮動匯率制,其資本項目的開放由20世紀80年代開始漸進式推進。1980年12月,日本通過了《外匯與對外貿易管理法案1980年修正案》,新外匯法的頒布,標志著外資流動由“原則禁止,例外許可”轉向了“原則自由,例外控制” (黃繼煒,2010),資本流動的障礙逐步被打破。直至1998年4月,《外匯與對外貿易管理法案1998年修正案》正式實現了資本項目的自由兌換。
浮動匯率制度與資本項目的開放為日元成為避險貨幣提供了制度保障,也是日元成為“避險貨幣”的第一步。從套利融資貨幣角度來看,高流動性與幣值的穩定建立在日本經濟與貿易發展的基礎上,而低息優勢的建立則需要依托于低通脹環境的形成。日本自1968年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其外向型經濟模式與龐大的對外貿易規模使日元迅速成為出口貿易中重要的結算貨幣。1971年,日本超越英國,成為僅次于美國和德國的世界第三大出口國。1980年,日元出口金額高達130.44億美元,而日本出口貿易中本幣結算比例也提高到29%(陳衛東和李建軍,2010)。貿易結算快速推進了日元國際化進程,日元在外匯交易中被廣泛使用,其國際化程度也在20世紀80年代快速提高(白欽先和張志文,2011)。1985—1987年間,經過日元兌美元的一次性升值后,日元兌美元匯率步入雙向波動時代,1987年至今整體圍繞110的中樞價格浮動,匯率相對穩定。另一方面,自1991年日本泡沫經濟破滅以來,日本陷入了長期低通脹甚至通貨緊縮的環境。對此,日本央行長期實施寬松的貨幣政策,1995年4月14日以來,日本央行貼現率始終在1%以內調整,且當前貨幣政策主要操作目標的無擔保拆借利率自1998年伊始也持續維持低位。由此,日元由僅在國內流通,通過貿易結算與對外日元貸款等形式一步步實現了國際化,并最終成為了套利融資貨幣。
持有大量的海外凈資產是影響日元避險能力的關鍵因素。Hossfeld和MacDonald(2015)認為,控制住套利交易的影響,依然能在危機時升值的貨幣有著“真正的”避風港屬性。Habib和Stracca(2012)對23個發達國家貨幣和29個新興市場貨幣的研究則發現,控制住與美國銀行同業拆借利差后,日元的避險能力仍然突出,而對其避險地位影響最為顯著的是海外凈資產規模。1985年《廣場協議》簽訂后,日元在近3年的時間里對美元單邊升值115.27%,在對日本貿易與經濟造成深遠影響的同時,也激起了日本海外投資的熱潮。1991年開始,日本正式成為全球最大的凈債權國,雖然國內經濟步入了“消失的20年”,但其龐大的海外資產在企業、居民的良好運營下很好地實現了保值與增值,日本國際投資凈頭寸全球第一的地位也一直延續至今。
由此,20世紀90年代來,海外資產的快速積累奠定了日元避險能力的基礎,而1995年以來日元逐步形成的套利融資貨幣地位也進一步強化了日元的避險能力。1990年以來,局部戰爭、金融危機、地緣政治、資本市場黑天鵝等風險事件的發生,均會引發衡量市場恐慌情緒的VIX指數(芝加哥期權期貨交易所的市場波動性指數)快速上升,而日元在多數情況下會同時快速升值。
日元避險屬性的變化
近期,俄烏沖突下,全球避險情緒再度升溫,但日元的避險表現卻顯著弱于歷史規律,引發了市場對日元避險屬性是否已經消失的爭議。俄烏沖突自2022年2月10日俄羅斯與白俄羅斯聯合軍演開始集中升溫,直至3月7日俄烏第三輪和談失敗升至峰值。期間,VIX指數從20.0快速升至36.5,避險資產則表現分化,美元指數和黃金分別上漲3.9%和8.4%,而美元計價下日元僅微升0.2%、瑞士法郎貶值0.4%。從與其他貨幣比價來看,日元指數和日元兌歐元分別上漲1.9%和5.2%,日元仍表現出一定避險能力。然而,1990年以來的17次VIX快速上升期,日元兌美元出現14次升值,本輪僅僅走平,日元的避險表現仍弱于歷史規律。
多因素導致了近期日元避險屬性的弱化。首先,新冠肺炎疫情以來,全球“大放水”使得美日、歐日利差快速收窄,日元套利融資貨幣定位受到沖擊,這是本輪日元“避險屬性”趨弱的主因。2020年3月以來,美聯儲重啟量化寬松政策,導致歐洲美元市場上美元隔夜拆借利率迅速滑落至低位,美日利差大幅收窄。與此同時,歐央行仍維系了負利率政策,并開啟新一輪資產購買計劃刺,導致歐日利差進一步走低。相對其他流動性更高的套利融資貨幣美元與歐元,日元失去低息優勢后,套利交易不再依賴對日元的拆入。根據IMF數據,2021年第三季度,日元對非居民信貸增速降至-5.8%,而美元與歐元對非居民信貸則加速增長(見圖3),套利融資貨幣地位出現了此消彼長。事實上,在前一輪歐美貨幣寬松階段也曾出現過類似的情況。2012—2014年,VIX指數與日元匯率相關性顯著走弱,VIX的四次飆升均未帶來日元的大幅升值,這與Yuki(2017)對于日元避險屬性變化的發現一致。

其次,美聯儲加息周期的開啟對日元的穩定性造成了沖擊,而套利交易依賴日元幣值的穩定。歷史上看,1999年6月和2015年12月開啟的美聯儲加息均導致了1個月期美元兌日元隱含波動率的大幅上升,而2004年6月美聯儲加息周期開啟后,日元的隱含波動率則保持了相對穩定。進一步看,2000年以來,共有5次發生在加息周期中的風險事件引起VIX指數快速上升,但僅在2018年10月日漸焦灼的中美經貿摩擦沖擊下,日元兌美元升值3.69%,其他幾次風險事件沖擊下日元兌美元的升值幅度均非常有限。
最后,俄烏沖突事件本身對日本也有波及。一方面,俄烏沖突推動能源價格高漲,日本國際收支進一步惡化。日本能源結構高度依賴油氣資源,根據美國能源信息署的數據,2020年日本對油氣的依賴度高達63%。俄烏沖突再度推升原油價格,3月7日,布倫特原油飆升至123.21美元/桶,顯著惡化了日本的貿易條件,日本花旗貿易條件在當日下行至-70.57,創歷史新低(見圖4)。貿易條件的惡化進一步沖擊了日本的國際收支,根據IMF數據,日本外匯儲備也較2020年底下滑了295億美元。另一方面,此次沖突對日俄雙邊關系也有擾動。俄日長期存在關于“南千島群島”(日方稱為“北方四島”)的地緣爭端,此次俄烏沖突后日本緊隨歐美對俄實施單邊制裁,導致俄羅斯停止與日本的和平條約談判,俄方即將退出雙方共同參與的南千島群島經濟活動。

日元避險地位的前景
短期來看,支撐日元避險地位的核心邏輯并未被打破。一方面,日本海外凈資產規模依舊龐大,海外資產回流渠道是日元避險地位的基本保障。另一方面,日本仍將維持低息。2022年3月18日,日本央行行長黑田東彥表示“日本不需要因為其他經濟體加息而加息”。在3月25日的國會講話中,黑田東彥也指出 “弱勢日元總體對經濟有利,日本央行將繼續實施刺激政策”。隨著歐美等經濟體貨幣政策正常化的推進,美日、歐日利差將再度走闊,而這也將促使日元作為套利融資貨幣的地位重新得到強化。
長期來看,日元的避險能力不會消失,但其避險地位會受到挑戰。避險能力描繪了貨幣在外部沖擊下貨幣保值/升值的能力,是一種絕對的概念;而避險地位則刻畫了避險貨幣間的競爭,反映了國際金融市場上風險來臨時,各類避險貨幣受國際投資者的相對歡迎度。從套息、流動性等角度來看,日本金融市場的深度、外匯市場的開放度均將長期維持。2013年1月22日,日本央行錨定2%的通脹目標,在長期經濟低速增長、需求疲弱難以提振通脹的背景下,日元的低息優勢也將得到延續。此時,決定日元避險地位的關鍵將是日本經濟的長期發展態勢。一方面,雙邊匯率根本上將由兩國間經濟基本面的強弱決定,日本經濟的發展將直接影響日元匯率的長期穩定性。另一方面,如果面臨長期停滯,日本海外凈資產的持續積累也將受到影響。
日本經濟自上世紀90年代起開始深受長期低速發展的困擾。其經濟對外依存度過高、能源結構過度依賴進口、人口老齡化問題嚴峻、產業結構過度依賴傳統制造業等一系列結構性問題,嚴重拖累了日本經濟的長期發展,時至今日,這類問題仍未被妥善解決。2009年以來,日本經常賬戶長期順差的格局被屢次打破,貿易順差的逆轉、外部風險敞口的暴露均將動搖投資者對于日本經濟長期的信心,進而影響其幣值的長期堅挺。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經濟既有的騰飛與未來的高確定性。2011年,中國經濟超越日本躍居世界第二。中國居民、企業的國際投資凈頭寸也在快速積累,截至2020年,中國國際投資凈頭寸高達2.29萬億美元,升至全球第二;外匯儲備規模高達3.22萬億美元,位居全球第一。出口方面,2009年,中國超越德國和美國,成為世界頭號出口國,截至2021年底,中國出口規模達3.36萬億美元,已近美德兩國出口總和。龐大的經濟貿易體量迅速支撐起人民幣的國際化地位,隨著2016年10月1日人民幣被正式納入特別提款權(SDR)貨幣籃子,根據BIS口徑,2019年人民幣的日均成交額已接近澳元、加元和瑞士法郎,全球官方人民幣外匯儲備規模也達到了3361億美元。在經濟轉型與結構升級的不斷推進下,我國正逐步完成新舊動能的轉換,“雙循環”格局的形成、“雙碳”先機的把握、“卡脖子”技術的突破將支撐起全球投資者對中國經濟發展的長期信心(趙偉,2020)。
借助于VIX、EPU等指標,張沖等(2020)考察了2006—2018年間人民幣的避險能力,發現人民幣的避險能力已經逐步顯現。依托于不斷增強的國力,隨著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的不斷推進與資本賬戶的穩步開放,人民幣的強勢崛起將有望在未來挑戰日元的避險地位。

責任編輯:郭建
投顧排行榜
收起

 產品入口: 新浪財經APP-股票-免費問股
產品入口: 新浪財經APP-股票-免費問股


 產品入口: 新浪財經APP-股票-免費問股
產品入口: 新浪財經APP-股票-免費問股
 產品入口: 新浪財經APP-股票-免費問股
產品入口: 新浪財經APP-股票-免費問股
APP專享直播
熱門推薦
收起
24小時滾動播報最新的財經資訊和視頻,更多粉絲福利掃描二維碼關注(sinafin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