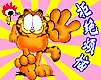| 第五問:土地私有化就可以拯救農民? | ||||||||||
|---|---|---|---|---|---|---|---|---|---|---|
| http://whmsebhyy.com 2004年08月19日 13:25 南風窗 | ||||||||||
|
2004年春節,光澤縣“當代農場主”傅光明,請來四鄉八鄰的“村官”們,搞了個縣城水平的PARTY,一頓酒席,外加一個500元的“紅包”。“村官”們驚嘆,這個將農業產業化的老板,這一回真大方。 知情者感慨,再富有的老板天性都是摳門的,要不古人怎么說“慈不帶兵,義不養財”呢。傅老板這樣做,也是無奈。他的養雞場都建筑在農民的承包責任田里,土地要想集
3個月后的延平區爐下鎮下井村,“還我良田”、“還我耕地”的標語插在正待開發的“工業園區”上。鎮黨委書記對前往調查的新華社記者說,2001年春天,為調整爐下鎮的產業結構,三級政府共同努力,從福建省鄉鎮企業局獲得了第一個“省級工業園區建設基地”。依規劃,首期2300畝工業園區和700畝商貿住宅。一年以來,延平區已投入1800萬資金用于土地的平整,填埋了422畝農田,涉及農戶425戶。 對于不同意征地的農民,官員們的想法是宣講開發區的意義、政策和前景。他們考慮農民以被征用的土地入股,逐年返還,讓農業的利益和企業的利益長期捆綁在一起,以尊重失去土地的農業的利益。 這樣的場景,雖然很多專家和官員們沒有見過,但他們想象過。2000年記者在京都一位智囊級學者家中,聽到他感嘆我們土地改革的滯后。土地不能私有化,不能買賣,在不少學者眼中,是政策上的遺憾。他們的論點大致如下:工業化的生產方式早已普遍進入發達國家的農業生產領域,而我們中國的文盲半文盲的農民,還在牛前人后地從事小農意識下的分散經營,如果我們不能創新土地經營制度,就走不出規模化、集約化、科技化的路子,社會資產就不能進入農業領域,在政府的政策性資金杯水車薪的冷酷現實下,傳統農業比較效益低的可憐狀態就難以改變。如此一來,當美國的農民說起基因農業太空農業,我們的農民可能連聽都聽不懂。 應該說,這樣的觀點,在邏輯上是沒有問題的。何況,臺灣的農民,就是在土地私有后獲得階段性飛躍的。 但是,這樣的觀點在現實中,是經不住推敲的。富裕地區的農村開展土地流轉是有必要的,可中國農民貧困的根源是什么?農業問題專家溫鐵軍提出了“人地關系高度緊張”的說法。 截至2002年,中國人口已增加到13億,人均耕地減少到約1.2畝。而且,由于人口分布不平衡,有1/3的省市人均耕地不足1畝,有666個縣低于聯合國確立的0.8畝的警界線,463個縣低于人均0.5畝的危險線。 由于人地關系高度緊張,中國的耕地,不再是西方經濟學者眼中的“生產要素”,它不能體現市場配置資源的效率,不可以源源流向收益高的行業或者個人。 為什么那么多的農民把耕地當作他們的命根子? 我們可以聽聽爐下鎮農民的說法。下井村72歲的老農王火金,從家中拿來兩本“承包土地經營權證”和“耕地承包合同書”,遞給新華社記者張國俊:“我家4口人,分得水田2.35畝,上面寫著承包經營權30年不變,如今怎地說收回就收回呢,現在我家一分地都沒有了,我人老了又不會做別的,除了種田根本就沒有其他收入,你叫我吃什么?” 在另外一個村,中年農民陳水金等春耕大忙時節坐在村口閑談,論及原委,陳說:“我家1.66畝水田,這次搞開發全部填埋了,現在又找不到別的活干,不聊天還能干什么?” 由此可見,耕地,對南平農民乃至中國的多數農民,還是生產資料。它所承載的生產功能,遠遠不如它對農民的福利保障功能。所以,我們應當強調耕地的公平原則,高于效率原則。 未來幾年,農業剩余勞動力不會少于1.5億,如此之多的失業農民怎樣才能棲息在我們這個地球上?這時候,專家們所呼吁的給農民以公平的國民待遇,讓他們自由地流動,就有了制度保障意義。讓農民在城鎮中尋找非農就業的機會,以增加他們的收入,就能解決三農問題嗎? 有人說,必須發展工業,通過工業帶動第三產業。并列舉了江蘇昆山的例子。問題又回到老路上,我們從哪里獲得發展工業的土地?規模經營,土地流轉,土地私有化,循環又出現了。 但是,如果農民不能在非農產業的土地上獲得就業機會,贏得更大收益,如果大多數農民離開被流轉的土地就找不到飯碗,規模經營,農業產業化等等,就失去了前提。 2001年,記者去浙江紹興采訪有第三次土地革命之稱的“土地流轉制度”。那里的經驗,確實值得借鑒。采訪期間,接待我們的地方官員應接不暇,因為從中國諸多省份來的取經者“踏破了門檻”。時任紹興市農辦副主任的陳功苗向記者抱怨偏遠落后地區的一哄而上:“我們紹興綜合經濟規模早就跨入全國大中城市20強行列,紹興農民2000年人均收入5000元,從事第二第三產業的農業占80%,這樣的前提條件,是取經者都具備的嗎?” 不曉得南平的官員們當時有沒有出現在取經的隊伍里。南平以及南平之類的農村,根本就沒有土地流轉的前提。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一位副主任,在福建泉州舉辦的“農村集體土地產權制度改革”研討會上說:“農村集體土地的流轉和集中,一定要從實際出發,切忌一哄而上,一股就靈。如果一個地方,人還是那些人,地還是那么多地,特別是土地使用權沒有發生多大變化的地方,流不流轉沒有多大必要。” 中國的學者們在鼓吹土地私有化的同時,要保持一份冷靜和責任心,不能被地方官員們謀求GDP的熱情所蒙蔽。2003年初葉,國土資源部官員對第三輪圈地風潮作了一個分析,稱違法圈地存在著周期性,一般情況下,新一屆地方政府這邊宣布各就各位,那邊圈地風馬上刮起。 在GDP高速增長的同時,《中國改革》農村版刊載的一項計算表明,如果按照現行征地制度與經濟發展速度,2030年,中國的失地農民將超過7800萬人,占現有農民數量的1/10。 2002年《南方周末》記者曾在一個大城市的郊區,作過一個郊區城市化的調查,最后的結論中有一點:農民在失去土地的城市化過程中,表面上從農民變成了市民,卻在實際上變成無所事事的流民。 所以,在人地矛盾暫時得不到緩解的當下,耕地與其說是生產資料,不如說是生存資料。我們對耕地意義的分析,首先要亮明的,是它的福利保障功能,而不是其他。中國的學者們,在為中國農民問題開藥方時,在農業產業化或者土地經營管理的研討會上,千萬別忘記了這個背景。中國需要摩登大廈,中國農民也需要穿衣吃飯。- 系列報道:
|
| 新浪首頁 > 財經縱橫 > 國內財經 > 關注“三農”問題 > 正文 |
|
| ||||
| 熱 點 專 題 | ||||
| ||||
| |||||||||||||||||||||||||
|
新浪網財經縱橫網友意見留言板 電話:010-82628888-5173 歡迎批評指正 新浪簡介 | About Sina | 廣告服務 | 聯系我們 | 招聘信息 | 網站律師 | SINA English | 會員注冊 | 產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4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