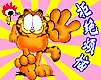| 南平折射的中國“鄉情”拷問三農藥方--下篇 | ||||||||||
|---|---|---|---|---|---|---|---|---|---|---|
| http://whmsebhyy.com 2004年08月19日 11:40 南風窗 | ||||||||||
|
作者:章敬平 中國三農問題的出路在于“消滅農民”?土地私有化能救農民于窮苦?“盆景農業”是中國農業的未來?民主制度能消弭三農難題于無形?面對高居“廟堂”的部分學者高調開出的三農“藥方”,處江湖之遠洞悉鄉村真實世界的人們,應該針對他們揮斥方遒的論調,多打幾個問號。
考察南平的現實,任何不懷偏見的人,都會發現高瞻遠矚的“消滅農民論”,多么像那個聽說災民饑荒遍野就說“給他們肉吃”的皇帝。而明知非農化有害的縣域經濟執行者,在尋求“消滅農民”理論支持時,又是怎樣的一種冷酷。 下篇:三農藥方再審視 第一問:“消滅農民”? 2004年春天,記者在南平電力賓館上網時,偶然看到一個投資機構的宏觀政策分析。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在于消滅農民,已經作為一個常識,一個無須再經論證的公理,成了投資決策者分析投資增長模式的論據。 我們不妨將部分相關文字援引如下:在投資的內生性與行政干預的較量中,有3個因素決定了目前投資增長模式的合理性和持續性。首先是全球制造業向中國轉移為投資大幅增長提供了外部推動力,其次便是農村城市化的新思路為城市基建投資提供了持續推動力。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就是消滅農民,讓農民變成城市工人;消滅農村,讓農村變成城市。農民變成農業工人,農業的產業化才有基礎。這一過程從城市向周圍農村的擴張開始,農民向中心城市聚集、城市群帶的發展對基礎設施建設、房地產及相關行業提出了更多的需求。由于城市化是一個長期的過程,由此導致的投資活動也將是持續的。 記者無意于辯駁該分析的正確與否,記者關心的是,消滅農民怎么成了一個廣泛的共識?誰說“消滅農民才是解決農民問題的根本出路”?消滅農民需要多長時日?在一個有著9億農民的國家,我們怎樣才能消滅農民? 記憶中,過去的3年里,中國的很多理論家和農村問題專家提出過這樣的“高見”。原以為他們的說法,僅僅是一種說法而已,沒料到它們對中國公眾的影響力竟然如此之大。 去網絡搜索引擎上一查,“消滅農民”確已成為公眾廣泛接受的概念,一個可以解決三農問題的“動賓結構”。從作客著名網絡媒介的人大代表,到著書立說的理論家,把脈三農問題,無不言之鑿鑿地開出“消滅農民”的藥方。 當然,他們一般會解釋其實不用解釋的兩個小問題:消滅農民不是從肉體上消滅,而是讓他們轉變為工人;農民的出路在于消滅農民,消滅農民的出路在于市場經濟和市場化的綜合改革,這是古典經濟學的邏輯。 顯然,這樣的藥方,已經贏得廣泛的認同。 2004年3月6日,一位知名策劃人以特約評論員的身份,出現在南方電視一頻道的“兩會報道”上,講到三農問題,他援引了當天早上從報章上看到的專家的一句話:“解決農村的問題在于消滅農村,解決農民的問題在于消滅農民。”他說:“雖然極端了一點,但是也不乏道理。” 記者出身的策劃家,顯然要比一般的專家冷靜,他在電視上說:中國的三農問題與美國等國家的情況不同,畢其功于一役的短線思想是解決不了問題的。 主張“戰略眼光,長線思維”的策劃家認為,如果能用20年解決中國的三農問題,已經是非常了不起的貢獻了。 他的估計,應該是樂觀了。我們從不相信中國農民問題無解,但我們絕對沒有樂觀到“20年解決三農問題”的程度。從西方經濟學中克隆出“消滅農民論”的專家學者們,如果沒有時間或者沒有興趣,把自己心靈中的“皮球”真正沉到鄉村的“水”中,那么可以看看李昌平的《我向總理說實話》。比較而言,李的書對中國鄉村現狀的描述,應該更客觀更真切些。 中國鄉村還沒有懂得市場經濟的原始概念,他們以為市場經濟就是集市上的提籃小賣,他們還不知道美國的柑橘商人的到來,對他們意味著什么,因為他們根本就不曉得大山外的市場是什么樣子,也無從獲悉上海小姐們對竹筍的口味需求,有了什么樣的變化。 面對這樣的情勢,20年解決三農問題,不是非常了不起,而是根本不可能。或許局部地區可以,但整體上是不可以想象的。可以說,至今為止,我們還沒有找到一副有效療治中國三農沉疴的靈丹妙藥,遑論畢其功于一役。 讓我們先考察一下世界歷史上解決三農問題的案例。一個大眾化的說法是:日本解決三農問題用了50年,美國花了70年,英國拖了近百年。考慮到中國三農問題的復雜性和特殊性,不知道專家們有什么理由相信,我們能在短期內消滅農民,完成農業現代化。 沒有人能推算,中國的三農問題能在多長時間內解決,中國的農民能在多少年后被消滅。但我們可以嘗試著以空間為經,以時間為緯,作個比較后的揣度。 從時間來看,消滅農民,進入農業現代化,是中共全面奪取政權后就開始追求的目標。1950年代初葉,毛澤東就從提高生產力水平入手,提出農業現代化的第一步:農業機械化。20年后,毛澤東終生的革命同志周恩來總理,亮明了四個現代化的第一個目標:農業現代化。又20年過去了,正如我們所看到的,中國農村大部分田地上的勞作方式,還是千年來亙古不變的牛前人后。 當然,應該客觀地指出,50年沒有“消滅農民”,沒有進入農業現代化,癥結在于領導層的精力不在生產力,而在生產關系的調整上。更為重要的是,農業完全是“零積累”,農業創造的剩余價值,都被工業化所榨取。如果排除這兩個要素,“消滅農民”的愿望是否就指日可待了呢?這讓人毫不樂觀。 僅就人口而言,較之過去可謂長勢憂人。人地關系高度緊張,這個中國農業不發達、農民貧困的關鍵要素,變得更為突出。根據農業問題觀察家溫鐵軍的數據,中國人均耕地減少到約1.2畝。由于人口分布不平衡,有1/3的省市人均耕地不足1畝,有666個縣低于聯合國確立的0.8畝的警界線,463個縣低于人均0.5畝的危險線。 從空間看,中國農村貧富狀態的地區差異委實太大。最近兩年,記者頻頻造訪蘇南和浙江紹興嘉興一帶的鄉村,那里的工業化程度,可以從農民的腳部看出,有人形容為:赤腳上田,穿上皮鞋,打上領帶。 2001年,記者曾去紹興采訪土地流轉,發現多數農民的土地,確如西方經濟學所理解的那樣,已是體現市場配置資源“效率”的“生產要素”。 而南平,耕地對占南平市總人口3/4的農民,是“生產資料”,是“命根子”。土地所承擔的福利保障功能,遠遠遜色于生產功能。 2002年,記者去溫州農村采訪,一個鄉鎮民政辦的小公務員,遞出的香煙是三五十元一盒的中華煙。 2年后的今天,記者在南平農村采訪。順昌縣一個鎮長接待包括縣委辦公室主任在內的我們,在食堂吃了一頓晚飯,寒酸得讓我們驚訝不已。那時候,我們心想,要是把溫州鄉鎮干部的生活告訴他們,他們會不會不想干了? 我們在談論空間差異的時候,還要強調一句:富裕的鄉村,是少數,貧窮的地方,是多數。 綜觀時間和空間的比較,現在,請專家們揣度一下,把“消滅農民”當作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出路,妥當嗎?- 系列報道:
|
| 新浪首頁 > 財經縱橫 > 國內財經 > 關注“三農”問題 > 正文 |
|
| ||||
| 熱 點 專 題 | ||||
| ||||
| |||||||||||||||||||||||||
|
新浪網財經縱橫網友意見留言板 電話:010-82628888-5173 歡迎批評指正 新浪簡介 | About Sina | 廣告服務 | 聯系我們 | 招聘信息 | 網站律師 | SINA English | 會員注冊 | 產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4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