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年好友蘇東坡9
來源:秦朔朋友圈
我最近看到了東坡的弟弟蘇轍寫的《榆》,內心深處被感動到了,于是這一篇講講蘇東坡與他弟弟的故事吧。
《榆》為什么讓人感動,因為它讓我泛起了生命記憶。我記得我小時候特別喜歡榆樹。十二三歲的時候我內心里就開始不自覺地長了一個孤獨、自由、寧靜的靈魂。在紅彤彤的落日底下,我一個人撿著暮春里飄落下來的榆夾,仿佛是撿起來了詩意和創意的種子,這讓人永生難忘。
從那時候起到現在我算是寫了二十年了,寫報告、論文、詩歌、散文、小說、廣告,什么都嘗試什么都敢寫,雖然沒寫出什么名堂來,但這顯然是我的生存和生活方式了。我的生命底色再蒼涼、寂寞,現實里再有什么動蕩和打擊,我都始終還有一個穩定的自我認知,永遠可以回到那個場景里,獲得生命力。
蘇轍是這樣寫的,“凜然造物意,豈復私一木。置身有得地,不問直與曲。青松未必貴,枯榆還自足。”
這首詩是東坡遭遇烏臺詩案,在御史臺獄中經歷磨難,有了人生中最強烈的對于死亡的恐懼時,他的親弟弟為了撫慰他的心靈而寫作的詩歌。
東坡被捕之后,蘇轍馬上上書說愿意代兄坐牢。他相信東坡是無罪的,便一直為他鳴不平,又不斷用書信詩歌鼓勵勸慰他哥哥。東坡在獄中最想與之交流的也是弟弟蘇轍,就怕與他就此訣別。還留詩(類似遺言)交給了獄卒。他們兩兄弟第一次有了生離死別之感。
解析一下《榆》,其含義是:“秋風吹過,萬物凋零,所謂貴賤榮辱就是地勢造成的。這只是大自然的規律。青松雖然在秋冬依然翠綠,并不是因為它本身有多高貴,而枯榆在凜冽的秋風中依然可以自足,等待來年。”
身處困境的時候,不要對未來灰心,不要自暴自棄,在逆境里怎么也能活下去,甚至活出尊嚴,我們要處賤不辱。
蘇轍不僅寫了《榆》,還寫了《槐》——“草木何足道,盈虛視新月。微陽起泉下,生意未應絕。”
好一句“生意未應絕”,事情沒有想象中那么好,肯定也沒那么壞。東坡后來果然在多方迎救下出了獄,但被貶為黃州團練副使。那一年,東坡42歲,蘇轍40歲。中年人的人生,是莫測的,若有一人相互扶持,始終相依相伴,心靠的很近,該多好啊。

東坡真幸運,在他64年7個月的人生中,弟弟蘇轍陪伴了他33年2個月。一半以上的生命有這個弟弟陪著。如果說現代人生二胎有什么好處的話,大概就是,若是像蘇氏兄弟這樣做到極致,真是人生之大幸。
他們的相伴真的是長長久久,即便是東坡的人生伴侶(妻妾)王弗、王閏之、王朝云都沒有這么長的。最長的王朝云,也只有22年。把周圍的幾乎所有“可用”“可陪”之人都培養成了知己,恐怕只有蘇東坡有這個能力。他的身邊從來沒有“最熟悉的陌生人”一說,因而不用戒備森嚴,不用懷疑質疑,該是多么有安全感、信任感的踏實一生。人生的實質和內容,大概就是這樣的形態。大部分人對于身邊的人,其實就是一個想的起來的“符號”,然后涂上一層所謂“人生意義”,其實很容易就褪色。
蘇軾與蘇轍,相差兩歲(分別1037年和1039年生人)。他們有好父親,也有一個好母親,都輔導他們讀書。而且由于家境優渥,父母供得起兩兄弟的理想和追求。
蘇轍曾回憶,“轍幼從子瞻讀書,未嘗一日相舍”。兩兄弟一起度過了天真爛漫的少年時代,也有了一起成就功名的美好時刻,成家之后剛開始的生活也是無憂無慮的,他們就這樣彼此相伴20年7個月。這個20年是少年時代、青春期,看起來真是不錯。人生的底打得好,怎么都夠了。
他們第一次分離,是嘉祐六年(1061年)辛丑,東坡去了鳳翔府(位于今陜西)任判官,蘇轍留在汴京侍奉父親蘇洵。他們從這一次開始就約定以后要早退、要隱居,“同歸林下,對床夜雨”,并且時常在往后的詩文中說起這件事。兩個人之間有某種約定,是件很奇妙的事情,它可以在歲月里打撈起不少月光般的東西。
一別三年,他們才重新相聚。后來一起經歷了父親去世的悲痛。隨后,因為兩人公事都繁忙,無法經常相處。五年后又分開了。東坡去杭州外派的時候,蘇轍去潁州相送,隨后的七年間(1071-1077年)始終分隔兩地。在這個第二個20年中,他們的官場生涯沒有太多波折,只是兄弟倆聚少離多。算一算,加起來有8年左右時間是團聚的。中年人生的初局通常還沒有太多波瀾,越往后走挑戰更大。
烏臺詩案發生后,他們之間剩下的另外的22年大致可以分為兩個階段。1080年,蘇東坡被貶黃州(今黃岡),路過陳州(今淮陽縣)的時候,蘇轍特意從南京趕來與哥哥相聚三日。后來他還送東坡家小來到黃州。東坡特地跑了20里地來迎接,接著又是四年沒見。
人到深度中年總是漂泊,身不由己,蘇氏兄弟經歷了各種生死攸關、步步為營、變幻莫測的官場環境,但始終相互攜手,沉穩前行,共進退、同患難。這14年1個月中,他們相處時間是4年6個月。
到了晚年,兩兄弟更是被一貶再貶,聚少離多,在近8年時間里,最多只在一起1個多月。
據統計,東坡涉及兄弟之情的242首詩歌創作中,只有49首詩創作于相聚時,193首都是分離狀態。可見,分離和思念總是詩歌最好的溫床。他們兩個總是有說不完的話,道不完的思念和內心的孤寂。
蘇轍的《懷澠池寄子瞻兄》,抒發了思念和孤寂。東坡則回應了《和子由澠池懷舊》,成為千古經典——“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抓,鴻飛那復計東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壞壁無由見舊題。往日崎嶇還記否,路長人困蹇驢嘶。”
中年人可能要面對各種離別。人生也就是這幾件難事——生老病死斷舍離。很多時候,這個問題是無解的,別離自己的朋友、親人,離開熟悉的地方、告別自己熟悉的、習慣的生活方式,而且還不知道別離會再發生多少次,要漂泊多久。對于這對“難兄難弟”而言,更是這樣。
由于他們感情太好,別離次數又過多,就為后世提供了很多面對失落和別離的方法。東坡曾寫“吾生如寄耳,何者為吾廬。”理解并接受了“人生如寄”。蘇轍寫了學術著作《古史》,他認為,百年人生不過俯仰之間,在歷史中,風雨和困難都是一瞬間,過好自己的生活只能求諸于己。在他二次被貶時,寫過“孤舟適遠身如寄,二頃躬耕道自肥。”因為人生如寄,本質上都是無依無靠的,最終還是要靠自己把自己活好。懂得了這個道理,修煉好了自己,也就光明得道了。
東坡幫蘇轍的女兒一個個都安排嫁到合適的好人家,也總是為他擔心這個擔心那個。但更多時候,他也不是全能的。在精神上,誰都是孤獨的。雖然在人生中,可能會有很好的父母、兄弟、朋友、貴人相助,但人最終是自己孤獨地走完這一生的,只能閉著眼睛勇敢闖蕩。在這個過程中,不可替代的精神對話者,是稀有的、最珍貴的。
東坡把弟弟當成知己——“嗟予寡兄弟,四海一子由。”“此外知心更誰是,夢魂相覓苦參差。”“吾從天下士,莫如與子歡。”“我少知子由,天資和而清……豈獨為吾弟,要是賢友生。”蘇轍是他的弟弟,更是朋友,是知己,是命運共同體。
人生在漫長的歷史與歲月中,真是不足道啊。哪里才是你的家?命運才是你的家。
另外,蘇氏兄弟告訴我們,只有思想與生活緊密聯系,才能走出困境。精神越是強大,它的外延就越小。自己擁有的樂觀是解救的藥丸,人生之幸可能在于,總有人可以相互監督鞭笞,做同一類型的事情,感同身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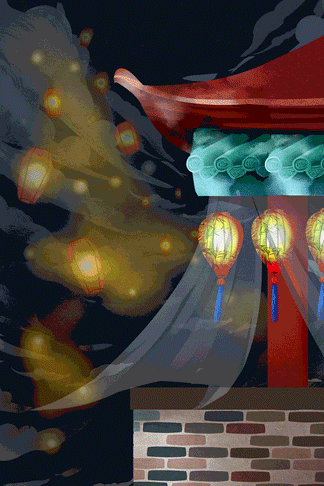
蘇轍的才華其實并不比東坡差。少時,他就比東坡沉穩圓滑些,但也容易因為剛直,堅持自己而得罪人,他第一次入仕就遇到挫折,官職化為烏有。但他很快想明白了,專心在京城隱居做學術研究,著書立說。這讓東坡很是欽佩。
我們現在最熟悉的是古人的詩詞,其實古人看中的是自己的學術研究、解決政事的能力,詩詞歌賦并不是文人的主業,只是調劑品。東坡是到24歲才寫詩,37歲才填詞的。從這種意義上說,真正讀得懂詞的都是有故事的中年人。
蘇轍更不愿意為了寫詩而寫詩,而他留下的詞也只有4首。東坡離世之后,蘇轍隱居在潁水邊,用心與自己的妻子孩子相處。他在東坡的光芒之下,心態從來是穩定的,一個人有了研究精神和真正的審美情趣之后,是可以自足的。
蘇轍從小體弱多病,所以比東坡更關注修身養性,在他的生命排序中,“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可能是倒過來的。
東坡很佩服弟弟的研究精神,他在黃州時,曾說“閑廢無心,專治經書”。他讀了《論語》《書》《易》,弟弟則同時讀了《春秋》《詩》。
東坡總是從弟弟的詩文和信為基礎,再做些延伸和拔高。這么看來,問題的發現者更具有原創性,是弟弟給了東坡新的啟發。他們從小志趣相同,蘇轍特別了解東坡的抱負,要實現“當世志”,想成為全才。比如東坡在1064年,27歲的時候夏軍攻邊境時,他還想去參軍帶兵。
他們有共同的工作和生活追求,所以總是有說不完的話題,思念、慣性(文學交往和學術探討)、情緒瑣事等等,都可以聊成經典。他們在被貶的時候,都有共同的救贖之道,就是相信道術和禪學。這樣,他們可以在做事的抱負和歸隱的樂趣之間自由切換。蘇氏兄弟于是成為了文化范型。
他們的“樂觀”礦藏豐富,可以隨時挖掘出來用。比如,對于東坡而言,買不起羊肉可以好好研發豬肉,于是給后世留了“東坡肉”。不戚戚于貧賤,不汲汲于富貴。世路無窮,勞生有限。他讓人明白,用你最好的能力去對付你最差的際遇,用你最好的一面擋現實的子彈,這就是自救。
怎么活得好呢?怎么養自己的氣質呢?靠社會實踐、游歷、向名師請教,跟賢人交往。蘇轍說的,心安就氣安。
東坡則提出了一個更美麗的概念,叫“身與竹化”。
這個詞源自于他的《書晁補之所藏與可畫竹》:“與可畫竹時,見竹不見人。豈獨不見人,嗒然遺其身。其身與竹化,無窮出清新。莊周世無有,誰知此凝神。”
什么意思呢?欲畫墨竹,需先胸有成竹,身與竹化,才能畫出竹子的神韻,將自己所見化為優美的藝術形象。
所謂審美是不帶任何欲求的,帶了就有煩惱和悲苦。蘇轍晚年經常入定,他獲得了那種進入虛靜接近無限的生命感受。
身與竹化,與大自然融為一體,世界萬物皆在我胸中。這樣才能不被困境、壞事、痛苦縈繞吧。還是祝大家好。

(聲明: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新浪網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