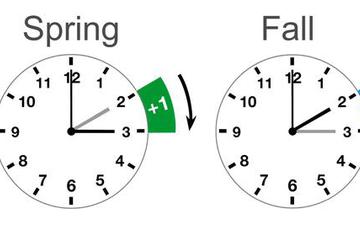Clubhouse能否被復制?面對負累與未知,誰會跑出來?

歡迎關注“創事記”的微信訂閱號:sinachuangshiji
文/趙衛衛
來源:藍洞商業(ID:value_creation)
原標題:Clubhouse能否被復制?
相比于美國Clubhouse被贊美為“一個更具思想性和更少受憤怒驅動的社交網絡”,Clubhouse的中國學徒們更像一個個溫熱的炕頭,等待前來嘮嗑的老鄉們。
“‘對話吧’大概會在3月20日重新上架。”深夜的“對話吧”里,有人給出了自己的判斷。
他沒有說出理由,故意賣了一個關子,但很快就有人猜出答案:3.15國際消費者權益日,是一個令各方企業都忌憚的敏感時期。過了這個敏感期,才會有更進一步的可能性。
過去的一個月里,Clubhouse這款多人在線語音聊天產品激發了眾多“中國學徒”:映客旗下的“對話吧”、36氪旗下的“Capital Cofffe”、小米復活的“米聊”等先后下場試水。
無一例外,它們都是對Clubhouse像素級別的山寨:語音聊天,選擇興趣房間,舉手參與,聊完即走、不留沉淀。
但隨著Clubhouse在國內被封禁,它的中國學徒們也陷入“半地下”的尷尬境地:一場投資大V們的帶貨直播后,“對話吧”被下架,官方解釋是技術調整;Capital Cofffe依然沒有通過IOS審核,是一個未受信任的企業級開發者產品;新米聊也在內測,距離它上一次“死亡”僅僅一周,能否借著Clubhouse的形式“還魂”,仍是一個未知數。
在差異化的競爭還未顯露之前,同質化的產品模仿是Clubhouse中國學徒們的常態。
相比于美國Clubhouse被贊美為“一個更具思想性和更少受憤怒驅動的社交網絡”,Clubhouse的中國學徒們更像一個個溫熱的炕頭,等待前來嘮嗑的老鄉們。
炕頭上,聊的是家長里短,關心糧食和蔬菜,都是熟絡的人;而在“對話吧”等產品里,你與蒙面的陌生人暢聊比特幣、盈利模式、運營技巧,話題千奇百怪,行業興趣人人不一,相同的卻是,幾乎每個人的用戶簡介里,都備注了自己的微信ID。
即便你可以在聊天的房間里關注對方,但“加個微信”是房間里出現的高頻詞匯,畢竟純語音還是限制了用戶之間溝通表達場景。
在顯著的商業盈利模式未被實現之前,發展私域流量,成為“炕頭樂”們的最顯著特征。
誰會跑出來?
連續三個晚上,從10點到凌晨1點,夏宏文都在主持“對話吧”的一個房間。他從事TMT領域投后管理咨詢服務,對脈脈和Linkedin頗為熟絡,工作內容就是“找人找錢找方向”。
主持人是房間的話題制定者和主持者,夏宏文要負責維護這個房間的發言秩序。房間人數最高時達到數十人,討論的話題包括在線教育、企業服務等等,這一晚,房間的名字叫“創投夜話:CH中國版的盈利模式”。

“奉總來了”,夏宏文注意到映客創始人奉佑生進了房間,雖然他們并不認識,而且奉佑生也沒有發言。
房間里的話題依然熱烈,從CH中國版是否適合招聘這個應用場景,到音頻內容的監管政策方法,房間里的話題不斷跳轉,夏宏文在中間穿針引線,他認為“對話吧”作為CH的中國版取得了先發優勢,但現階段定義它為時尚早,后面“高速高質量的增長才更為重要”。
夏宏文把“對話吧”定義為一個“超級流量入口”,刷到金沙江創投董事總經理朱嘯虎朋友圈里的邀請海報之后,他開始玩起了“對話吧”。幾天之后,他在“對話吧”里有400多粉絲,通過了幾十個人微信的申請。
在“對話吧”首次大咖對話中,朱嘯虎、昆侖萬維CEO周亞輝、華興資本董事總經理杜永波、復旦大學副教授蔣昌建上線交流“在中國能做成一個Clubhouse嗎?”,吸引了1800多人線上圍觀。
夏宏文提問,“對話吧”的粉絲和抖音的粉絲有什么區別?
朱嘯虎的回答大概是,相比于抖音中心化的流量分發機制,“對話吧”更像是私域流量,粉絲和KOL之間的鏈接更強。而另外一點則是,“群體之間的交互更多,內容不隨著話題延伸裂變,這是一種網狀結構的群體智慧,而不是KOL單一輸出。”
夏宏文對主持“對話吧”房間的熱衷,與映客官方沒有關系。在他看來,CH的中國版吸引了眾多創業者和投資人加入其中,這種群聊激發了更多想法和感受,也彌補了認知上的欠缺。
半夜一點,奉佑生早已經不在房間里,“對話吧”里的氣氛開始冷淡,在這個陌生人圍觀的線上,有人談到,“對話吧”代表著映客的某種焦慮,“映客還沒有現象級的產品”,但這個話題也點到為止。
言外之意誰都清楚,映客作為曾經的“直播第一股”,如今業務單一,已經被抖音、快手遠遠甩在身后。即便映客豪言要拿出40億打造CH中國版,社交產品的競爭殘酷性和難度也非一日之功。
預測Clubhouse中國學徒們的競爭趨勢,依然是一件困難的事情。現在,被下架之后的“對話吧”依然在悄悄更新版本,它的新功能包括用戶可以提前預約感興趣的話題房間等等,但這依然是在模仿Clubhouse。
“就像梅花創投吳世春說,不到100萬用戶,誰也別談先發優勢。”夏宏文說,Clubhouse中國學徒們還處在同一個起跑線,未來大概率是會跑出幾家,“那一定是產品和運營能力強的公司,比如頭條”。
負累與未知
就像Clubhouse的中國學徒們必將面臨騰訊或是字節跳動系的競爭,在美國,Clubhouse也面臨著Facebook、Twitter的競爭。Twitter已經開始了群組音頻聊天功能Spaces的內測,Facebook也開始開發類似Clubhouse的產品。
Clubhouse仍舊在著力挖掘內容優勢提高社區的豐富程度,其已經開始試驗通過打賞、票務和訂閱來為平臺上的創作者提供資助。就像朱嘯虎提到,音頻社交產品的根基是內容質量,“驅動機制上,光靠興趣是沒有用的,必須給予用戶賺錢的機會。”
但伴隨用戶病毒式激增,危險也更加顯而易見。
在美國,Clubhouse遭遇的問題是安全漏洞。Clubhouse負責的是用戶體驗,而后端的業務支持依賴于中國上海的服務商聲網Agora。在2021年2月中旬,已經有黑客通過系統程序,把多個房間內的私人聊天內容傳輸到第三方網站上,這與平臺上聊完即走、沒有音頻文字存檔的設計背道而馳。
某種程度上,Clubhouse迅速躥紅成長,也正因為其處在內容監管的縫隙中,當Facebook、Twitter等主流社交平臺早已開始加大內容審核力度,Clubhouse未來同樣會受到越來越多的監管壓力。
這個道理,同樣適用于中國的Clubhouse學徒們,在商業模式、用戶增長、社區內容等等問題之前,平臺責任和監管政策是首要面臨的問題。
相比視頻直播一對多的審核方式,Clubhouse的多對多、純語音信息的方式,無疑增大了內容審核的成本壓力。目前商湯等人工智能公司提供的語音內容審核檢測精度大于90%,即便如此,人工審核語音信息也是中國Clubhouse學徒們的壓力所在。
而對于用戶來說,毫無疑問,Clubhouse激發了人們的表達欲,它為志同道合的一批人提供了聚集方式,其中蘊含著無限的可能性。樂觀者們期待它,有望成為Facebook,Instagram,Twitter,LinkedIn和YouTube之后的“第六網絡”。
一些借助Clubhouse發展私域流量的個體已經顯現光芒。比如在遙遠的島國毛里求斯,一個叫曼蘇(Axel Mansoor)的28歲歌手,他在房間內唱歌,在不同的房間內穿梭,分享自己在中國、印度和奧地利等地巡演和旅行的故事,他已經發展了8萬多粉絲。
即便Clubhouse的邀請制讓很多人無法參與其中,延遲效果也不能音樂合奏成為可能。但曼蘇說,“Clubhouse傳達了我的本質。”
這一切,顯然都是規模化效應之后才出現的結果。
對于中國Clubhouse學徒來說,他們能否孕育更多的可能性,顯然還是未知數,這取決于它們的“炕頭”能否維持住一個安全的溫度。

(聲明: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新浪網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