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普林小虎隊
編者按
2021年10月1日是楊振寧先生的百歲華誕。(楊先生實際年齡99歲,虛歲一百,官方文件上的生日是9月22日。)我們特發(fā)表此文,為楊先生賀。
撰文|倪憶
楊振寧先生(1922.10.1— )從來不認(rèn)為自己是一位數(shù)學(xué)家。事實上,楊先生曾經(jīng)說過:“現(xiàn)今只有兩類數(shù)學(xué)著作。一類是你看完了第一頁就不想看下去了, 另一類是你看完了第一句話就不想看下去了。”然而,楊振寧先生對現(xiàn)代數(shù)學(xué)有著廣泛而深遠(yuǎn)的影響。在20世紀(jì)后半葉的物理學(xué)家里,恐怕只有威騰(Edward Witten,1951— )對數(shù)學(xué)的影響能夠跟楊先生相提并論。本文試圖對楊先生的數(shù)學(xué)貢獻(xiàn)作一些簡單介紹。需要說明的是,這里涉及到許多非常深刻的數(shù)學(xué),作者本人了解的僅僅是其中一小部分,錯漏之處在所難免,希望方家指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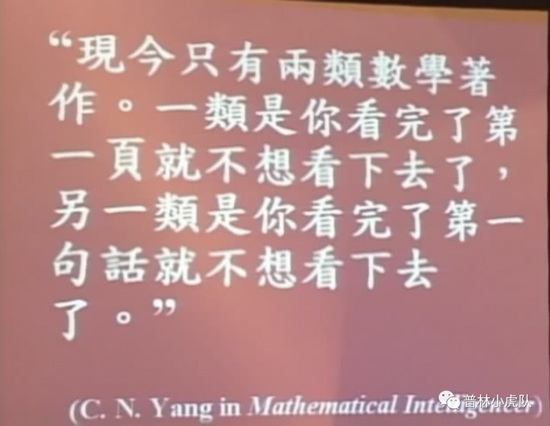
楊-米爾斯理論
楊振寧先生最重要的成果是楊-米爾斯理論(Yang-Mills theory),這是一種非阿貝爾規(guī)范場論(nonabelian gauge theory)。規(guī)范場論的思想在麥克斯韋(James Maxwell,1831—1879)的電磁學(xué)理論里便已經(jīng)出現(xiàn)。1918年,外爾(Hermann Weyl,1885—1955)試圖統(tǒng)一電磁場和引力場,在場論中引入了一個尺度因子。這個尺度因子帶來了一定的冗余度,需要選定一個“規(guī)范”(gauge)來剔除此冗余度。外爾的這一嘗試并未成功,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1879—1955)高度評價其中的數(shù)學(xué),卻強(qiáng)烈批評其中的物理。[1]

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在四十年代的一次會議,其中有愛因斯坦(左三)和外爾(右二)(圖源:高等研究院檔案)
外爾最初引入的尺度因子是正實數(shù)。量子力學(xué)興起后,外爾在1929年修改了他的規(guī)范場論,把尺度因子改成模長為1的復(fù)數(shù),用以描述電磁場。福克(Vladimir Fock,1898—1974)和倫敦(Fritz London,1900—1954)等人也在這一時期作出了類似發(fā)現(xiàn)。1941年,泡利(Wolfgang Pauli,1900—1958)把規(guī)范場理論普及給物理學(xué)界。
在數(shù)學(xué)里,所有模長為1的復(fù)數(shù)組成一個群U(1)。這個群被稱作外爾規(guī)范場論里的規(guī)范群。如果一個群里的乘法是可交換的,這個群就被被稱作阿貝爾群,反之就是非阿貝爾群。例如大多數(shù)矩陣群都是非阿貝爾群,因為乘法交換律對于矩陣乘法不成立。外爾理論里的規(guī)范群是阿貝爾群,所以外爾理論是一個阿貝爾規(guī)范場論。
我們知道,自然界中有四種基本力:電磁力、弱相互作用、強(qiáng)相互作用、萬有引力。外爾等人的工作把電磁力用U(1)規(guī)范場論來描述,而萬有引力的物理理論則是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1954年,楊振寧和米爾斯(Robert Mills,1927—1999)把規(guī)范場論里的規(guī)范群從U(1)改成二階正交酉矩陣群SU(2),建立了第一個非阿貝爾規(guī)范場論。楊振寧和米爾斯最初想用這一理論來描述強(qiáng)相互作用,但這并不正確。經(jīng)過后來許多物理學(xué)家的努力,SU(2)規(guī)范場論被成功地用于描述弱相互作用。而強(qiáng)相互作用則需要使用規(guī)范群為SU(3)的規(guī)范場論,通常也被稱為楊-米爾斯理論。

1999年,楊振寧與米爾斯在楊振寧退休慶祝會議上(圖源:American Institute of Physics)
統(tǒng)計學(xué)家斯蒂格勒(Stephen Stigler,1941— )曾提出一個“斯蒂格勒定律”,即“沒有一個科學(xué)發(fā)現(xiàn)是以最初發(fā)現(xiàn)者的名字來命名”。斯蒂格勒定律本身就符合這一定律,因為斯蒂格勒認(rèn)為這個定律是默頓(Robert Merton,1910—2003)首先提出的。楊-米爾斯理論也符合斯蒂格勒定律,——泡利在1953年就得到了一個類似的理論。日本物理學(xué)家內(nèi)山龍雄(1916—1990)為了統(tǒng)一萬有引力和電磁力,在1954年獨(dú)立提出了非交換規(guī)范場論。他曾在京都大學(xué)作報告,但沒有得到聽眾的積極回應(yīng)。得知楊-米爾斯的工作后,內(nèi)山龍雄在1955年把自己的論文修改成為一個更廣泛的規(guī)范場論,并在1956年發(fā)表。比楊振寧和米爾斯稍晚,薩拉姆(Abdus Salam,1926—1996)的學(xué)生蕭(Ronald Shaw,1929—2016)在1955年也獨(dú)立發(fā)現(xiàn)了楊-米爾斯理論。
盡管泡利、內(nèi)山、蕭都獨(dú)立于楊振寧和米爾斯得到了非交換規(guī)范場論,但楊振寧和米爾斯毫無疑問應(yīng)當(dāng)獲得最大的榮譽(yù)。泡利和蕭的工作都沒有發(fā)表,因為他們對其中的物理圖景不甚明了。內(nèi)山發(fā)表論文在楊-米爾斯之后,且受到楊-米爾斯的影響。只有楊振寧和米爾斯將這個尚存瑕疵的理論率先發(fā)表出來,讓后來者得以在此基礎(chǔ)上進(jìn)行研究。一個經(jīng)常被提到的故事是,當(dāng)楊振寧在普林斯頓作楊-米爾斯理論的報告時,臺下的泡利不停地問他非阿貝爾規(guī)范玻色子的質(zhì)量是什么。泡利曾經(jīng)深入研究過這一問題,知道質(zhì)量應(yīng)該是零,而這是不可能的。楊振寧回答說他不知道,但泡利一再追問。楊振寧認(rèn)為泡利的敵意過重,干脆停止演講坐到臺下,場面一時十分尷尬。最后,奧本海默(J。 Robert Oppenheimer,1904—1967)說,“我們應(yīng)該讓楊振寧繼續(xù)講。”楊振寧才回到講臺上,而泡利也沒有問更多的問題。[2] 楊-米爾斯理論中的質(zhì)量問題直到六十年代才通過希格斯機(jī)制得到解決。

1945年,泡利在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慶祝他的45歲生日(圖源:CERN)
楊振寧和米爾斯建立了楊-米爾斯理論的數(shù)學(xué)形式,其物理應(yīng)用則應(yīng)歸功于后來者。然而,與楊-米爾斯理論有關(guān)的數(shù)學(xué)成為現(xiàn)代數(shù)學(xué)里一個重要組成部分。1969年,楊振寧在紐約州立大學(xué)石溪分校講授一門廣義相對論課程。一天,他在黑板上寫下廣義相對論所需要用到的黎曼曲率張量公式,突然發(fā)現(xiàn)這個公式很像楊-米爾斯理論里的一個公式。他十分震驚,便去請教數(shù)學(xué)系主任西蒙斯(James Simons,1938— )。西蒙斯告訴他這兩個公式都是纖維叢(fiber bundle)上的聯(lián)絡(luò)(connection)。楊振寧被這一美妙的聯(lián)系深深地震撼了。[3]

楊振寧與西蒙斯(圖源:The Stony Brook Dialogues in Mathematics and Physics)
1975年,楊振寧同吳大峻(1933— )發(fā)表一篇論文,把纖維叢的數(shù)學(xué)語言翻譯為楊-米爾斯理論的物理語言,引發(fā)了數(shù)學(xué)界和物理學(xué)界對彼此工作的濃厚興趣。這就是著名的吳-楊字典(Wu-Yang dictionary)。事實上,關(guān)于纖維叢與楊-米爾斯理論的關(guān)系,在吳-楊字典之前就有一些人提到。例如赫爾曼(Robert Hermann, 1931—2020)在1970年的一本專著中對此有詳細(xì)闡述。但此類工作沒有產(chǎn)生吳-楊字典那樣的影響,這或許也可以算作斯蒂格勒定律的一個例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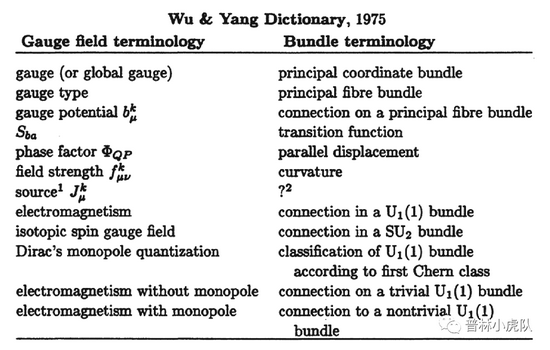
吳-楊字典(圖源:I。 M。 Singer, Some problems in the quantization of gauge theories and string theories)
七十年代后期,辛格(Isadore Singer,1924—2021)把吳-楊字典介紹給數(shù)學(xué)界,引發(fā)了數(shù)學(xué)家們學(xué)習(xí)楊-米爾斯理論的熱潮。一大批嶄新的數(shù)學(xué)工作得以誕生,為數(shù)學(xué)發(fā)展提供了新的動力。以下簡要介紹其中一部分。
楊-米爾斯理論中出現(xiàn)了一個偏微分方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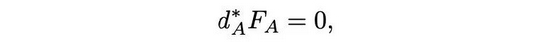
被稱為楊-米爾斯方程。1974年,楊振寧訪問其父楊武之(1896—1973)生前任教的復(fù)旦大學(xué)。他同谷超豪(1926—2012)、胡和生(1928— )等人談起楊-米爾斯理論中的數(shù)學(xué)問題。雙方展開合作,在國際上率先對楊-米爾斯方程進(jìn)行研究,解決了該方程的許多基本問題。

1974年,谷超豪(左一)、胡和生(左二)與楊振寧開始合作研究規(guī)范場論(圖源:中國科學(xué)報)
1977-1978年,阿蒂亞(Michael Atiyah,1929—2019)、希欽(Nigel Hitchin,1946— )和辛格證明了四維球面上楊-米爾斯方程的解的模空間是一個流形,并用指標(biāo)定理計算了其維數(shù)。1978年,阿蒂亞、希欽、德林菲爾德(Vladimir Drinfeld,1954— )、馬寧(Yuri Manin,1937— )四人合寫一篇論文,完全確定了這一模空間。
1982年,烏倫貝克(Karen Uhlenbeck,1942— )證明了楊-米爾斯方程解的許多基本性質(zhì),包括(四維的)可去奇點(diǎn)定理和(任意維數(shù)的)緊性定理。田剛(1958— )和陶哲軒(1975— )后來把可去奇點(diǎn)定理推廣到了高維。

烏倫貝克于1969年在伯克利(圖源:Oberwolfach Photo Collection)
1982年,陶布斯(Clifford Taubes,1954— )發(fā)現(xiàn)了一種新的構(gòu)造楊-米爾斯方程解的方法,對于一大類四維流形證明了解的存在性。
復(fù)流形上楊-米爾斯方程的研究始于阿蒂亞和博特(Raoul Bott,1923—2005)在八十年代初的工作。小林昭七(1932—2012)和希欽猜測復(fù)流形上楊-米爾斯方程的解跟向量叢的穩(wěn)定性有關(guān),這一猜想被唐納森(Simon Donaldson,1957— )、烏倫貝克和丘成桐(1949— )解決。受此啟發(fā),丘成桐對復(fù)流形的凱勒-愛因斯坦度量作出類似猜想。田剛和唐納森進(jìn)一步闡述了丘成桐的猜想,引入了K-穩(wěn)定性的概念,在復(fù)幾何和代數(shù)幾何領(lǐng)域起到了核心作用。

1982年,丘成桐、阿蒂亞和希欽(圖源:Oberwolfach Photo Collection)
希欽在1987年定義了一維復(fù)流形上的希格斯叢,并研究了其上的楊-米爾斯方程。辛普森(Carlos Simpson,1962— )把希欽的工作推廣到了高維。希格斯叢是近年來幾何拓?fù)漕I(lǐng)域的研究熱點(diǎn),并且在數(shù)論和表示論中得到了出乎意料的應(yīng)用。吳寶珠(1972— )使用希欽的工作證明了朗蘭茲綱領(lǐng)中的“基本引理”,并因此獲得2010年菲爾茲獎。1986年菲爾茲獎得主法爾廷斯(Gerd Faltings,1954— )開創(chuàng)了p進(jìn)數(shù)域上希格斯叢的研究。卡普斯金(Anton Kapustin,1971— )和威騰則使用希欽的工作(及其推廣)來研究幾何朗蘭茲綱領(lǐng)。
楊-米爾斯方程最著名的數(shù)學(xué)應(yīng)用是在低維拓?fù)漕I(lǐng)域。1983年,在烏倫貝克和陶貝斯工作的基礎(chǔ)上,唐納森使用楊-米爾斯方程研究四維流形的微分拓?fù)洌〉昧肆钊梭@異的結(jié)果。把唐納森和弗里德曼(Michael Freedman,1951— )的工作結(jié)合起來,能夠證明四維空間R^4上有怪異的微分結(jié)構(gòu),而這一點(diǎn)對其余維數(shù)的歐氏空間不成立。唐納森后來進(jìn)一步發(fā)展了他的理論,定義了光滑四維流形的不變量。唐納森因此獲得1986年菲爾茲獎。

2009年,唐納森(右二)和陶貝斯(右三)獲得邵逸夫數(shù)學(xué)獎(圖源:中國政府網(wǎng))
1988年,弗洛爾(Andreas Floer,1956—1991)把唐納森理論發(fā)展到了三維流形上,定義了瞬子同調(diào)論。1998年,唐納森和他的學(xué)生托馬斯(Richard Thomas)使用SU(4)規(guī)范場論來研究卡拉比-丘三維復(fù)流形。2006年菲爾茲獎得主奧昆科夫(Andrei Okounkov,1969— )和他的合作者們對唐納森-托馬斯理論有重要貢獻(xiàn)。
唐納森理論的思想如今在低維拓?fù)洹⑿翈缀巍⒋鷶?shù)幾何、復(fù)幾何等許多領(lǐng)域里都占據(jù)著主導(dǎo)地位,其后續(xù)發(fā)展包括格羅莫夫-威騰理論、塞伯格-威騰理論等等,盡管楊-米爾斯方程在這些理論里已經(jīng)不再出現(xiàn)。
楊-米爾斯方程在低維拓?fù)淅锏牧硗庖粋€應(yīng)用跟瓊斯多項式有關(guān),這是瓊斯(Vaughan Jones,1952—2020)在1984年發(fā)現(xiàn)的一個新的紐結(jié)不變量。威騰在1989年指出,瓊斯多項式可以用楊-米爾斯理論來解釋。威騰的思想被雷希蒂欣(Nicolai Reshetikhin,1958— )和圖拉耶夫(Vladimir Turaev,1952— )發(fā)展為嚴(yán)格的數(shù)學(xué)理論,可以用來構(gòu)造一般三維流形的不變量。近二十年來,瓊斯多項式的一個推廣——霍瓦諾夫同調(diào)論(Khovanov homology)——成為低維拓?fù)淅锏难芯繜狳c(diǎn)。威騰同樣用楊-米爾斯理論給出了霍瓦諾夫同調(diào)論的一種解釋,引發(fā)了許多數(shù)學(xué)家的關(guān)注。
楊-巴克斯特方程
楊振寧另外一項對數(shù)學(xué)有深遠(yuǎn)影響的工作是楊-巴克斯特方程。這是一個形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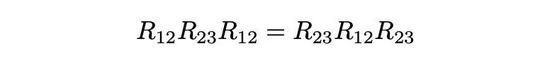
的矩陣方程,涉及了非線性可積物理模型的嚴(yán)格解。
楊-巴克斯特方程最早可以追溯到昂薩格(Lars Onsager,1903—1976)在1944年關(guān)于二維伊辛模型的工作,其中使用了星形-三角形方程。[4] 1963年,UCLA的一名博士生麥奎爾(James B。 McGuire,1934—2019)在研究一維量子多體問題時發(fā)現(xiàn)了類似的矩陣方程。楊振寧在1963年訪問UCLA時,跟麥奎爾討論了一維量子多體問題。當(dāng)時楊振寧已經(jīng)是名滿天下的諾貝爾獎得主,而麥奎爾僅僅是一個博士尚未畢業(yè)的無名小卒,然而楊振寧并未因此輕視麥奎爾的工作。受到麥奎爾的啟發(fā),楊振寧在1967年和1968年的兩篇論文里提出了現(xiàn)今形式的楊-巴克斯特方程。后來巴克斯特(Rodney Baxter,1940— )在1971年和1972年的兩篇統(tǒng)計力學(xué)論文里也獨(dú)立發(fā)現(xiàn)了此方程。

楊振寧與巴克斯特在楊振寧退休慶祝會議上(圖源:Symmetry and Modern Physics - Yang Retirement Symposium, 1999)
七十年代末,法捷耶夫(Ludvig Faddeev,1934—2017)領(lǐng)導(dǎo)的蘇聯(lián)數(shù)學(xué)物理學(xué)派將這一方程命名為楊-巴克斯特方程,并深入研究其在數(shù)學(xué)和物理里的應(yīng)用。受他們工作的影響,德林菲爾德和神保道夫(1951— )開始了“量子群”的研究。德林菲爾德甚至將一類量子群命名為“楊代數(shù)”(Yangian),以紀(jì)念楊振寧的貢獻(xiàn)。
楊-巴克斯特方程可以看作是數(shù)學(xué)中“辮群”的一個基本關(guān)系,能夠用如下“辮子”的圖像來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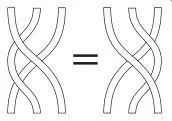
上圖中的辮子關(guān)系在紐結(jié)的瓊斯多項式里起到重要作用。圖拉耶夫發(fā)現(xiàn),包括瓊斯多項式在內(nèi)的許多紐結(jié)不變量都可以從楊-巴克斯特方程的解得到。雷希蒂欣和圖拉耶夫進(jìn)一步的工作則是使用量子群來構(gòu)造紐結(jié)不變量。

西蒙斯幾何與物理中心的墻上鐫刻著一些基本的物理公式,圖中左下角即楊-巴克斯特方程(圖源:西蒙斯幾何與物理中心)
1990年四位菲爾茲獎得主中,德林菲爾德、瓊斯和威騰的(部分)獲獎工作都跟楊-米爾斯理論和楊-巴克斯特方程有密切關(guān)系。森重文(1951— )是一位代數(shù)幾何學(xué)家,他的獲獎工作跟物理沒有直接聯(lián)系。近年來許晨陽(1981— )等人的工作把森重文開創(chuàng)的極小模型綱領(lǐng)同K-穩(wěn)定性結(jié)合起來,而K-穩(wěn)定性很大程度上是受楊-米爾斯理論啟發(fā)而建立起來的。

1990年四位菲爾茲獎得主,左起:威騰、森重文、瓊斯、德林菲爾德(圖源:ICM2002.org.cn)
李-楊單位圓定理
李政道與楊振寧在1952年發(fā)表了兩篇統(tǒng)計力學(xué)方面的論文,其中證明了某一類配分函數(shù)的零點(diǎn)都在單位圓上,這就是著名的李-楊單位圓定理。愛因斯坦對這一工作非常感興趣,邀請李楊二人到他的辦公室去討論了一個半小時。[5]李-楊定理依賴于一個純數(shù)學(xué)結(jié)果,即某一類多項式所有零點(diǎn)都在單位圓上。為了證明這一結(jié)果,李楊二人翻閱了哈代(G。 H。 Hardy,1877—1947)、李特爾伍德(John Littlewood,1885—1977)、波利亞(George Pólya,1887—1985)所著的《不等式》一書,還咨詢了馮·諾伊曼(John von Neumann,1903—1957)和塞爾伯格(Atle Selberg,1917—2007)等同事。卡茨(Mark Kac,1914—1984)當(dāng)時在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訪問,他聽到李楊的問題后,立刻想到了波利亞一篇關(guān)于黎曼假設(shè)的論文,并用其中的方法證明了李楊所需結(jié)果最簡單的情形。卡茨將此事告知了李楊。受此啟發(fā),楊振寧和李政道繼續(xù)研究了幾個星期,終于用卡茨的方法以及數(shù)學(xué)歸納法證明了最廣泛的情形。[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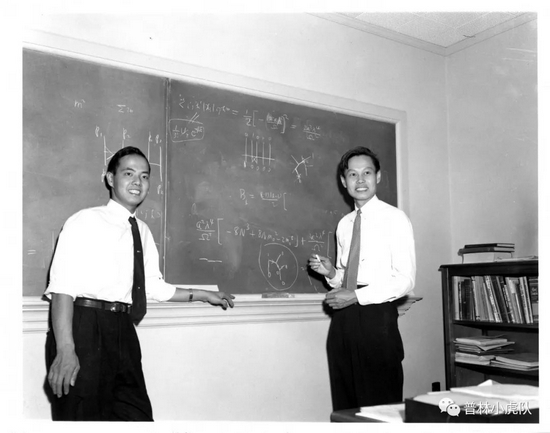
1957年,李政道和楊振寧在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圖源:IAS Archives)
李-楊單位圓定理是統(tǒng)計力學(xué)里的重要工作,但它對數(shù)學(xué)的影響遠(yuǎn)不能同楊-米爾斯理論和楊-巴克斯特方程相提并論。然而,這個定理的敘述跟黎曼假設(shè)非常相像。如果作一個變量替換,就能把李-楊定理敘述成:某一類配分函數(shù)的零點(diǎn)都在虛軸上。黎曼假設(shè)說的是黎曼ζ函數(sh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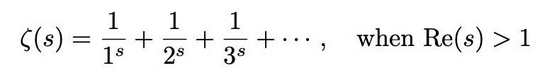
的非平凡零點(diǎn)都在直線Re(s)=1/2上。故此,有一部分?jǐn)?shù)學(xué)家希望能夠把黎曼ζ函數(shù)表示為某個物理系統(tǒng)的配分函數(shù),從而研究黎曼假設(shè)。(用物理方法研究黎曼假設(shè)是當(dāng)前的一個流派,這方面更常見的工作是將量子力學(xué)與黎曼ζ函數(shù)聯(lián)系起來。)
楊振寧的純數(shù)學(xué)工作
楊振寧曾多次表示,如果自己不做物理,一定會去做數(shù)學(xué)。[5,7] 事實上,除了數(shù)學(xué)物理方面的眾多成果以外,楊振寧也發(fā)表過一些純數(shù)學(xué)論文。這些工作對于楊振寧這樣的科學(xué)巨人來說無足輕重。然而,從這些論文中可以看出,跟許多其他理論物理學(xué)家不同,楊振寧也可以有跟數(shù)學(xué)家一樣的品味,使用跟數(shù)學(xué)家一樣的語言。楊振寧發(fā)表的第一篇論文就是純數(shù)學(xué)論文。這是他在西南聯(lián)大時寫的,題為“On the uniqueness of Young‘s differentials”(Young微分的唯一性),1944年發(fā)表在《美國數(shù)學(xué)會通報》(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Mathmatical Society)上。這篇論文的水平不高,楊振寧對它也很不滿意。楊振寧最初僅僅是把它當(dāng)作學(xué)習(xí)微積分的課外練習(xí),幾年后才在授課老師曾遠(yuǎn)榮(1903—1994)的建議下投寄出去發(fā)表。[8]楊振寧的父親楊武之教授在芝加哥大學(xué)獲得博士學(xué)位,歸國后任教于清華大學(xué)數(shù)學(xué)系,是中國數(shù)論研究的先驅(qū)。在楊武之的博士論文里,他考慮了華林問題的一個變種:求最小的k,使得任何一個自然數(shù)能夠表示為最多k個“金字塔數(shù)”之和。這里的“金字塔數(shù)”指形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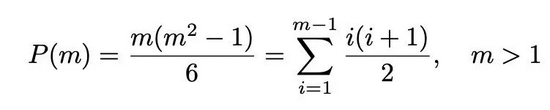
的數(shù)。楊武之證明了k不超過9,這一結(jié)果后來被人改進(jìn)為8。

1993年,楊振寧和鄧越凡(1962— )用計算機(jī)研究了這一問題,發(fā)現(xiàn)十億以內(nèi)的自然數(shù)都能表示為至多5個金字塔數(shù)之和,并且其中足夠大的數(shù)表示為至多4個金字塔數(shù)之和。據(jù)此,他們猜想足夠大的自然數(shù)都能表示為至多4個金字塔數(shù)之和。他們進(jìn)一步猜想了能表示為至多k個金字塔數(shù)之和的自然數(shù)的個數(shù)的漸進(jìn)公式。
楊振寧與陳省身
陳省身(1911—2004)和楊振寧兩位先生是二十世紀(jì)華人科學(xué)家中的翹楚。他們兩人私交甚篤,在學(xué)術(shù)上也有密切聯(lián)系。陳省身1930-1934年間在清華大學(xué)擔(dān)任助教和攻讀研究生,同楊武之教授有師生之誼。陳省身與夫人鄭士寧的婚事就是楊武之夫婦介紹的。陳省身曾多次到楊武之家中吃飯,見到過年僅八歲的楊振寧,但楊振寧對陳省身并無印象。[3,9] 后來楊振寧在西南聯(lián)大求學(xué)期間,曾經(jīng)選修過陳省身開設(shè)的多門課程,包括微分幾何。[3]
陳省身是纖維叢和聯(lián)絡(luò)理論的主要推動者。他的陳-韋伊理論把楊-米爾斯方程中的曲率項同陳示性類聯(lián)系起來,而陳-西蒙斯理論也跟楊-米爾斯理論密不可分。1975年,理解了楊-米爾斯理論與纖維叢的關(guān)系后,楊振寧驅(qū)車到陳省身家中,同他談起此事,說:“這既令我驚訝,也令我迷惑不解,因為你們數(shù)學(xué)家憑空夢想出這些概念。”陳省身當(dāng)即提出異議:“非也,非也,這些概念并非是憑空夢想出來的,它們既是自然的,也是實在的。”[3]

陳省身先生1985年在南開大學(xué)創(chuàng)建了南開數(shù)學(xué)研究所,他邀請楊振寧于1986年在所內(nèi)建立了理論物理研究室。經(jīng)楊振寧推薦,葛墨林(1938— )具體負(fù)責(zé)理論物理研究室的工作。這一研究室主要的研究方向便是與楊-米爾斯理論和楊-巴克斯特方程相關(guān)的數(shù)學(xué)。
楊振寧在七十年代寫下一首詩《贊陳氏級》,在數(shù)學(xué)與物理學(xué)界廣為流傳:
天衣豈無縫,匠心剪接成。渾然歸一體,廣邃妙絕倫。造化愛幾何,四力纖維能。
千古寸心事,歐高黎嘉陳。
其中最后一句稱贊陳省身是可以與歐幾里得(Euclid,公元前3世紀(jì))、高斯(Carl Friedrich Gauss,1777—1855)、黎曼(Bernhard Riemann,1826—1866)、嘉當(dāng)(élie Cartan,1869—1951)并肩的幾何學(xué)家。
2002年,江才健出版了《楊振寧傳-規(guī)范與對稱之美》。陳省身先生也賦詩一首作為序言:
以詩代序
愛翁初啟幾何門,
楊子始開大道深。
物理幾何是一家,
炎黃子孫躋西賢。
注: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將物理釋為幾何。規(guī)范場論作成大道,令人鼓舞。
兩位大師盡管身處不同領(lǐng)域,但他們的偉大工作相得益彰,堪稱佳話。

楊振寧(攝影:鄧偉)
[參考文獻(xiàn)]
[1] 張?zhí)烊兀?/p>
外爾與楊振寧——物理的真與數(shù)學(xué)的美 | 量子群英會
[2] Mikhail Shifman,非阿貝爾規(guī)范場的起源與爭執(zhí):關(guān)于泡利與楊振寧的軼事
[3] 張奠宙,楊振寧如何看待數(shù)學(xué)與物理
[4] Helen Au-Yang and Jacques H。 H。 Perk, Onsager‘s Star-Triangle Equation: Master Key to Integrability, Advanced Studies in Pure Mathematics 19, 1989 Integrable Systems in Quantum Field Theory and Statistical Mechanics
[5] 劉鈍、王浩強(qiáng)訪問整理,愛因斯坦、物理學(xué)和人生——楊振寧先生訪談錄
[6] Mark Kac, Comments on G。 Pólya‘s “Bemerkung uber die integraldarstellung der Riemannschen zeta-funktion”
[7] 華東師范大學(xué)數(shù)學(xué)科學(xué)學(xué)院,楊振寧專程看望數(shù)學(xué)科學(xué)學(xué)院張奠宙先生
[8] 施郁,楊振寧對西南聯(lián)大的新回憶
[9] 陳省身,我與楊家兩代的因緣

“掌”握科技鮮聞 (微信搜索techsina或掃描左側(cè)二維碼關(guān)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