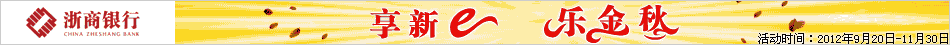90后富士康員工的自白:希望管理不那么簡單粗暴
富士康的新命題:“90后”工人時代到來
李娜
作為全球最大的電子產品代工廠,富士康以其極為出色的代工能力征服了全球合作伙伴,卻始終苦于沒有一套讓自己滿意的“員工解決方案”。
身為“90后”的一員,王大橋(化名)2010年來到富士康,成為深圳龍華廠區iPad 3生產線上的一名工人,平時的工作是把那些從各個地方運來的零件組裝起來,成為一臺完整的iPad 3。電池、主板、攝像頭、屏幕和外殼——這些零部件會按照不同的組,分配給工人進行流水作業。
“工作雖然枯燥一些,但是別的地方也許拿不到同樣的工資。”他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2010年6月份的時候他的底薪從900元上調到1200元,到了2010年底,他的底薪已經漲到了2000元,而到了今年3月份,底薪升至2350元。王大橋說,加上加班費,他每個月的收入可以達到4000元左右,一年下來,他可以用這些錢為家里置辦一些新的家具。而他周邊的工友,更多的屬于“及時享樂”型,每個月剩下的錢并不多。
據了解,目前在富士康中,“90后”的隊伍正在逐漸壯大。在富士康的基層員工中,“80后”、“90后”打工者,已經超過了85%。
富士康工會副主席曾經對外描述過他眼中三種典型的富士康年輕人:一種是家庭條件較好,出來不是為了掙錢,主要是看世界,在北京、上海、廣州這些大城市轉過一圈后,再回去成家立業。
另一種是家庭條件差,出來打工,把每年掙的錢都攢下來,3年攢到五六萬,回家蓋房結婚過日子。
還有一種有理想、有事業心,能吃苦,利用富士康提供的從專科到博士的培訓,實現自己的理想。
王大橋把自己歸類為第二種人,但除了掙錢,他更希望留在深圳。
“回到家里也不一定能適應,沿海城市還是有很大的優勢。”王大橋說,與他同鄉的工友回到家里后,找的工作發現環境沒有太大改善,工資倒是低了不少,“更重要的,待在家里很無聊。”
一深圳制造企業負責人對記者說,與老一代農民工不同,新生代農民工對精神層面的需求遠高于其父輩。不少新生代農民工渴望能“過得更多彩”,而家里的物質條件并不能滿足這些已經見過世面后的打工者。
但事實上,王大橋并不能掌握自己的命運。
“現在因為內遷的事情,很多事業群都在往內地搬遷,因為不愿意回去,很多人也選擇離開了富士康。”王大橋說。
跨部門實施支援是富士康所采取的成本管控的方式之一。“哪個部門訂單過剩,有多余的人力,就把這些多余的人力調配到其他部門進行支援,不再是某條生產線的專門工人。”王大橋說,這樣的調配在今年變得很頻繁,一個地方還沒有呆熟悉就去另外一個地方了,有的更是直接調往外地。
“這也是引起內部矛盾的一個原因。”王大橋告訴記者。在蘋果生產線沒有那么忙的時候,王大橋和工友曾經被安排到深圳富士康觀瀾廠區進行過短期的諾基亞(微博)手機生產組裝工作。
“過去長期做iPad產品,對手機的組裝還是有一些生疏,到了不同的組后,對方會進行一些指導,但是指導的時候因為語氣等問題,會產生一些小的矛盾,積聚久了就容易出事。”王大橋說。
對此,富士康管理層一內部人士對本報記者說,富士康試圖改變這樣的情況,但磨合中往往還是會忽略一些問題。
“目前廠區內大部分的員工都是85后和90后,對于他們來說,富士康是一份工作,但也許也是他們第一次真正意義上去認識社會、去接觸社會。更重要的,不能用原來的管理模式去要求他們。”上述內部人士說,現在的工人通過“短工化”、“旅游式”的打工或者父輩打工的積累基本能夠滿足生存需求,但他們也有更高的追求,希望能夠平等地享受城市生活,最終在城市生根。
王大橋說,雖然這里有標準的足球場,有三甲醫院,有企業大學,有情侶座、卡座、包廂座的網吧,但自己都用不上。
在深圳的富士康廠區可以看到,雖然人數和一個城市類似,但其他指標卻遠遠低于城市。“城市里最基本的元素是家庭,但這里卻是單個的個人。城市里有占地面積都很高的社會化設施,而這里雖然有網吧、游泳池等諸多公共設施,卻難以滿足幾十萬人的使用。”一學者評論道。
王大橋告訴記者,對于自己來說,加班時間是非常重要的,直接影響到工資,而這個是他來深圳打工的目的。但除此之外,他希望廠區的管理能夠不那么簡單、粗暴,多一些“人文關懷”,但具體怎么做,他表示自己也說不清楚。
他對記者說,事實上,“服從命令”是每個來到富士康的工人所必須認同的基本規定,不愿意聽從只能辭職。
市總工會曾經如此批評過富士康在管理方面存在漏洞和不足:新生代農民工對企業現有的管理模式、制度和方式方法有要求變革的強烈沖動,企業本就應該及時加以調整和改變,不斷適應這種變化,才能避免不必要的傷害。
一華南高校教授對記者表示,雖然郭臺銘為富士康設計了種種完美制度,甚至會教管理層怎樣提升員工滿意度、怎樣與員工交流等眾多細節,但富士康的“管理鴻溝”還是因為年齡、閱歷、秉性、生活方式等差異而不可逾越。
“但富士康只是一個企業,不能承擔一個城市的社會職能。”此前,富士康相關發言人說。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