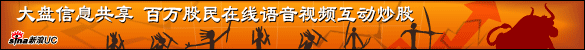不支持Flash
|
|
|
|
汪暉:現代化本身需要被反思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8月04日 14:51 經濟觀察報
本報記者 馬國川 北京報道 7月11日,三聯書店正式宣布,汪暉不再擔任《讀書》執行主編。這一人事更迭迅速成為媒體焦點。《讀書》無小事,從1979年到2007年,它的創辦、發展和嬗變,可以幫我們辨識出近30年來中國社會結構和思想形態的大變動。如今,這份人稱在最近10年蛻變為“新左派”主要言論陣地的雜志,是要回到“以前的樣子”,還是要完成一次官僚化的收編?對此,人們作出了各種各樣的解讀。 我們堅定地支持市場取向的改革,認同改革開放,對汪暉主編之《讀書》所倡導的一些價值取向并不贊成——我們從來不認為關懷窮人是“左派”的專利,在倡導社會公正上,“右派”在道德上從來不低于“左派”;恰恰是為了公平問題,“右派”才強調市場經濟的力量——但是,思想觀念之間的分化與沖突,是構成現代社會的一個重要因素,知識分子階層本是一個相對分化的領域,而不應一聲令下,步調一致,或者因為我是多數、我是主流,少數派就得閉嘴。因此我們專訪汪暉先生,就一些有爭議的話題進行了交流。 我們認為,“新左派”自我加冕的救世主意識與專制傾向實不足取,而以反對民粹主義為由否認改革的人民性、扭曲改革的公正性,也必須反對。無論左右,我們應該有一個共同的前提——或者說是底線——這就是我們每個人追求個人利益的權利、我們每個人追求言論自由的權利。 漢代劉向說:“君子欲和人,譬猶水火不相能然也。而鼎在其間,水火不亂,乃和百味。”一些觀念分歧勢同水火,若有一只鼎隔在其間,許多討論就可以持續下去、深入下去。我們愿意成為這樣的“鼎”。 —— 編者 “為什么我們就不能夠發一些不同的聲音?” 問:1996年當你接手《讀書》雜志的時候,它面對的社會環境和沈昌文先生主持時期已經不一樣了吧? 汪暉:九十年代中期中國正在經歷一個大轉變。鄧小平南巡講話是在1992年,此后的第一波市場化浪潮被人們所感知,大概就在1994、1995年。1996年初,我應邀擔任《讀書》雜志的主編的時候,也正趕上這一浪潮。房地產市場、股票證券市場、開發區建設等一下就使得市場化的潮流涌動起來,在拉動經濟的同時,導致急劇的分化和腐敗。也是在這個背景下,許多知識分子下海了,經濟學家們開始給企業老板打工了,關于市場化和全球化的看法在知識分子中間開始激烈分化。 問:也就是說你在接手這個雜志的時候,實際上面臨著一個新的選擇。 汪暉:當然。我們不可能簡單照搬過去十幾年的《讀書》道路,必須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尋找一條新的道路——你也可以把它理解為在新的情境中激活《讀書》的批判傳統。 問:這個新的道路的選擇,是你個人的想法,還是《讀書》的一個共識呢? 汪暉:尋找新的道路大概是共識吧,但如何尋找,我們自己也在探索中。坦白地說,那個時候,知識界的新迷信已經很嚴重了,必須解放思想,打破新迷信,實事求是地面對新的問題。如果說市場意識形態是在反對計劃經濟和傳統體制的過程中形成的,那么,它現在已經從一種解放的工具蛻變為一種新的迷信和拜物教。這種迷信和拜物教已經把很多社會危機和社會問題合法化——用面包做大來為嚴重的社會分化和腐敗辯護,如果這不是迷信,就是有意的掩飾。你可以說安徽小崗村在改革初期有多么偉大的成就,但是要以此來掩蓋普遍的三農危機的話,那就不只是迷信了;過去講國有企業有問題,計劃經濟有問題,倡導私有化,但在國家的強力主導之下,國有企業的私有化過程產生了極度的社會不平等、大規模腐敗和國有資產流失,不但中國的支柱型產業瓦解了,而且中國工人階級曾經獲得的尊嚴感也喪失殆盡。用市場拜物教為這一進程辯護,在理論上是自相矛盾的,因為他們倡導的國家退出不過是大規模的、強制性的國家介入的幌子而已。我們面對的就是這樣一個新的迷信的氛圍,在這個氛圍中,你怎么探索新的道路?我們要創造一個討論現實問題的平臺,讓不同的聲音出來,一起來探討一些問題。 問:當你力圖打造一個平臺來討論現實問題的時候,一些人在指責你:一方的聲音越來越強烈,而另一方的聲音好像越來越弱,甚至后來是聽不見了。 汪暉:第一,幾乎主要問題的討論中都有不同的聲音。比如物權法、私有產權的討論,既有吳敬璉、張維迎他們的一組文章,也有崔之元、王紹光他們的一組文章。在三農問題上,你也可以從《讀書》中找到不同觀點的文章,其他問題上大概都是如此。但是,你也知道,經濟學家現在寫文章越來越少了,他們都很忙。我們很希望他們能夠寫文章。只要是認真的、有質量的討論,我們沒有排斥任何人。 第二點,2000年以后,有關改革的爭論集中在三農危機、醫療改革、教育改革、產權改革等問題上,原先自命為某一派的那幾位似乎從未提出也從未真正參與過這類問題的討論。此外,在整個中國的媒體領域里面,主流的聲音鋪天蓋地,為什么我們就不能夠發一些不同的聲音,或者讓不同的聲音更大一點? 問:但是在你主持下的《讀書》和之前的《讀書》差異太大了。在此之前的《讀書》是以啟蒙者的姿態來承擔它的歷史責任的,但到了今天呢?——啟蒙好像越來越趨于消逝了。 汪暉:你的這個提法好像不準確。如果要回答你的問題,先要問什么是你所理解的啟蒙?在上世紀80年代,人們對于現代化抱有樂觀的情緒,但90年代,隨著這個現代化進程的發展,對這一進程本身進行反思變得不可避免了。在你看來,這些反思與啟蒙毫無關系? “反思啟蒙不是反對啟蒙” 問:你說是反思啟蒙? 汪暉:當然。反思啟蒙就是在推進啟蒙,沒有對啟蒙的反思和自我批判,啟蒙就會僵化為教條、甚至成為新的權力的關系的合法化表述。因此,就像沒有對改革的反思,便不可能推進改革一樣,沒有反思啟蒙,啟蒙就會被僵化為教條。有人說1989年后啟蒙突然中斷了,在我看來并非如此,中斷是片刻的。反思是啟蒙的第一要義。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潮流在中國的長足發展是從哪兒來的?我們當然要反思這個過程。反思啟蒙不是反對啟蒙,而是在更高的層面推進啟蒙。 問:你所說的反思啟蒙是不是包括對歷史的反思和對現實道路的反思?你們對歷史的反思,包括從歷史進程中尋找一些具有現實合理性的東西,比如說文革期間的醫療制度已經有了成功的制度雛形。但有些人認為你這樣做有為文革翻案的危險! 汪暉:反思啟蒙當然包含對整個現代歷史進程的再思考,它是批判性的,不是辯護性的。我不是很理解你的問題。歷史永遠不可能簡單重復,對于歷史的追尋永遠是對現實問題思考的一個部分,除非我們把自己已經僵化到不能夠反顧歷史的時候。反思啟蒙更不等同于就是重新討論文革,我不知道你在什么意義上將這兩個問題放在如此確定的框架里。誰在簡單地為文革辯護?這種說法實在有欠考慮。文革當然要反思,社會主義歷史、21世紀歷史都要反思,但是不能夠總體化的否定,總體化的否定只有一個功能,就是強固某一種歷史形態,即通過對某個時期的全盤否定為現實本身提供合法性證明。我想,我們最好離開那種“翻案”史觀,我對此一點興趣也沒有。我沒有什么覺得不可以質疑的前提,恰恰相反,沒有新的思想解放,我們就會陷入更大的危機。 問:你對現實道路的反思恐怕更會招致批評,因為在很多人看來,1840年以來中國的歷史就是不斷推進現代化過程的歷史,中國最終要向一個現代化國家轉型,實現現代化。在這個過程中,你這種反思——即使是必要的話——要盡可能的克制,因為這很可能影響到對一些既定目標的追求。 汪暉:我不相信你說的既定的目標,這是歷史目的論。你說的既定是誰定的?現代化本身就需要被反思。談論鴉片戰爭以來的現代化運動,離開殖民主義、帝國主義,離開在新的條件下產生的社會不平等和危機,有可能嗎?對于反思而言,什么叫“盡力克制”?過去有過為了革命我們要盡力克制反思和批評的經驗,現在再來一次嗎? 問:但是現代化的許多價值目標,包括自由、民主、文明,難道不是普世價值嗎? 汪暉:自由、民主、文明都是很好的字眼,但殖民主義時期,文明國家指的就是基督教國家、歐洲國家,也就是別的文明都不是文明。 問:但是你不能否認,在今天的眾多西方國家——比如北歐的瑞典——從歷史上來看,它比以前獲得的自由、民主權利要大得多。 汪暉:北歐,歐洲,以及美國都有值得我們學習的東西。這些國家的成就是各種社會力量漫長歷史進程的產物。北歐的社會制度中有許多社會主義的因素,歐洲的福利傳統也是長期社會斗爭的產物。不要把這些問題簡化為現在這樣的提法,人為地造成分裂。此外,根據自己的實際去學習別人的經驗,而不是用別的經驗全盤地否定自己的傳統和歷史,這里有一個思想方法的問題。 帝國主義經常采用普世價值為其行徑提供合法性,一些國家的所謂“自發私有化”(其實根本上就不是 “自發的”),以及隨后產生的寡頭民主,也是在你所說的普世價值的名義下完成的。我們應該壓抑對這一進程的反思嗎? “為了推進民主,我們必須破除(民主)迷信” 問:難道你也要質疑民主的價值嗎? 汪暉:我支持民主。事實上,我認為今天中國的問題之一是普通民眾缺乏政治參與的途徑,工人、農民不能上升為一種更強大的政治力量,就無法保護他們的權利。可是,什么樣的民主才能在我們這個社會里頭生根,產生出實質的意義?你愿意看到民主化過程變成少數人瓜分權力和社會資源的過程嗎?你愿意民主化產生出一個完全分裂和沖突的社會嗎?民主迷信造成的問題,比不民主,一點也不小。因此,為了推進民主,我們必須破除迷信。 1993年的時候我有機會到俄羅斯考察。后來我也到過波蘭、匈牙利、捷克等東歐國家,感覺后社會主義國家改革雖然經過了民主化的浪潮,但仍然出現了很多很多的問題。我們應該研究這些問題。最重要的問題是不要讓民主化的浪潮變成了少數利益集團合法地瓜分社會財富和政治權利的過程,而要讓這個過程變成普通大眾獲得真正的政治權利的過程。 問:你對中國的民主進程也產生了懷疑? 汪暉:你是想說我反對中國的民主化嗎?如果是這樣的話,我不知道這個問題是從哪里來的?我對回答這樣的問題沒有興趣。中國要探索一個更為民主、更為公平的社會,需要根據自身的社會條件,探索自己的道路。我希望避免的,是少數精英集團利用這個過程將自己對社會財富的剝奪和政治權力的攫取合法化。我們要探索一個讓社會大眾獲得政治權利和社會地位的民主進程。如果工人、農民和許多普通人在這個進程中喪失了他們的尊嚴和位置,這還是民主化嗎? 今天的 問:我認為,對民主可能帶來的問題的擔心,不能成為我們抗拒、排除民主價值的理由。 汪暉:我認為你混淆了問題。首先,我們討論的并不是對未來的擔心,而是對現實進程的分析;其次,對民主的追求必不可免地包含了對民主的反思。 比如說現在有很多人談歐洲的福利國家,民主社會主義的話題很熱門,我也覺得歐洲有很多值得我們學習的制度。但是我們也要知道,在過去的二三十年當中,福利國家制度已經面臨巨大的危機,中國13億人口,資源這么匱乏,能夠建立歐洲的這種社會福利制度嗎?所以不可能簡單地復制歐洲的福利制度,我們要學習它的很多的經驗,同時要了解它的價值,要找到新的道路。不要從一個制度的模仿到另一個制度的模仿,不要從一個拜物教到另外一個拜物教。 “也有很多人支持我的看法” 問:那么你認為中國如何推進民主建設? 汪暉:根據自身的歷史條件,借鑒其他社會的歷史經驗和教訓,探索中國政治改革的道路。制度創新與社會斗爭是民主實踐的有機部分。 問:你說的社會斗爭是什么? 汪暉:社會斗爭各種各樣。如果沒有黑人運動、婦女運動、工人運動等等,美國的民主制度也是不可能的。 問:這種斗爭會不會導致民粹主義? 汪暉:為了捍衛自己權利的斗爭怎么就叫民粹主義呢?這是完全顛倒黑白!布什是民粹主義,小泉純一郎是民粹主義,貝羅斯科尼是民粹主義!新自由主義的政治是民粹主義政治,但把普通工人農民爭取自己權利的斗爭稱為民粹主義,這是站在什么立場上說的? 問:“大眾”有時候是不理性的。 汪暉:誰理性一點呢?資本是最理性的?為了資本的利益最大化,剝奪許多工人的權利,是理性嗎?我怎么沒聽說要以理性的名義節制資本啊? 問:坦率地說,許多人對你質疑現代化、全球化的做法很不以為然。 汪暉:對不起,也有很多人支持我的看法。我認為現代化需要反思,全球化需要分析,難道我們要將現代化和全球化奉若神明,置如此之多的社會危機于不顧嗎? 問:中國有中國的問題,恐怕不能和世界上其他國家相提并論吧。 汪暉:這句話的含義好像很不清楚,你的針對性是什么?我一再強調的就是中國有自己的獨特條件,獨特問題,但從不認為這些問題是與世界的問題無關的。沒有世界性的變化,怎么理解十九世紀以來中國的變遷? 來源:經濟觀察報網
【發表評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