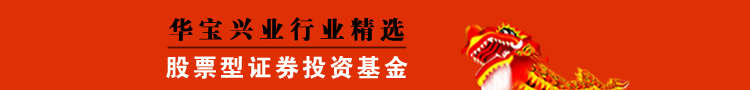 |
|
|
|
第一期:1977-改變命運的開端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6月08日 19:21 經濟觀察報
徐友漁 1977年9月,鄧小平再一次恢復中央工作 1977年10月,恢復高考 1977年是改變命運的開端,對國家是如此,對個人也是如此。 雖然嚴格說來,關鍵的變化發生在1976年的9月,隨著毛澤東的去世,歷史正在展開新的變化。但社會和思想的惰性是巨大的,“照既定方針辦”和“批判鄧小平、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口號還是照舊。對于像我這樣遠離政治中心,只能感到灰心失望,看不出人事變動與方針政策的變動有關系。當我能夠感覺到變化正在醞釀、發生時,已經是過了1977年的上半年。 恢復高考是棄舊圖新的標志 不論對個人還是對國家來說,1977年恢復高考都是一件標志著發生翻天覆地變化的大事。所謂的“文化大革命”,首先就是從停止高考開始的,整個運動期間,“教育革命”的口號不絕于耳,高校是受文革蹂躪最重的地方,如果真有撥亂反正的想法,也應該從教育領域開始,尤其是應該拿大學招生的辦法和標準開刀。 我還記得,1966年6月中旬,正當文革的烈火在神州大地燎原之際,《人民日報》發出消息,北京女一中高三(四)班學生寫信給黨中央和毛主席,強烈要求廢除原有的升學制度,緊接著,北京四中全校師生致信中央,響應女一中發出的倡議。《人民日報》在6月18日發表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的通知,決定招生暫停,以改革高等學校招考辦法,廢止現行辦法,將來的辦法是推薦與選拔相結合,要突出政治,要走群眾路線。《人民日報》同時還配發社論,稱“舊招考制度是資產階級政治掛帥,分數掛帥,嚴重違反黨的階級路線,把大量優秀的工人、貧下中農、革命干部、革命軍人、革命烈士子女排斥于學校大門之外,為資產階級造就他們的接班人大開方便之門。” 從此之后,中國的大學停辦多年,文革期間,大學成了批評斗爭校長、老師、“牛鬼蛇神”、“階級敵人”的場所,成了用刀槍搞武斗的戰場。到了1968年7月,毛澤東發出最高指示:“大學還是要辦的,我這里主要說的是理工科大學還要辦,但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1971年,“四人幫”炮制出“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其中提出危害深遠的所謂“兩個估計”:文革前17年的教育戰線是資產階級專了無產階級的政,大學教師和這17年培養的大學生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 1973年的大學生招收本來打算略有改進,在推薦、選拔、突出政治的原則之上加一點文化考核,這一點小小的變化在全國成千上萬渴望進大學的青年中不知激起了多大的興奮、多少期望,他們除了勤奮好學之外,實在沒有什么本事來滿足“突出無產階級政治”的標準。但是,“四人幫”連這一點稍微像話的變動都不能容忍。他們利用遼寧青年張鐵生在文化考核時交白卷一事發難,把白卷先生樹為“反潮流的英雄”,再次掀起大批判的浪潮,廣大青年的學習和上進熱情受到無情嘲弄。 文革積重難返,撥亂反正需要大手筆 上學讀書需要考試,上大學需要比較嚴格、全面的文化考核,這本來應該是不言而喻的常識,但是,文化大革命把最基本的是非觀念顛倒了,更何況,關于高校的種種方針和措施,是毛澤東高度重視和親自指示的,任何變動,都涉及到是不是“正確對待文化大革命”的問題,都涉及到是不是“忠于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問題。 文革期間“四人幫”炮制了一部以批判鄧小平為主題的電影《決裂》,其中情節的矛盾焦點就是“什么人可以上大學”的標準問題。影片鼓吹的觀點是,知識不但不重要,而且往往是負面因素,考核的標準是“是否忠于革命路線”,即忠于文革那一套,影片主人公豪氣沖天地舉起自己的手,氣壯如牛地說:手上長滿老繭,這就是上大學的資格!這句話和這個形象,完全就是文革時政治標準的象征。文革時搞文化專政,萬花凋謝,這部宣傳“革命路線”的電影在全國發行,幾乎每個人都熟悉它的觀點和情節。這一套現在看起來是邪說謬見的東西,在文革中是如此有威勢和深入人心,以至于被許多人當成天經地義。我記得,當我向一個在大學擔任系主任職務的親戚表示自己還有上大學的希望時,他異常肯定地說:“你們還要上大學,想都不要想!”他指的既是政治形勢和政治標準,也包含年齡。在這些搞教育的人看來,年近30歲,早就過了讀書的年齡。我聽了他的話既傷心又寒心:在這些心地不壞的人看來,我們被文革耽擱了,這一輩子就算完了。 確實,1976年秋季中南海內的劇變似乎與社會生活、與老百姓的命運前途沒有關系。個人迷信仍然大行其道,只不過在“偉大領袖”之外又加了一個“英明領袖”。甚至到了1977年的2月,權威的宣傳機器“兩報一刊”(《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和《紅旗》雜志)在其重要社論中還在鼓吹“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這個后來以“兩個凡是”載入史冊的口號使不少人對所謂“第二次解放”產生的歡欣鼓舞發生懷疑:是不是“四人幫”沒有打倒,是不是文化大革命還沒有結束? 回歸正常來之不易 到了1977年7月,鄧小平在十屆三中全會上再一次恢復職位,他復出后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召開科學和教育座談會。從報上得到的消息是令人鼓舞的,科學家和教授們紛紛發言,揭露和控訴文革的破壞,提出許多恢復科學研究和大學教育正常秩序的建議。希望的火苗又開始在心中閃爍,雖然我這時已經年滿30歲,但我不甘心。 我從小把上大學看成一件神圣的事,我父親早年畢業于武昌師大,1925年去法國就讀于巴黎大學文學院,1927年入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他的經歷、見識對我有很大影響。我剛上小學,他就教我外語和古文(他年輕時曾經是國學大師黃侃的弟子,上世紀50年代在四川大學當俄語老師)。在我年屆30時,雖然完全談不上孔老夫子的“三十而立”,但人生觀也相當成熟和堅定,我經常向朋友們宣稱,人生一世,官可以不當,錢可以不賺,但大學卻不可以不讀,不讀大學是終生遺憾。 我想讀書的動力是太大了。我承認,在下鄉的艱苦日子,在回城當鍛工的時候,我抓緊學習具有功利的目的,我想通過掌握豐富的知識來獲得某種工作崗位,從事或多或少帶創造性、研究性的工作。事實上,不論在鄉下還是在工廠,我的確利用我的知識優勢得到一些好處。但是,我的讀書動力更具有一種精神性的根本目的,面對文革的種種倒行逆施,我逐漸產生了一個明確的想法:我們這一代必須抗拒愚昧,必須首先把自己從蒙昧和野蠻中拯救出來。我曾和一群知青朋友爭論,他們一小群人抓住機會就玩,以朋友關系的親密無私追求善和美,抗拒文革中普遍的冷酷和殘忍,對我整天讀書不以為然。我對他們說,“真善美”三種價值中,求真為第一位。有人要剝奪我們天生受教育的權利,要讓我們成為沒有頭腦的機械工具,我把這當成精神強奸,我激奮地說:喜兒受了黃世仁的凌辱要反抗,我們不拼命追求知識就太沒有血性了! 6月底,教育部提出改變以選拔和推薦的方式招收工農兵大學生,通過考試招收應屆高中畢業生,這個辦法實際上是把我們“老三屆”排除在外,讓我們成為文革的犧牲品。我和妻子得知這個情況時,覺得這不公平,這個辦法對培養人才不利,對中國的現代化建設不利。我們連夜給鄧小平寫了一封長信,提出我們的看法和希望,并寄給物理學家楊澄中,請求他轉交。我們并不認識這位科學家,只是天天看報紙,感到他的發言思想很開放,對于文革破壞教育、科技、文化的后果認識非常深切。 雖然我們的呼吁信很可能沒有送達到鄧小平手里,但最后國家的政策確實如我們所愿,我們獲得了參加高考的機會。 我后來聽說,有關人員曾對鄧小平說,招生工作會議已經開過,恢復高考當年來不及,要改也得到明年。但鄧小平非常堅定,決定打破常規,堅持當年就改。他說,看準了的事情不能等,招生工作會議,重新開一次就是了。 進大學真不容易 1977年秋、冬之交的日子,我是在緊張的備考中度過的。坦率地說,這段時間我信心十足,說夸張一點還有幾分趾高氣揚,因為我覺得自己的優勢很大。 聽不少人講,面對這千載難逢的機會,他們卻歷盡波折,甚至飲恨終身。雖然國務院的通知規定高校招生原則為自愿報名、統一考試、擇優錄取,但在一些地方和單位,領導并不支持大家去報名參加高考,甚至以種種理由(比如,文化大革命中有什么問題)刁難和阻止。我去廠部教育科報名本來還有點忐忑不安,作了要大費唇舌的打算。因為報名條例并不是說任何人想去考都可以,對于年齡大的人,要有一定專長,表明是個人才。我過分認真地對待這個條件,背了一大包書去,證明自己自學過英語、日語、德語和大學的化學課程,讓主管干部考我。結果人家哈哈一笑,大筆一揮,輕輕松松就批準了。 不知道是不是我所在的四川省或成都市的政策特別寬松,似乎任何愿意參加高考的人都得到了批準。因為我后來發現,不少在文革前1965年參加過高考而落榜的老高中生也參加了考試,從文件規定的條件看,他們明顯不屬于有高考資格。幾乎每個大學都收錄了這些1965屆的高中畢業生,看來,在那個百廢待舉的時刻,敢于冒險和打破常規的人是會得到額外好處的。 我也聽說,一般在工廠或其他單位上班的人都感到備考時間來不及,因為通知很晚,而且不能撂下自己的工作不管。但我比好多人條件要好一些,因為我干的鍛工活很重,一個班真正干活的時間決不可能是8小時,空余時間比較寬裕。 荒廢10多年后第一次面臨“開科舉考”,許許多多的人還真是手腳無措,合適的教材成了極度稀缺的資源,久違了的讀書習慣要想恢復也并非易事。對于我,這一切都毫無問題。作為一個極其規矩的好學生,我把自己從初一到高三的所有課本都完好無缺地保存了下來,這樣的課本被認為是最有價值的。另外,這么多年我一直保持刻苦學習的習慣,甚至覺得10多年前學得的知識并沒有忘掉多少。 我就是在這種占盡優勢的心理下參加高考的,不用說,我填的志愿都很高,一副即將進大學,以后當科學家的架勢。 但是,出乎意外和令人尷尬的是,我落榜了。其實,以我的見識和閱歷我應該有所預料,但我對“新時期”和“國家急需人才”這些話太當真,我完全沒有想到,這次高考和文革前一樣,仍然有“政治審查”這一關,而且標準和文革前一樣,所謂“家庭出身”仍然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我強打起精神在車間干活,并裝出若無其事的樣子,把幾個一起復習功課并考上重點大學的親友送到學校(77屆新生入學已經是在1978年初)。在難受的日子,一股激奮之氣在心中油然而生。我認定,新的時代就要到來,我還有其他機會。 到了1978年3月初,我居然接到四川師范學院數學系的錄取通知。雖然我的志愿上沒有填這個學校和這個專業,但我十分高興,這使我擺脫了落榜的羞恥,而且,我從來就非常喜歡數學。 據說,是鄧小平知道有不少學業不錯的考生因故落榜而叫補招的。許多大學還不肯,說是校舍已經滿了。鄧小平說,那就招走讀吧。我相信這是真的,只有以他的眼光、魄力和威望,才能夠再三打破常規。可能也只有他這樣的人,才對中國的現代化事業有那么急切的心情。 難忘的大學校園生活 我入校時,學校已經開課一陣了。走讀生剛進校時不那么自然,似乎低人一等,補招進來的,牌子是不怎么硬。但界限很快就消失了,因為我們人很多,而且其中有人學業相當優秀。比如走讀生老蔡原來是中學英語老師,他的水平之高,可能超過不少英語系的教師(他現在在美國一個大學當系主任)。我的英語也比較突出,遠在數學系公共英語課教師水平之上,我去上了幾次課,她就建議我參加一個免修的考試,通過之后就不上這門課了。 走讀是相當艱苦的,因為學校離家很遠,在城市另一端的郊區。我們紛紛在學校附近的農民家租房,住得比學生宿舍寬敞、舒服多了。這一帶的農民經營花木,我們好像是生活在空氣清新、鳥語花香的花園中。不久,學校安排出了校舍,我們搬進校內,頭上的“走讀生”帽子徹底摘掉了。 文革后的第一屆大學生不像正常時期那么單純,比如年齡最大的和最小的相比,幾乎年長一倍。學校把年齡大的學生分在一起,稱為“大班”,這里面真是藏龍臥虎,什么出類拔萃之輩都有。比如大班有個同學姓鄧,文革前是高中生,進大學前一直在中學教數學,而且一直在鉆研數學,他進校后就免修所有的專業課,幾乎成天窩在寢室里寫數學專著。他聲稱,他在學校呆4年,也就是圖個文憑而已。他的水平顯然比一般的青年教師高許多,他偶爾自習課時到教室里來指點一下同學,為的是調劑腦子,也從大家的贊嘆中獲得心理上的滿足。 除了鄧姓同學這種數學天才,大班生中不少人是以前的中學教師,或者單位的領導、骨干,他們學習輕松,多才多藝,常有驚人的表現。比如,有個同學寫劇本、排話劇,學校文藝匯演時引起轟動,拿了第一,弄的本該獨占鰲頭的中文系同學很沒面子。另一個同學會作曲,精通幾樣樂器,他創作和指揮排演的歌舞,在匯演時一舉成名。還有一個同學是優秀的男中音,表演節目時一曲“拉茲之歌”,使得“再來一個”的呼聲不絕。甚至我們學校保持多年的跳高記錄,也是數學系大班的一個同學打破的。大班學生的種種不俗表現,使得小班的同學非常敬佩,而且把他們的崇拜流露于言表,這使得大班的一些人心里非常舒坦熨貼。 77級學生入校后,普遍產生了一個問題,是校方和老師們完全沒有預料到的。經過嚴酷考試篩選,懷著“天之驕子”心態進校的77屆新生與尚未畢業的“工農兵大學生”之間的沖突在各個學校都發生了。新生對未經考試就讀大學的人表現出公然的鄙視,“工農兵”們也不服氣,學校費了好大的力氣才使雙方相安無事。我們數學系教訓新生的辦法很特別,系上舉行一次“摸底測驗”,試題相當深,以至于大半同學不及格。這么一來,大家感到自己其實并沒有多么了不起,也深感學習負擔很重,自然失去了沒有了“工農兵學員”的心思。 當年一個普遍而又嚴重的問題是77屆學生中出現了“陳世美”,一些人“中舉”之前“落難”在農村或基層單位,草草結婚,生子育女,一進大學,周圍是如花似玉、天真清純的“小班”姑娘,情不自禁地燃起拋棄發妻,另度一春的欲念。記得那時學校領導、年級主任或班主任經常接待前來哭訴、哭鬧的“秦香蓮”,流言和故事飛快地在同學中傳播。當年《人民文學》上有一篇小說“杜鵑啼歸”,講的就是這種事,影響很廣。據我觀察,我校的“陳世美”們似乎沒有人成功地謀得新歡,除了暴露自己的不忠,只落得學校的處罰和同學的批評、議論。 經歷文革摧殘的大學校園在70年代末顯得生機勃勃,思想空前活躍。最吸引我的是各種課外講座,數學教授們的講演我幾乎一場不缺,值得回味的是,他們講完專業問題之后,總要小心翼翼、自責地補充一句:“我這次沒有闡述馬克思《數學手稿》中的光輝思想,這是我今后要努力學習和改進的。”我讀過馬克思的《數學手稿》,那根本不是數學著作,而是黑格爾哲學概念的搬用和演繹,但教授們感到不發揮馬克思的思想總有一種有罪感,就像幾年前發言、寫文章不引用毛主席語錄就沒有正確性一樣。四川著名作家雁翼的講演很大膽和刺激,我記得最清楚的一句話是:“其實,歷次運動整知識分子,下手的還是知識分子。”在討論“真理標準”的開始,四川大學一位哲學教師來做報告,談到她在北京開會的情況,似乎有以身家性命為賭注的緊張氣氛,我不明白,為了一個簡單的哲學命題,怎么會鬧到這個地步。 我們都有類似于劫后余生的感覺,特別珍惜現在的機會,學習極其刻苦用功。不過,據我的體會,數學恐怕是各學科中最難學的,因為面對數學的高度抽象和推理的極度復雜艱難,勤奮和刻苦基本上無濟于事。特別是,因為合格的教師奇缺,急需人才,有關部門決定我們大班變為快班,用最難的教材,抽調本校最好的教師,把本來4年的學習任務3年完成。這一下,使不少人叫苦不迭。我周圍的許多同學原先在單位都是佼佼者,聽慣了贊揚的,現在學習吃力、掉隊,內心的沮喪和折磨,我能夠感覺得到。特別是,人們經常聽到隔壁寢室里政教系的同學聊天、拉琴,感到非常不平,他們口出怨言:數學系這么苦,人家這么悠閑,到頭來工資還不是一樣? 又一個新的開端 不管是樂也罷,苦也罷,我在大學本科生涯還不到一半就離開成都到了北京,我被學校破格特許考研究生,于1979年秋季來到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 這是又一個新的開端。北京的生活、氣氛與故鄉大不相同,尤其是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節奏飛快,刺激性事件接二連三,令人目不暇接,有時甚至使人喘不過氣來。比如,西單“民主墻”的大字報前人山人海,“星星”畫展叫人眼界大開。 開學典禮就給了我非常深刻的印象,這是在一個豪華的大禮堂中舉行的。當社科院一些領導從大門魚貫而入時,我和其他人立刻發現了其中有王光美,他們緩步前行,和過道旁的同學一一握手,碰巧,我就坐在過道旁。當我和王光美握手時,聽見她緩緩地說:“謝謝同志們”,感到意味深長。當他們就坐后,滿場的人齊聲喊叫,希望王光美發言,推辭幾次后她站起來說:“我知道,同學們的熱情,并不是沖著我來的。”這時劉少奇還沒有得到平反,這一幕當然意義非同小可。 我所在的哲學系有一個“毛澤東思想”專業,其導師有哲學所的所長。他以前是部隊的軍級干部,他經常來和學生見面,說話大膽坦率。那時黨內高級干部正在討論和爭論《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一系列未定稿,他把各種議論、看法告訴自己的研究生,我們立刻聽到第二手消息,引發種種興奮和猜測。 從1977年開始的大學和研究生階段是我的生活的一個新開端,它們剛好和我們國家告別過去,走向新的一輪現代化途程的開端相重合,我想,也許是憑這一點,我至今習慣于把自己的未來和祖國、民族的前途聯系在一起。 作者介紹:中國著名學者,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主要著作有《“哥白尼式”的革命》、《形形色色的造反》、《告別20世紀》、《不懈的精神追求》等10余部。 來源:經濟觀察報網
【發表評論】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