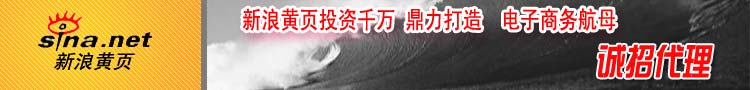
|
|
|
|
|
游說 站在大門口的陌生人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9月28日 13:17 《董事會》
站在門口的陌生人編者按:十幾年前風靡一時的電視劇《公關小姐》曾讓很多國人開始懵懂地接受“公關”這個概念,盡管在某些人心中仍有將其與“攻關”賄賂聯系在一起的偏見。但經過這么多年,隨著外來事物的大量涌入,很多人已經日益認可了公共關系在公司活動中的正當性存在。而如今,一個更加時髦的詞匯開始在圈內流行,那就是 “游說”。游說其實在國外早已經是在法治約束框架下的公開活動,然而在中國卻依然是頗多忌諱的詞語。同時,也正是“游說”活動本身所固有的不事張揚的規定性,又讓多數國人無法領略其真正的內涵。其實,《董事會》的努力也僅是給讀者展示那浮在水面上的冰山一角,更多的細節就只有依靠國家立法來推進“游說”浮出水面,進入公眾視野。 游說,站在大門口的陌生人 游說對于大多數中國人而言,還是個站在大門口的陌生人。可是,這個陌生人其實早已進了自己的家門。 文/劉晶 2006年6月22日,美國前商務部長唐·埃文斯(Don Evans)來訪北京。與之前訪華時有所不同的是,此時的埃文斯已經是美國“金融服務論壇”(Financial Services Forum)的CEO。在北京期間,埃文斯會同美國大使雷德一道,與北京市長王岐山進行了會面。第二天,《華爾街日報》和《金融時報》相繼刊登新聞,稱埃文斯在北京與政府官員會談后表示,中國有可能在對五大國有商業銀行放松外國投資上限之前,先上調中小銀行的外資最高持股比例。 這其實是一次地地道道的游說之旅。埃文斯所在的“金融服務論壇”也并不是一個關于金融服務的清談機構或者民間智庫。如果你去LobbyWatch這個專門搜集游說公司公開業務資料并加以統計的網站檢索,就會很容易地查到“金融服務論壇”其實是一家專門針對金融業的商業公關游說公司。它的成員包括美國國際集團(AIG)主席兼CEO馬丁·蘇利文(Martin Sullivan),高盛集團(Goldman Sachs)主席兼COO布萊克·費恩(Lloyd Blankfein),德意志銀行集團(Deutsche Bank)執行委員會主席阿克曼(Josef Ackermann)等等歐美金融界的頭面人物。美國現任財政部長鮑爾森(Henry Paulson)就曾是該論壇的主席,現任主席是花旗集團CEO普林斯(Charles Prince)。如此龐大的陣容,要做的事情只有一件:在華盛頓販賣他們身后所代表的金融業界集團的影響。當然,他們活動的范圍要比華盛頓特區大得多,埃文斯的中國之行便是例證。 很長一段時間以來,國人對于媒體上出現的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官員會見到訪的外國商界人士等類似的事件,都抱著一種很單純的看法:增進友誼,促進經貿交流,吸引外資。事實上,起初這類政商界的溝通的確也都是以這些比較單純的內容為主。但隨著中國經濟開放程度的日益加深,外資介入中國市場的程度也在同步深入。國內市場早已經不是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和三資企業各安其分,市場分割涇渭分明的局面了,政府已經開始評估外資進入的正面和負面影響。 今天外資進入中國所要面對的,既有政府對國家經濟安全的考量,也有中資同業競爭者各種非商業形式的競爭和尋求政策壁壘的保護,更有對高風險項目投資所面臨的信息不對稱等狀況。于是,以各種面目出現的商業游說和政府公關公司的生意便日漸興隆起來。外資公司也早就開始利用在國外已經較為成熟的游說手段和策略,嘗試著進入中國市場,并盡力打造有利于自身發展的政商關系。 在中國,普通人對于游說的理解大多還停留在蘇秦張儀式的外交政治游說層面。一談到商業游說,不免聯想起“拉關系”、“走后門”這類本國特色的灰色商業行為。對于外國公司的游說活動,則多與商務談判聯系起來。很多人并不知道游說對于商業成功的重要性,出于一些顯而易見的原因,人們也不清楚游說的過程和操作手法。游說對于大多數中國人而言,還是個站在大門口的陌生人。 可是,這個陌生人其實早已進了自己的家門。 尋找Mr.Key 游說并不僅僅是面對面的口頭工作,而是為了達到最終目的而設計的一整套公關策略。外資公司在進入中國市場的時候,最常見的游說管道是利用改革開放以來“吸引外資”這一天然的政治正確方針,以外資身份直接獲得與當地對口行政官員見面交流的機會,在會談中討價還價,達成企業的商業目標。但這種比較正式而直接的單一游說管道,早已不再是外資游說的主要方式了。這種直接游說方式的優點在于透明、游說過程的成本低,但缺點是必須面對同質化的游說對象(包括人和政策),游說空間固定,因此不容易取得較為滿意的效果。于是,尋找Mr. Key(關鍵人物),通過關鍵人物的社會關系網絡(主要是政商關系)進行相對間接的游說,輔之以直接游說,就成為外資進入中國市場,尤其是敏感產業的主要游說形式。 2004年8月,《財經》雜志的封面報道《高盛進入中國》,曾引起了各界的廣泛關注。高盛歷時三年的中國攻略,其游說策略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部分:與中國政府高層和金融主管部門建立良好的關系;愿意掏錢幫助解決中國的“問題券商”,以換取進入中國證券業的門票;尋找關鍵人物作為自己的緊密合作伙伴,將與政府高層和國內業界的信息渠道和溝通渠道固化。 根據媒體的報道,時任高盛公司董事長的亨利·鮑爾森幾年來數十次造訪中國,在中國政界、金融業界乃至學界交友廣泛,其與中國政府當時的高級領導人江澤民、朱基等人有著相當良好的私人關系。在金融界,鮑爾森不僅與前后兩任證監會主席周小川和尚福林保持著密切的溝通關系,而且高盛參與的中國電信、中石油、中銀香港等大型國企海外上市項目,為高盛公司在中國政商界奠定了良好的口碑。 盡管自身實力雄厚,且有經營多年的政府關系,但高盛進入中國證券市場的步伐并不輕松。從2001年開始,高盛連續三年在中國獲得的業務幾乎空白。當中國證監會兩任主席三次向高盛方面“交底”,可以以“買門票”的方式進入中國市場時,高盛方面仍未能解決一個能最終對其商業目的達成與否起到決定性影響的問題——中國方面的合作者是誰。 高盛進軍中國的目的并不僅是持股一家券商,這只是第一步。在日后中方的政策環境允許時,取得一家證券公司的控股權才是高盛的長遠打算。根據中國加入WTO時的承諾,高盛很難突破合資證券公司外資最高持股33%的政策限制。對于這種剛性的約束條件,任何意在當即改變法規政策的游說都不可能起作用。于是,高盛找到了一位Mr.Key來幫助它解決這么一個看似無解的難題。這個人就是方風雷。 雖然公開資料上沒有任何正式的官方身份,但方風雷的履歷讓人乍舌。尤其是上個世紀90年代前后方棄政從商的經歷在國內幾乎無人能及。方在90年代初移居美國,1992年回國經商,1993年回到北京,參與籌建中國建設銀行和摩根士丹利合資的中金公司,隨后出任副總裁。2000年,方離開中金公司,專任中銀香港總裁。2002年出任工商東亞總裁。與方風雷做過同事的有目前北京市長王岐山、央行行長周小川。被西方同行稱為“Rainmaker”的方風雷,顯然是個“神通廣大”的布衣商人。 那么,方風雷是如何起到Mr.Key的作用呢?據國內某財經媒體報道,據信方風雷等人的中方出資資金,實際上為高盛方面借給方等人的資金,與高盛所出的33%股權合資成立高華證券。這其中涉及到兩點突破性的操作,一是國家外匯管理部門批準了方風雷等以個人名義向外資機構借款這一交易行為,此為首例;二是高盛很可能獲得了未來政策環境允許時,購回方風雷等人在高華控股權的選擇權,從而為最終在中國控股一家證券公司埋下了伏筆。 正是因為方風雷在中外投資銀行界皆有良好聲譽,同時兼具堪稱獨一無二的政界和商界背景及人脈資源,才使得高盛在進入中國證券市場的時候,克服了難以逾越的政策障礙。試想,如果不是方風雷多年與高盛等國際投行共事,高盛無論如何不敢以控股權的選擇權這種非正式條款為約束,借款給方風雷等人作為中方出資。而如果不是方在過去十幾年無出其右的政商經歷,政府有關部門也絕難為這種“繞道”的金融投資創新模式開綠燈。這種通過延攬本土Mr. Key拓展在華業務的外資企業游說案例近年來屢見不鮮。方風雷只是其中最為典型的一個。 從“零售”到“批發” 通過Mr.Key這個管道進行游說,是典型的“零售”游說方式。“零售”游說適用于那些技術細節較多,公眾難以對事情本身做出簡單判斷,甚至根本缺乏關注興趣的事情。但是這種游說方式不適合那些很容易進入公眾視野的事件。當外資游說公關的事件演變成公眾關心的話題時,“零售”游說所慣用的找關鍵人的方法就很可能失效,因為游說中的關鍵人本來就慣以低調面目示人,避免意想不到的壓力和干擾。而公眾的關心很容易讓關鍵人失去低調的保護,“零售”游說也由此轉變成“批發”游說,即更多地借助于直接管道之外的間接力量,構建游說壓力,以迫使游說對象做出有利于自己的行動。 我們不妨以京滬高速鐵路建設方案的游說為例。在中方否定了磁懸浮方案之后,德國和日本兩方的游說過程便出現了由“零售”游說向“批發”游說的轉變,更富有戲劇性的是,日本在這一過程中從略占先機到先發劣勢,幾乎均源于其游說失策。 首先,德國方面在第一階段技術選擇論證有了確切結果,且己方最有優勢的磁懸浮方案出局之后,德國立刻變換口吻,開始大力宣傳德國的高速輪軌技術。為此,當時的德國總統約翰·內斯勞親自跑到中國,在上海的磁懸浮列車上為德國鐵路廠商大作廣告,充當了一回最高級別的商業說客。緊接著,德國BWG、普弗萊德爾和西門子三家公司宣布,將在廣州成立“德國高速倡導組織”,并與廣東省鐵路集團有限公司合作在廣州建立實驗中心。德方宣稱將通過該中心向中國國有和地方的鐵路運營單位提供支持和技術訣竅。 德國方面的一系列游說策略起到了相當不錯的效果。作為當時歐洲與中國關系最為親密的國家,德國在中國公眾心目中有著良好的形象。借助這一形象背景,德國總統親自來華游說,一下子令德國在高鐵方案中的公眾印象排名躍升到了第一位。而成立“德國高速倡導組織”,并立刻宣布向中方合作者提供技術支持,可以說是“批發”模式中直接游說戰略的經典策略。通過向對方提供信息幫助,可以迅速加強游說者同游說對象之間的聯系紐帶。德國人的這一做法,深得美國政治游說模式的真諦:讓說客成為被游說者工作的好幫手,而不是做單純的推銷員。 反觀日本,原本在高速輪軌的技術方案上,日本的新干線一直占優。中國媒體和部分專家也一度在輿論上一邊倒地傾向于日本的新干線方案。但是日本沒能利用好這個時機,被突然殺出來的民間反游說活動搞得徹底淪為被動。2003年4月,日本媒體錯誤地判斷,認為日本鐵路業者已經得到中方高層的明確表示,“中國選定新干線的可能性為95%”。結果這條消息立刻引起了中國民間對日反感者的激烈反應,一家名為“愛國者同盟網”的網站在十天之內就征集到超過8萬個網民簽名,反對政府采納新干線方案。日方顯然對這種利用新興媒體的草根動員反游說策略準備不足,接下來采取的游說策略更是一錯再錯。在國土交通大臣扇千景臨時改變攜日方巨額貸款游說新干線來華的舉措之后,日方沒能及時調整對華外交政策,使得中日關系滑落到建交以來的最低谷,政治因素對高速鐵路方案的游說工作造成了致命打擊。 德、日兩國在爭奪京滬高鐵項目上的截然不同的表現,印證了外資進入中國的游說工作正在變得日益復雜,尤其是“批發”式的游說,需要多方游說管道步調一致的配合。一些游說技術手段之外需要考慮的東西,比如政治關系變化、輿論民情反應以及應對反游說的應急方案,都必須要納入到整個游說過程的策略組合當中去。 為“陌生人”立法 前文所述,更多的是在介紹外資進入中國采取的游說手段和實際的游說效果。其實,外資有意識地開始游說中國早不是新近才發生的事情,掐指算來,至少已有十年了。但游說這一行為本身仍掩藏在會談、公關甚至商業賄賂等名目之下,從未被規范過,也從未被正名。“陌生人”并沒有因為他進了家門而變得不再“陌生”。 在那些陽春白雪的外資游說案例之外,那些并不怎么正當的游說活動從未停止過。以Mr. Key模式為例,像高盛和方風雷這種過程上較為公開透明的合作方式其實是少數,很多外資公司進入中國某些政府管制較多的產業時,除了與政府當局現任官員進行正式的溝通外,還普遍聘任有影響的前任官員和該產業的國內資深人士(多為國有企業前高管和人脈資源豐富的“老領導”)出任公司顧問,或者干脆為這些人單獨成立一家顧問咨詢公司,以這種游說方式繞過官方談判繁文縟節的阻礙,直接達成商業目的。也恰恰是在這些環節中,滋生了大量的灰色甚至黑色交易。 游說滑向商業賄賂的腐敗案例中外皆有。美國早期的國會游說活動充斥著金錢、美女等游說腐敗的元素。盡管從1938年起,美國就開始了針對游說活動的立法,在1946年通過了里程碑式的《聯邦游說管制法》,并于1995年和1998年分別通過了《游說公開法》和《游說公開修訂法》,但還是沒有能夠避免2005年爆出游說大鱷阿布拉莫夫對國會議員的行賄丑聞。正如“游說中國網”(LobbyChina.org)的創建人、資深公關顧問吳東所言,中國如果想避免阿布拉莫夫式的丑聞發生,必須要明確游說活動的存在,使游說行為從地下走入地上,并制定法律加以監管。 但在中國進行游說立法的首要困難,是如何在政治上,尤其是憲法層面上,確認游說活動存在的合法性。與美國不同,美國的憲法明確公民擁有請愿權利,并由此延伸出游說行為的合憲地位。而政治學家D.B.杜魯門的研究則指出,現代社會的游說行為必然建立在多元社會中利益集團彼此利益沖突的基礎之上。即首先承認存在著利益集團,而后再承認利益集團利用游說手段謀取自身利益的行為是合法正當的。上述這一從憲法政治出發,為游說行為尋找的合法性基礎,在中國恰恰是最為薄弱的。可能也正因為游說活動在政治界定上的模糊,在外資大舉進入中國的今天,并沒有看到為游說正名的實質舉措。 但現實不容回避,游說,這個熟悉的陌生人,已然站在我們的門口,而我們卻不知如何應對。 相關鏈接:
【發表評論】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