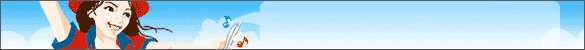|
本報記者 丁凱 北京報道
你正在俯瞰著整個城市,桌上的電話不時響起,一會是抱怨交通擁擠、居住條件惡劣的市民,一會是要求提高財政撥款的大學、醫院和警察局;而你此刻不得不考慮的是是否接受高污染企業落戶的要求,作為交換,他們愿意分擔你的一部分財政壓力……
你憂心忡忡地想著機場的位置、高速公路和地鐵的走向——如同這個世界上的每一位市長。不同的是,當你覺得一團糟的時候,可以把一切摧毀重來,或者退出這款名為《模擬城市》的電腦游戲。
最近,居住在北京且關心城市規劃的人們有了另外一個設想城市未來的方式,他們中的很多人已經或正在接受“新城規劃小組”的訪問,對訪員描述你想要的城市,或者直接對通州的未來發展提出意見——首都規劃建設委員會委托調查機構正在進行的這一訪問覆蓋面甚廣。人們對城市的需求和設想必然千差萬別,但面對他們的,只有一個最終的規劃方案;而最優城市是什么樣,無論提出設想的人還是制定方案的政府都沒有見過。
實際上,我們今天談論的城市規劃,是建立在烏托邦的理想之上。清華大學建筑學院院長助理周榕認為,城市規劃實際上是用統一計劃進行城市資源的配置,在這個過程中,一定要努力減弱規劃的剛性,為市場資源的博弈留出充分的空間,“如果權力一時不能交給市場,是否可以讓權力的邊界有限?”
這一發問可以看作反思中國城市規劃的濫觴,這種反思在2005年7月21日建設部召開的全國城市總體規劃修編工作會議上也在進行。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總規劃師楊保軍透露,恰恰是在這次會議上強調“要區分政府行為和市場行為,政府提供環境、公共服務、安全等無法由市場實現的部分,不能什么都管”。
北京及其他城市的方向
周榕指出,城市規劃本身是建立在所有資源由計劃進行配置的思路基礎上的,我們目前的城市規劃體系,實際上是原原本本地復制了前蘇聯的模式。在從前,這種計劃思路一直主導城市規劃的方向。楊保軍也表示,以往的城市規劃往往是從需求出發,事先設定目標,如果不具備實現條件,就人為努力創造。
“這一思路是在發展愿望急迫,生態環境矛盾不尖銳時的思路。”楊保軍說。轉變發生在當前正在進行的北京周邊11座新城的規劃之中,新城規劃將把當地資源環境情況作為規劃的前提。新城規劃是目前首規委的主要工作,楊保軍所在的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負責其中通州新城的規劃。而由于北京核心優勢是人力優勢,生態環境相對脆弱,今后將以發展服務業為重心。
圍繞節約型社會的方針,北京未來在交通規劃方面提出“公交優先”,改變交通出行結構,公共交通占據人們出行方式的比重將從目前的20%左右提高到50%-60%,而小汽車的比重將相應控制在20%以下,這一目標將通過大力發展軌道交通、限制小汽車使用方式實現,具體說來,可能在某些時段和地段禁止小汽車的使用。
楊保軍表示:“我們國家現在還是要強調政府對于規劃的控制和引導。但如果控制力度過大,凡事干預,就會扼殺市場的調節能力。”據他透露,在7月21日召開的城市總體規劃修編工作會議上,圍繞建設節約型社會的方針,幾個地區的經驗,將成為全國城市規劃的引導方向。
其一是江蘇無錫的農地占用和補償辦法,將有可能成為未來城市規劃中集約利用土地的方向。如果無法補償相應面積的耕地,當地將無法獲得更多的建設用地,因此,當地通過盤活閑置的宅基地實現農地占用與補償的平衡。
在統籌城鄉發展的過程中,由于農村村落分散,建設公共服務設施成本高昂但效率低下,同時,有大批農民已經離開農村,這批人口因為在城市中從事第二、三產業工作,已經開始城市化。無錫市利用政策引導這些農民在城市集中,為其建設農民新村等形式的居住社區,這種轉換過程的成本由需要用地的企業負擔。農民可以自由決定是否在城市獲得一套住房,拆除農村房屋將宅基地復耕。
楊保軍說,這實際上是一種空間上的置換。就好比在未來,一個北京大興的農民在北京城區找到一份工作,但沒有住房。他可以選擇在北京擁有一套住房,拆除自己在農村的住房并同時要求獲得補償,他在大興的宅基地將重新變成耕地,而同時,北京周邊其他地區將有可能因此獲得一塊可開發的土地。
此外,對全國各地城市規劃具有示范意義的還有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的發展以及四川省下派城市規劃督察員的制度。
規劃模式的反思
全國城市規劃工作會議為我們提供的一系列范本,都圍繞構建和諧社會、集約利用資源的主導思想,而這兩點實際上代表了城市規劃的初衷:保護城市中的弱勢群體、提高資源配置效率。
然而,對于我們目前的規劃體系是否可以達到這兩個目標,周榕持保留意見。他表示:“我個人認為,城市規劃是一種很落后的資源配置方式,城市規劃從理論上假設可以通過統一的配置保護城市弱勢群體的利益;第二,可以達到系統配置的最佳效率,而現在這些基本上都不成立。”
新中國的城市規劃直接沿襲了蘇聯的思路,而這種學習并不成功。其特點在于,其一強調對城市資源的高度控制,在此基礎上可以進行配置。其二,以單位而不是個體作為資源分配的單元,兩個單位之間用圍墻嚴格分隔,院內的居民幾乎一切生活需求都可以在圍墻內解決,沒有公共服務進行了社會化。這種單位體制就直接造成了城市空間和資源的巨大浪費。
在北京,局部平均計算每個大院超過1公頃,而每個大院都囊括了食堂、商店、浴室、理發店等等設施,且往往有大片空地。周榕將這種狀態稱為“新里坊制”,里坊制是中國唐代長安的典型城市局部模式,到宋代,發展為街巷式,而商品經濟也隨著這種變革發展起來,周榕認為,學習蘇聯城市規劃經驗,使中國城市實際變成了新里坊制,是一種退步。
周榕認為,用統一方案配置城市資源,這與二十年前我們在其他經濟領域遇到的問題極為類似。城市規劃牽涉到整個經濟制度和政治體制,如果不認清這一點,目前談論如何進行城市規劃,是無法解決城市存在的根本問題的。“城市規劃是計劃經濟的最后一個堡壘。”如果城市規劃脫胎于計劃經濟,我們今天是否還需要城市規劃?
著名城市理論家芒福特(Lewis Mumford)曾說:“人類花費幾千年時間才對城市發展的規律有了局部的認識。”周榕認為:“這就好比盲人摸象,試圖用獲得的一點點認識統攝所有城市的規劃,我認為這是一個根本悖論。”
大家應該熟悉我們的停車管理,我們的汽車只能停放在用白線預先劃好的一個個車位里,不得越線,而在國外很多地區,停車管理是通過“雙黃線”實行,即除去雙黃線以內,任何地方都可以停車,楊保軍則提出,這實際上是兩種城市規劃思路的體現。其一是我國目前的“目標和行動”的思路。認為城市發展規律可以被認識、掌握并用于引導其他城市發展,因此應該根據研究,分析城市發展規律,然后確定城市發展目標并付諸實踐;另一種是“控制性”的規劃思路,認為城市千差萬別,并無規律,所以只要在城市發展中防范最壞的情況發生。
楊保軍認為,西方國家之所以適合第二種方式,是因為他們的城市已經進入穩定期,沒有大規模的物質空間變化,而目前,北京一年的建設量甚至高于歐洲15個國家的總和,這種情況下,還要堅持指導和控制結合的方向,政府不能缺位,但重要的是,城市規劃要配合政府職能轉變,政府應與市場分離,避免制度剛性過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