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團體博弈:多數服從少數 | |||||||||
|---|---|---|---|---|---|---|---|---|---|
| http://whmsebhyy.com 2006年04月06日 14:41 南方周末 | |||||||||
|
□郭譽森 在美國,幾百戶甜菜農,聯合了果糖加工廠與玉米農,竟然使美國糖價幾十年間比國際市場貴幾倍,而3億受害的消費者加上食品巨人可口可樂等竟然一路輸到底。在經濟學家看來,原因是愈小的利益團體,組織成本愈低,游說效率愈高
幾星期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E.Stiglitz)在北京提醒,“中國要把利益集團對經濟的影響限制在最小程度。” 利益集團在美國囂張的干政與影響力是眾所周知、眾所詬病的。為什么經濟學家不信任甚至仇視利益團體的活動呢? 1970年代,管制經濟學開山祖師喬治·斯蒂格勒(GeorgeStigler)在研究各國政府對市場干涉行為后指出,看起來很不同的政治體制下,政府透過管制對社會一些群體進行交叉補貼的行為卻驚人地類似,比如讓長話客戶補貼市話用戶,讓低谷時的用電戶、通話者、道路使用補貼尖峰時的使用者,等等。 是不是各種利益團體在看似不同的政體中“生產”政治影響力的動機與成本其實差別不大呢?為什么在一般的用語中,利益團體常被稱為“特殊利益”團體?一般利益在各國政壇上又為什么常常顯得蒼白無力呢? 在市場經濟之中,任何一項稅收或補貼、或任一項政府管制的改變都會使一部分人得利,另一部分人受損。好的制度,也就是有效率的制度,是使那些總得益大于總損害的政策得到執行,相反效果的政策則會遭到否決。 任一政策的受益人與受害人,都會試圖影響政府決策過程,如果他們的影響力與其利益變動成正比,那在受益與受害團體間的談判、交易甚至斗爭的過程中,好政策自然會勝出,因為得益方的力量比受害方的力量大,而無效率的政策自然會遭否決。此時,政治市場中的競爭均衡會是有效率的,我們就可以不管,就應該放任利益團體的組織、競逐——如果假設這些組織、活動費用可以不計的話。可惜,這個世界不是這樣的。 要動員那些利益團體的成員共同支持或反對某項管制或稅目,必須要想法讓他們每人出錢出力,這是一項極為困難的工作:爭取來的政策對小團體而言是“公共品”——為了維持外資超國民待遇,外資汽車公司、A地方政府寫信給商業部、出錢請教授做“研究”寫文章,反對外資待遇國民化。而外資電腦公司、B地方政府不必花錢、花力氣、花面子,一樣可以享受外資汽車公司、A地方政府“辛苦”爭取來的政策。 換言之,外資電腦公司與B政府可以搭外資汽車公司與A政府的便車,可以不勞而獲。所以要動員這些利益小團體們不容易———每人都希望別人努力“游說”,自己則坐享別人爭來的“公共品”(政策),而且這種搭便車的動機會隨此群體的人數增加而不成比例地增加。 所以建立一個能克服這種“三個和尚沒水喝”問題的組織,其組織成本會隨其人數增加而不成比例地增高,其能發出的影響力會不成比例地減小。換句話說,利益愈集中力量愈大,愈分散則力量愈少,特殊利益團體會因此系統性地壓倒較廣泛的利益,更會壓倒全民(國家)利益。 通常一個政策的得益方與受害方,其分散度并不相同,雙方在政治市場中能發出的能量,并不會與他們的利益成正比。勝出方未必就是那些總得益大于總損害的好政策。 事實上,對美國政府經濟管制行為的主要結論是——行為不理性,系統性地偏離效率準則,偏離任何所謂的“公平”標準,即使何謂“公平”本身也并無定論。 所以無論從理論還是實證角度,我們不能將經濟政策交付給利益團體“博弈”決定。比如在美國:幾百戶甜菜農,聯合了從玉米中提取果糖的加工廠與玉米農,竟然使美國糖價幾十年間比國際市場貴幾倍,而3億受害的消費者加上用糖大戶可口可樂等食品巨人竟然一路輸到底———盡管其總受損量清楚地大于糖業的得益量。東南部一小撮幸存的紡織廠,其工廠主及工人,竟然能讓美國政府要求外國政府對紡織品設限,等于“逼”外國政府(或廠商)收取美國的關稅,使美國消費者受到的損害遠遠超過這一小部分人的得益,達數十年之久。 在得票多者勝的美國式民主下的政治市場上,似乎總是多數服從少數,以至政府決策明顯地、系統地偏離“全民利益”。 兩黨制下的美國如此,那么一黨獨大的、內閣制的日本如何呢?政府行為也差不多,也是少數農民“剝削”市民,農產品貴到其國民愿意從美國提著牛肉與大米回家。我國多年來“剪刀差”的方向相反,是農民“哺育”市民,是不是也是因為我國與美日相反——市民是少數,農民是多數呢?而這二十多年來農民/市民的比例快速下降,是不是正是推動近年來“工業反哺農業”政策轉變的真正力量呢?也許。 上述分析,說明利益集中(或分散)的程度會影響利益轉化成政治力量的效率,其中并沒有假設特定的政體形態,所以應該在任何政體下,特殊利益都將勝過一般利益。 如果制度使媒體廣告決定政客的飯碗,利益團體就會組織政治獻金;如果清廉的政治家相信學者,利益集團就會資助對其有利的學者、學派的研究與出版;如果國家實行科舉考試,他們就會資助窮苦書生考試,并對中舉者謀官必要的應酬進行融資;如果地方官的升要看招商引資業績,他們就投資換取廉價土地;如果政府腐敗,游說集團就會集資賄賂;甚至如果天下大亂,他們就會像南北戰爭時期的美國北方工業主和南方莊園主一樣,出錢資助對其有利的內戰一方! 正因如此,斯蒂格勒才會有前述的觀察:利益團體在表面很不同的政體下,其影響相當類似,因為政治力量的形式是可塑的。 這里只談了利益分散/集中對政策博弈的影響,沒有談利害總量會受哪些因素,比如產品或要素的供給或需求彈性的影響,為什么租金好像總能產生比利潤、工資或利息更大的政治能量等問題。即使如此,我們已可確定,政府必須理直氣壯地抵抗各種利益集團的關說、宣傳、壓力、收買等活動,防止特殊利益凌駕于全民利益之上。這或為中國走向和諧社會必須應對的一大挑戰。(作者為國際濟豐投資公司首席經濟學家、西安交通大學金禾經濟研究中心教授,電子郵箱kwoh@tom.com) |
| 新浪首頁 > 財經縱橫 > 經濟學人 > 正文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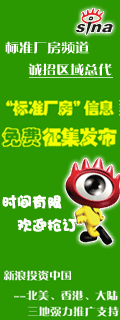 |
| 熱 點 專 題 | ||||
| ||||
| 企 業 服 務 |
| 股市黑馬:今日牛股! |
| 1.28萬辦廠年利100萬 |
| 名人代言親子裝賺錢快 |
| 小女子開店50天賺30萬 |
| 女人錢,怎么賺 (圖) |
| 06年賺錢項目排行榜! |
| 介入教育事業年賺百萬 |
| 100萬年薪招醫藥代理 |
| 品牌折扣店!月賺30萬 |
| 泌尿頑疾——大解放! |
| 拒絕結腸炎!! 圖 |
| 從此改變哮喘氣管炎! |
| 特色治失眠抑郁精神病 |
| 糖尿病——重大發現! |
| 高血壓!有了新發現! |
|
|
|
| ||||||||||||||||||||||||||||||||||||
|
新浪網財經縱橫網友意見留言板 電話:010-82628888-5174 歡迎批評指正 新浪簡介 | About Sina | 廣告服務 | 聯系我們 | 招聘信息 | 網站律師 | SINA English | 會員注冊 | 產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2006 SINA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