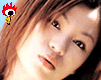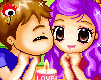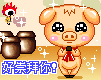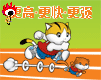| 貴州煤電博弈背后(圖) | |||||||||||
|---|---|---|---|---|---|---|---|---|---|---|---|
| http://whmsebhyy.com 2004年07月27日 13:04 21世紀經濟報道 | |||||||||||
貴州煤電博弈背后 本報記者 程必忠 貴陽報道 “有煤,他們是不愿拿錢買煤,真正的原因就是想以此舉給政府施加壓力,阻止煤炭漲價并盤剝上游產業的利潤,以利于自己獲取高額壟斷利潤。”貴州煤炭行業一負責人直言電廠停機或限制發電的原因。 貴州缺煤嗎? “你先看看幾組數據,就會明白真相在哪里!”7月15日,貴陽煤炭大廈一間辦公室里,吳文學低沉的聲音中帶著幾絲不滿與激動,“相對于許多行業來講,煤炭行業是弱勢群體,對于強勢的電力企業,則更是如此”。 吳文學是貴州省煤炭管理局下屬企業——貴州黔聯煤炭銷售公司的總經理。該公司負責貴州省國有煤礦的煤炭銷售。 “在煤炭系統工作幾十年,與電力部門打交道幾十年,電煤之間可謂恩恩怨怨幾十年!”吳文學說。 今年,這種恩怨被再次放大。 一季度,貴州省由于缺煤被迫停機或限制出力的火電機組一度高達220萬千瓦,發電量為30億千瓦時。 1-5月,貴州省總裝機容量達740余萬千瓦的10多家火電廠,庫存煤最高僅為30萬噸,相當部分電廠只有兩天、一天或者半天的存煤。 貴州省電力公司新聞信息部一位女士透露,直到今天,電廠用煤情況仍然緊張,沒有從根本上好轉,大部分電廠存煤儲備都不到5天。 但是貴州煤炭行業一資深人士坦言,“這是表象而不是真相!” 真相在哪里? 事實上,貴州并不缺煤! 從2001年至2003年,貴州原煤生產總量由3700萬噸增加到了7800多萬噸。同期,貴州電煤需求量從1200萬噸增加到了2420萬噸,今年電煤的供貨合同是2600萬噸。 吳文學透露,今年上半年貴州已經產煤4025萬噸,給電廠實際供煤是1254萬噸,與電廠全年的需求基本平衡。“發電用煤供應并沒有問題。” 可火電廠發電機組停機限制出力的情況卻是不爭的事實,電廠、電力公司方面的解釋是因為“缺煤導致的結果”!問題的關鍵在哪里?一發電廠生產計劃部人士稱,煤炭價格上漲太快,“計劃電”用不起“市場煤”。 據了解,貴州電煤供應價格執行的是政府指導價,其中統配煤(國有)的價格從2001年的每噸100余元上漲到了今年初的145元(出廠價),統配煤在2003年,執行的價格為每噸133元(出廠價);“西電東送”配套礦井電煤出廠價為126元;小煤窯的價格也從當初的每噸80元(到廠價)上漲到2004年初的126元(到廠價)。從7月1日起,統配煤、配套礦井、小煤窯煤炭價格再上漲10元。分別為每噸155元、138元、136元。 該人士認為,貴州的上網電價低,每噸煤上漲10元,今年全省的電煤成本將因此增加2.6億元,這對全省發電企業來講,都是一筆沉重的負擔,發電企業承受不了。 不過,貴州一礦務局銷售部一負責人認為電廠在撒謊,“漲10元?再漲30元發電企業的利潤都很高!” 貴州省一電廠的內部資料顯示:2002年,該廠發電40.95億度,上網電價是0.178元,銷售收入是7.2億元。而該廠當年發電用煤180萬噸,全部是小煤窯的煤,每噸到廠價為85元,電煤成本為1.53億元,管理、工資、利息成本為1.2億元,稅前利潤達到4億元(但是該廠的資料顯示,利稅只有4700萬元)。 即便按照現在煤炭供應的最高價格155元計算,該電廠的利潤依舊豐厚,而且從7月1日開始,貴州省發電企業的上網電價已經上調,該電廠的上網電價為0.235元/千瓦時。 吳文學稱,標煤350—400克即可發一度電,通過折算,以最高500克發一度電計算,一噸煤至少可以發電2000度,銷售收入是470元,通常電煤成本占發電成本的75%,統配煤每噸155元(出廠價),加上30元運費及其它成本,每噸煤電廠獲得的稅前利潤為221元,即便維持原上網電價,也是109元。 既有利潤又不缺煤,那么發電企業停機限制出力的原因何在? “有煤,他們是不愿拿錢買煤,真正的原因就是想以此舉給政府施加壓力,阻止煤炭漲價并盤剝上游產業的利潤,以利于自己獲取高額壟斷利潤。”貴州煤炭行業一負責人直言。 這種觀點同時也得到了貴州省發改委官員及職能部門權威官員的認同。貴州林東礦務局副局長熊禮忠說:“過去電煤價格雖然也是實行的政府指導價,但實際上是沒法執行,2003年,林東礦務局賣給一些電廠的每噸價格只85元,比政府定價少了48元,小煤窯價格則更低,今年貴州電煤指導價是由省委常委開會決定,但每噸依然要少12元,現在又漲價,對于習慣了盤剝的發電企業肯定不適應。” 煤炭漲價,電廠停機也就在“情理”之中! 煤炭業處境 省內發電企業不愿拿錢買煤,而省外發電企業又急需電煤,于是貴州煤商選擇了外賣。 據了解,貴州今年電煤出省平均出廠價為每噸190元,貴州盤江煤電集團公司賣到廣西來賓B電廠的電煤,出廠價為215元。 貴州省煤炭管理局一官員透露,算上國家調撥煤,去年,貴州外出動力煤達到了3000多萬噸。 但是,煤炭外賣的通道并不順暢。2004年5月13日,貴州省物價局、財政廳、煤炭管理局聯合發文,沒有完成國家或者省內重點訂貨合同的煤炭企業,將控制其煤炭出省。為盡量減少煤炭出省,對出省煤炭每噸征收30至70元不等的煤炭調節基金,并用這一基金來平抑市場煤價。 “煤炭行業剛剛出現復蘇,生長的動力又被扼殺。”貴州某煤炭企業一負責人以此來表達對征收調節基金的不滿。 不僅行業對此有不滿情緒,與貴州有煤炭購銷往來的湖南、湖北、廣東、廣西、江西等省區也感到“不安”。 據知情人士透露:貴州征收煤炭調節基金剛一宣布,這些省區立即上書北京,“反對貴州搞地方保護”。到目前為止,調節基金都沒有得以執行。 7月20日,一可靠消息稱,貴州幾大部門又在醞釀此事。“不管結果如何,在完成任務的情況下,即便多賺5塊錢,我們也將選擇外賣。”上述煤炭企業負責人說。 貴州煤炭企業在努力爭取外賣通道的時候,也在試圖通過各種途徑解決與發電企業之間的一些“恩怨”。 7月14日,貴州省煤炭管理局向省經貿委、省政府辦公廳報告:清鎮電廠在煤款結算中存在許多問題,已經嚴重影響到煤炭企業供應電煤的積極性。 報告稱,清鎮電廠長期拖欠2004年度以前貸款不予歸還,其中水城礦業集團公司275.3萬元,六枝工礦集團公司110萬元,林東礦務局1966.2萬元。另該礦務局還通過法律手段索賠金額2238萬元(其中代墊運雜費1838萬元,利息400萬元)。 據知情人士透露,拖欠煤款的不只清鎮電廠,其它部分電廠也存在這方面的問題。 “政府制定的指導價不給足,企業代墊費用也不給,煤炭外賣又要受到諸多限制,如果電廠再不解決這些問題,我們也將采取措施應對!”一煤礦負責人表示,停止供煤是誰也不愿看到的。 畸形產業結構 貴州的供煤結構原本是大礦作為主導,小煤礦作為調節,現在已經完全倒置。今年上半年,貴州產煤4025萬噸,其中大礦只有800萬噸,其余全部是小煤礦生產。 “煤炭產業的畸形結構,與電力企業有很大關系。”貴州省煤炭管理局一官員認為,這一點從電煤合同的執行情況可以看出。 該官員稱,每年電煤訂貨會上,發電企業都是爭著要國有大礦的統配煤,這有兩大好處:發電企業在核算成本(包括上網電價調價)時都是以統配煤價格記入,但電廠簽下合同后,并不購買或者少買大礦統配煤,而是去大量購買小煤礦的煤炭,因為價格便宜,賺取利潤差。其次是保障自己的原料供應,一旦小煤礦的供應跟不上,電廠就要按合同辦事。 “后果就是,大煤礦的合同電煤在短時間內沒法外運出去消化(煤炭現在還是計劃運輸),長此以往,大煤礦的發展滯后,小煤礦發展超前并成為主力。”該官員說。 對主管部門來講,目前批不批小煤礦已經成為了一個難題———不批,電煤供應沒法保證,批了不利于大礦發展。而且安全事故、生態環境等問題開始凸現,整個產業結構發展出現失衡。 而更令人主管部門擔心的是,當小煤礦在煤炭開采中占到主力地位的時候,對電力能源的穩定也產生了諸多不穩定因素。從2001年開始,貴州省就已經推出了“大煤保大電”戰略,并相繼投資建設了中嶺煤礦、五輪山煤礦、林華煤礦、龍鳳煤礦等大型煤礦。但是,尷尬依舊存在。 中嶺煤礦是為納雍電廠配套而修建的,年產300萬噸,一期工程去年底完工,年產能力為100萬噸。 納雍電廠一年耗煤330萬噸。在今年初的訂貨會上,按分配指標,納雍電廠應該吸納中嶺煤礦60萬噸煤,其余的270多萬噸都是在小煤礦購買。據貴州省煤炭管理局一人士透露,納雍電廠答應中嶺煤礦購買55萬噸都是迫于壓力而簽下的合同!據透露,到6月底,納雍電廠在中嶺煤礦所購電煤為10多萬噸,此時電廠的煤炭庫存已經達到了14萬噸,于是,“電廠向中嶺煤礦提出不要煤炭了”。 “專門為電廠建的煤礦,都不靠近鐵路沿線,電廠不要,生產出來的煤怎么辦?”該人士說,這是一個棘手的問題。 出路在聯營? 當煤電之爭這種“新仇舊怨”矛盾無法調和的時候,貴州也開始寄望于走煤電聯營路子來化解雙方的“恩怨”。 中嶺煤礦便是其中之一,由貴州水城礦業(集團)公司、山東兗礦集團貴州能化公司、水城鋼鐵(集團)公司和貴州電力公司等共同出資開發。 林東礦務局也先后與貴州能發公司(貴州金元電力公司控股,金元公司擁有習水電廠、納雍電廠、發耳電廠等發電企業,與貴州省電力公司有著極深的血緣關系)投資開發了桂箐煤礦、林華煤礦,與中國華電集團投資開發了平壩煤礦。 但是,聯營之路也沒把煤電之間的深層矛盾消化。林東礦務局一人士稱,“煤電聯營從表面上看似乎解決了電煤供應的問題,但這種聯營只是滿足了局部利益,而不能解決煤電之間根本的問題。如果國家金融機構能給煤礦企業貸款,我們也不愿與電力企業合作,我們的資源,電力可以進來,為什么發電企業不讓我們進去?” 電力與煤炭之間不管是聯營還是互相滲透,就能化解電煤之間的恩怨嗎?這又會不會形成新的壟斷和不公平? 貴州省社科院一研究員稱,這是一個需要實踐來回答的命題。
|
| 新浪首頁 > 財經縱橫 > 滾動新聞 > 正文 |
|
| ||||
| 熱 點 專 題 | ||||
| ||||
|
|
新浪網財經縱橫網友意見留言板 電話:010-82628888-5173 歡迎批評指正 新浪簡介 | About Sina | 廣告服務 | 聯系我們 | 招聘信息 | 網站律師 | SINA English | 會員注冊 | 產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4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