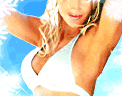|
□ 王家新
1960年初夏,美國(guó)著名的文學(xué)雜志《巴黎評(píng)論》發(fā)表了《三訪帕斯捷爾納克》,訪問(wèn)者奧麗嘉·卡里斯萊,一位美籍俄羅斯文學(xué)女性,她的父親也是一位作家,并和帕斯捷爾納克本人認(rèn)識(shí),而她的祖父為十九世紀(jì)末俄國(guó)著名作家列昂尼德·安德列耶夫。
多年前,我在烏蘭汗譯的帕斯捷爾納克的回憶錄《人與事》的附錄中讀到這篇訪問(wèn)記,便為它深深吸引。這是我所讀到的最有獨(dú)特價(jià)值和魅力的文學(xué)訪談。我甚至每過(guò)幾年都要把它找出來(lái)看一看,就像一個(gè)人渴望呼吸到某種空氣一樣。的確,這不是一般的訪談,這是精神的敘事,是兩個(gè)靈魂的相遇。它所散發(fā)的氣息,它的那些涌動(dòng)的潛臺(tái)詞,甚至使我想起了《日瓦戈醫(yī)生》中男女主人公的這樣一段道白:“現(xiàn)在我和你是這幾千年來(lái)世界上所創(chuàng)造的無(wú)數(shù)偉大的事物中最后的兩個(gè)靈魂,正是為了懷念這些已經(jīng)消失的奇跡我們才呼吸、相愛、哭泣,互相攙扶,互相依戀”。
這也就是為什么奧麗嘉由一開始的怯生生的探訪(因?yàn)榕潦献≡谶h(yuǎn)離莫斯科的別列捷爾金諾,而且不愿意會(huì)見來(lái)訪者),到最后居然從心中涌起了一種“幸福感”的最根本的原因。別列捷爾金諾之行使她滿懷感激地意識(shí)到這一點(diǎn)。因此她不僅將她對(duì)詩(shī)人的印象,也將她自己最隱秘的個(gè)人感受不無(wú)勇氣地寫了出來(lái):“我還清清楚楚地記得,當(dāng)時(shí)我感到何等的幸福……我們就這樣坐了兩個(gè)小時(shí)或更久一些,我希望這種時(shí)間能夠延長(zhǎng)下去,再延長(zhǎng)下去……”
這種情感的涌動(dòng)是在第三次探訪期間,當(dāng)時(shí)詩(shī)人剛剛結(jié)束早上的散步(穿著一身藏青色運(yùn)動(dòng)服,而不是中國(guó)的文學(xué)小青年所想象的那種風(fēng)衣),而她被請(qǐng)進(jìn)陽(yáng)光明媚的二樓上的書房。這當(dāng)然不是那種盲目崇拜,而是建立在一種深刻的相互認(rèn)知上(第一次見面,她就意識(shí)到莫斯科文人圈中關(guān)于帕氏的傳言是多么荒謬,什么“陶醉于自我形象”啦,什么“自我中心主義”啦……),因此,這種情感的涌動(dòng)會(huì)在這次訪問(wèn)的最后再次出現(xiàn),雖然它帶著告別——也許是永別的意味:“我已經(jīng)走下門廊,踏上了小路,他又叫我了一聲。我趁機(jī)又停下了腳步,感到幸福,我回過(guò)頭去,最后望了望帕斯捷爾納克……”
奧麗嘉來(lái)得太遲了。奧麗嘉來(lái)得正是時(shí)候。她來(lái)得正是“獲獎(jiǎng)風(fēng)波”(1958年帕斯捷爾納克因《日瓦戈醫(yī)生》獲諾貝爾文學(xué)獎(jiǎng),隨即遭到當(dāng)局的嚴(yán)厲批判和指責(zé))尚未完全過(guò)去、詩(shī)人有太多的話要對(duì)一個(gè)可信任的人講的時(shí)候;她來(lái)得正是詩(shī)人步入人生的晚年,要回首歷史并清點(diǎn)自己的一生的時(shí)候。對(duì)她自己更重要的是,她來(lái)得正是她需要理解什么是人生的意義和價(jià)值、什么是俄羅斯知識(shí)分子最優(yōu)秀的品質(zhì)的時(shí)候。因此,訪問(wèn)記中這種情感的坦露和涌現(xiàn),雖然引人暇想,但卻不可混同于一般的羅曼史。它帶著一種靈魂之間無(wú)言的理解,帶著一種真正稱得上是“純潔”的精神的氣息,也帶著人的高貴和尊嚴(yán)。別列捷爾金諾之行是一次精神之旅,對(duì)每一個(gè)讀到它的人,也將是一種照亮和提升。
奧麗嘉就這樣寫下了她的訪談,同時(shí),她也被詩(shī)歌所書寫的——那遠(yuǎn)離莫斯科的雪中的開闊小鎮(zhèn),那座處在鄉(xiāng)村路拐彎處的棕色的有云杉作背景的房子,那忐忑不安推開的花園與道路之間的柵欄門,那懸掛在墻壁上的出自詩(shī)人父親手筆的托爾斯泰、斯克里亞賓、拉赫馬尼諾夫的肖像畫,那緩緩穿越積雪山坡和墓地(它看上去“宛如夏加爾油畫中的背景的一個(gè)小角落”)時(shí)的交談,那行經(jīng)結(jié)冰路面時(shí)的細(xì)心攙扶,那由詩(shī)人本人端到餐桌上的橘子(“我有一種奇異的感覺(jué),似乎我已經(jīng)吃過(guò);帕斯捷爾納克的作品里經(jīng)常出現(xiàn)橘子——在《日瓦戈醫(yī)生》開頭部分,在早期的詩(shī)里”),那種七旬老人如同年輕人的精神煥發(fā),那回首一生時(shí)內(nèi)心的某種迸發(fā)(“茨維塔耶娃的死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悲痛”),那種寫作《日瓦戈醫(yī)生》時(shí)盤居在詩(shī)人心頭的巨大的“欠債感”,那走出車站、臨近詩(shī)人住房時(shí)突然刮起的暴風(fēng)雪(“我看到雪花像海浪一般層層飛過(guò)……再過(guò)幾分鐘,我將跨進(jìn)他的家門,聽到他那詩(shī)一般的語(yǔ)言,真覺(jué)得不可思議”),當(dāng)然,還有那種從內(nèi)心深處涌起的幸福感,那種對(duì)生命、對(duì)大地和星空的感恩之情,將伴隨著奧麗嘉乘上返回莫斯科的火車,也將伴隨她回到更遙遠(yuǎn)的另一個(gè)世界。這些,將成為她一生中最珍貴的記憶。它們將被書寫下來(lái),但仍將是她最隱秘的記憶。
那么,帕斯捷爾納克本人又如何呢?也許這就是所謂“命運(yùn)”:奧麗嘉的這篇訪問(wèn)記,詩(shī)人本人并沒(méi)有來(lái)得及讀到,就在它發(fā)表的前兩周,1960年5月30日,詩(shī)人因癌癥在莫斯科一家醫(yī)院逝世(“昨天無(wú)與倫比的聲音落入沉默/樹木的交談?wù)邔⑽覀冞z棄/他化為賦予生命的莊稼之穗/或是他歌唱過(guò)的第一陣細(xì)雨……”阿赫瑪托娃《詩(shī)人之死》)。死前他是否惦念過(guò)遠(yuǎn)方的那個(gè)訪問(wèn)者呢,我們不知道。我只是知道他曾寫過(guò)令人難忘的詩(shī)句,來(lái)描述那種曾照亮他的、給他生命帶來(lái)新生的美麗女性。
帕斯捷爾納克,1890年2月生于莫斯科。1912年赴德國(guó)馬爾堡大學(xué),研究新康德主義學(xué)說(shuō)。1914年,出版了第一部詩(shī)集《云霧中的雙子星座》。1958年,他因小說(shuō)《日瓦戈醫(yī)生》受到嚴(yán)厲譴責(zé),過(guò)著離群索居的生活。1960年5月,在莫斯科郊外彼列杰爾金諾寓所中逝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