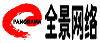世界新貨幣博弈:要有長期應對美元風險策略
劉艷妮 張 航
將于4月2日在英國倫敦舉行的G20峰會備受社會各界矚目。會議尚未召開,許多國家就提出了改革國際貨幣體系建立超主權儲備貨幣的要求。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提出“創造一種與主權國家脫鉤、并能保持幣值長期穩定的國際儲備貨幣”。這一言論立刻引起了全球的關注。
金融危機下的美元霸權
雖然布雷頓體系已經終結,但美元仍是無可爭議的國際貨幣,美元占全球外匯儲備的64%(歐元27%,英鎊5%,日元3%)、外貿結算的48%和外匯交易結算的83%。
美元具有主權國家貨幣和國際貨幣雙重身份。作為主要的儲備資產,美元的國際供給與國內供給混合在一起,它由美聯儲決定,缺乏內在的自發約束,美國可利用其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優勢地位,采取不負責任的單獨行動或脅迫其他國家配合其行動,將國內經濟問題與矛盾外溢和轉嫁給其他國家。當美國出現經常帳戶逆差時,可以通過印刷美鈔來彌補赤字,既可減輕外債負擔,刺激出口,又可維持國民經濟的平衡,將通貨膨脹轉嫁給其它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美元貶值10%,即可導致相當于美國GDP的5.9%的財富轉移到美國。僅在1985年3月至1986年3月的一年間美元貶值就減少了美國約三分之一的債務。20世紀80年代,“廣場協議”迫使日元經歷了長達10年的持續升值過程,日本在80年代對美國的貿易順差的總和幾乎都賠了進去。20世紀90年代末,歐元進入流通,對美元的唯一世界貨幣地位構成威脅,美國就以1999年科索沃戰爭為契機,造成歐元前景模糊不定,對美元一度貶值,歐元信用大為削弱。2003年歐洲經濟剛剛有所復蘇,美國有意無意的釋放多年來的經濟風險,立即造成歐元匯率一路走高,對美元匯率一度達到1.6,歐盟的出口競爭力再遭打擊。美國就是這樣利用美元貶值一方面來吸納全球財富,另一方面利用貶值來擊潰別國貨幣和經濟。
要有長期應對美元風險策略
作為美國國債的最大債權國,同時也是美元儲備最多的國家,中國無疑是美元貶值最大的受害者。首先是伴隨美國政府債券收益率下降而降低的7400億美元(相當于美國國債總額的6%)國債的投資收益率;其次是美元持續貶值之后中國龐大的美元儲備所蒙受的長期性匯兌損失。不僅如此,美元貶值也將帶動人民幣的被動性升值,令中國出口遭遇更大的市場阻力,這對于中國出口導向型的經濟增長模式無疑是重大打擊,如果不及時應對,美元貶值將成為新的妨礙中國經濟今年“保八”增長的因素。近來財政部和國家稅務總局決定,自4月1日起再次上調出口退稅率,這是去年下半年以來,中國第六次上調出口退稅率,共涉及紡3802個稅號。無論是美元儲備投資,還是出口退稅,損失都由中國政府承擔了,這一政策也是出口加工型國家的必然選擇。
當然,出口退稅不可能成為長久之策。對中國來講,在人民幣升值背景下,依靠廉價勞動力和低成本資源進行簡單加工,打價格戰的模式已經越來越不現實,必須盡快利用這一契機實現產業升級。
建立世界新貨幣是艱難的博弈
周小川在G20峰會即將召開之際提出“超主權貨幣”的主張,超主權儲備貨幣不僅克服了主權信用貨幣的內在風險,也為調節全球流動性提供了可能。IMF1969年創設的特別提款權(SDR)便具有超主權貨幣的特征和能力。應該由一個值得信任的國際機構將全球儲備資金的一部分集中起來管理,并提供合理的回報率吸引各國參與,對投機和市場恐慌起到更強的威懾與穩定效果。對于參與各國而言,也有利于減少所需的儲備,節省資金用于發展和增長。當一國主權貨幣不再作為全球貿易的尺度和參照基準時,該國匯率政策對失衡的調節效果會大大增強。這些能極大地降低未來危機發生的風險、增強危機處理的能力。當然,SDR能否順利承擔這一重任還需要經受制度安排、技術處理、各國博弈等多重考驗。
兩次世界大戰淘汰了金本位;“特里芬”困境解體了布雷頓森林體系;牙買加體系雖然被稱為“沒有體系的體系”,但實質是美元主導的“影子體系”;這次次貸危機能否終結美國的“世界央行”地位?完全的牙買加來了么?這些都將是一場艱難的博弈。但我們應該知道,每一次世界主導貨幣的選擇都是歷史選擇的必然結果,并不以任何個人和個別國家的意志為轉移。而在這場大博弈的棋局中,只有以實體經濟為重的中國才是以虛擬經濟為重的美國的對手。博弈的目標不是分出高低輸贏,而是要達到雙贏和多贏,這將是一輪超高智力的較量。這是一個增加中國在國際舞臺上話語權的時代,也是考驗中國領導人的大智大勇的時代。
(作者均系中央財經大學金融學博士)
新浪聲明:此消息系轉載自新浪合作媒體,新浪網登載此文出于傳遞更多信息之目的,并不意味著贊同其觀點或證實其描述。文章內容僅供參考,不構成投資建議。投資者據此操作,風險自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