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事會》封面文章:領導哲學的困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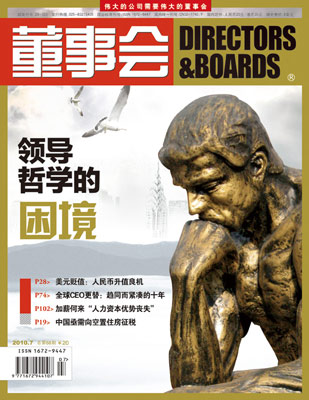
策劃:何玉梅
中國企業家在經濟高速增長的30年中獲得了極大成功,在短期內積累了驚人的財富,創造了無數世界級的“業界神話”。然而,處于而立之年的中國企業家群體卻陷入了一種后“富裕”時代的焦慮,掙扎于義與利、道與術的糾結,不知道財富的真正意義在哪里,困惑于領導力的日漸疲弱和企業生命力的缺失。這是一個時代的困境,是這個時代企業家精神和商業倫理迷失、社會文化心理脆弱的必然產物。
企業家的“騎士難題”
人的生命力和生命的光環是全然的兩回事。生命的光環再多,可能一丁點也換不來生命力!做公司同樣如此。可惜人們為著光環而在殘害生命
文/王育琨
騎士習慣了盔甲的光芒,卻沒有注意到盔甲已開始生銹。終于有一天,驀然驚覺,他已經深陷生命的危機而不能自拔。
《盔甲騎士》 是探索生命本質的鉆石般的杰作。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心地善良、充滿愛心、堅毅勇敢的騎士,他鏟除惡龍、拯救危困中的公主、備受世人推崇,為此,國王賞賜他一套閃亮的盔甲。騎士非常喜歡穿上盔甲,他漸漸習慣了人們的詫異與贊揚,習慣了盔甲帶來的力量與安全感,習慣了盔甲所散發的神秘與光芒,習慣了盔甲塑造的另一個自我,那個可以隨時躲避世人包括他妻兒的自我……久而久之,騎士習慣了盔甲的光芒,卻沒有注意到盔甲已開始生銹。終于有一天,驀然驚覺,他已經深陷生命的危機而不能自拔。一直以拯救他人為己任的騎士,居然自己陷入了嚴峻的生存危機。
企業家危難的哲理
騎士的難題,與我們那些正在經受磨難的企業家之命運何其相似!企業家,尤其是那些成功企業家,曾經影響了數不勝數的事件,榮譽、秘籍、成功、果斷、進取等等光環加身,讓他們有了一覽眾山小的豪邁,同時也落下了身置于人群中的孤獨與落寞。站在高處的企業家們,其高大、陽光、優雅的一面,受到媒體與公眾的傾慕。
可是誰又知道,企業家正遭受著怎樣的沒人理解的孤寂與身負重荷的彷徨。企業家們的雙重人格究竟造就了怎樣的一個傲慢者、一個抑郁者或一個破壞者?企業家們的雙重視野究竟讓他們陷入了怎樣的落寞,或贏得了怎樣的靈感與精神明辨力?他們是否也像山上的樹一樣,愈求升到高處和光明,它的根就愈掙扎向下,向地里,向黑暗,向深處?我們這些山下人不得而知。他們不像常人,可以隨意向人訴說苦悶,小心翼翼或大大咧咧地化解掉任何一點兒危險。
企業家的定位與潛規則,使他們面對任何苦悶和無奈時,只有自己消化,很少有人可以為之緩解或分擔。久而久之,一種巨大的不安全感襲來,形成他們懷疑一切人的心理機制。他們沒有傾訴對象,甚至佛或上帝也不與他們同在,所有的難題只能在一個狹小的空間里化解。于是,他們紛紛穿上已有的或現成的盔甲,或日夜由生猛的保鏢護衛,或一味將繁雜的業務纏于一身,或進入不知為誰忙亂的債滾債的泥沼,或干脆就患上抑郁癥,陷入了深深的生存危機……自殺與非正常死亡的數目,很是驚人。
固然,虛榮心、膽大妄為、虛偽的羞愧、豪賭的果斷、無盡的貪欲、信仰的迷失等在很大程度上是造成這一切的原因,但是又有誰曾探究過這些受到創傷的人們的內心深處,并了解過他們隱藏在內心深處而不為外人所知的奧秘呢?在那漫長的歲月里,他們的家人、朋友、公司同事、社會的智者等,本來是能夠發現、捕捉、探聽出這些人心靈中的某種奧秘,以理解和緩沖其內心的煩惱和痛苦的,但人們卻沒有這樣做。
企業家艱難攀登上了眾人向往的無限風光的峰頂,還沒來得及陶醉喜悅,旋即被那里冰刀一樣的寒冷、稀薄的空氣、不見底的懸崖等窘境所迫,于是便想走下山來。可是,他們卻找不到插足的地方。而且,他們原來上山時住過的客棧此時已經沒有了他們的容身之地。因為,一種不平衡的情緒在醞釀、生成與膨脹。企業家們的出類拔萃,成為一些人的眼中釘———這些人要在思想上、理論上、輿情上將企業家們摧毀,有時甚至要摧毀其肉身。好像企業家就應該承受高風險,就應該為自身的出類拔萃埋單,就應該為取得財富付出代價。顯然人們忽視了這些企業家也是人,也有脆弱的情感,也存在承受的極限。
2400年前,柏拉圖在《裴多篇》中說出了千古難解的話:“真正愛好哲學的人,無不追求著死亡和死。”這很可能不為他人所理解。危難、壓力、陰謀、成功、失敗、無聊與孤獨,使企業家或多或少地在某個時刻,能夠聽到內心深處的一個聲音———“生就是死,死就是生”。他們深知看破“生死之門”是一種內在的情愫,是絕對不能說出來的,因為即使說出來,也沒有人相信這樣的話。死亡有自己的真理,自己的明顯性,自己的可能性與不可能性,并且不容忍我們的尋常觀念,我們也很難理解死亡。只有特異之人,在精神極度興奮的罕見時刻,才能聽到和理解神秘的死亡語言。
企業家危難的哲理,要比人們想象的更為深奧。
“天職精神”也迷失
企業家都有一種創富的“天職精神”。天職精神也迷失。
“天職精神”,是馬克斯?韋伯所概括的資本主義精神。在傳世著作《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一書中,他沒有明確界定資本主義精神,但是他的敘述表明,個人有增加自己資本的責任,而增加資本本身就是目的。精于職業,精于賺錢是一種美德。這種美德同時與這樣一個詞語相聯——“天職”。韋伯說:“一個人對天職負有責任乃是資產階級文化的社會倫理中最具代表性的東西,而且在某種意義上說,它是資產階級文化的根本基礎。”
韋伯為自己的邏輯深深擔憂。他明白,當竭盡天職已不再與精神和文化的最高價值發生直接聯系的時候,或者從另一方面來說,當天職觀念已轉化為經濟沖動,“價值理性行動”也就轉變成“工具理性行動”時,那時就沒有自由的人了。韋伯悲哀地說:“沒有人知道將來是誰在這鐵籠里生活;沒有人知道在這驚人的大發展的終點會不會又有全新的先知出生;沒人知道會不會有一個老觀念和舊思想的偉大再生;如果不會,那么會不會在某種驟發的妄自尊大情緒掩飾下產生一種機械的麻木僵化呢,也沒人知道。因為完全可以,而且是不無道理地,這樣來評說這個文化的發展的最后階段:專家沒有靈魂,縱欲者沒有心肝;這個廢物幻想著它自己已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
韋伯的預言不幸應驗了。肆虐全球的金融危機,是韋伯描述的“驚人大發展”的邏輯結點。就是交易所這樣明明白白的公共機構,都可以被執掌者用來為自己巧取豪奪1800億美元的財富,所有那些不可一世的投行,都大睜著眼指鹿為馬、虛增市值。全球都在反思。
韋伯100多年前為資本主義梳理尋找到的那束光,顯然不夠強盛,照不到那些陰暗的地方,人們容易在那里折戟。一個人冥冥之中都有一盞燈,忽明忽暗,導引著你人生的旅程。要成為什么,要到哪里去,那是在你困頓時給你勇氣和希望的東西。從那里開始,有一種深深的內在的自覺,那是你做人做事原初的動力。失去了那樣一盞燈,無可避免會導致世間亂象人間悲劇。
物質財富那束光還不夠照耀萬千公司。現代人在財富之外,終于認識到了生態。只有從大生態的觀念上,照看你的人生和你的公司,才不至于出大錯。大生態的觀念,也就是中國國學中“天人合一”、“天人一也”的思想。尋求人的發展,發展人,是一切發展的旨歸。發展人,就是造就發展天人合一的整體人。造就整體人,正是中國古老的教育傳統。
現實中,每個人都在追求財富、權力和名望。那是生命的光環。有了那些耀眼的光環,生命看上去充滿了色彩和美麗,生命力也似乎得到了張揚。可是,那畢竟只是光環,而不是生命本身。我們往往不會去區分什么是生命力,什么是生命的光環。發生在商界的一波一波并購,大多是為了公司規模(或光環)而發出的一次次沖擊,有太多的公司因為“黃袍加身”喪失了生命力,而最終歸于失敗。
生命是找尋,不是欲望
無論是老子、莊子,還是耶穌、佛陀,無論是古希臘文明,還是東方文化,一切都是生命體驗的結晶。這些人類經典文化的結晶,是由無數鮮活的生命所體悟出來的。正因為有體驗,每個人都能發現真理,都能悟到真理。
我一直在尋找公司生命的本真。生命的光環和生命力,公司的規模和公司生命力,這是長期困擾著我而沒有解開的疙瘩。去年在穿越西藏雅魯藏布江大峽谷無人區時,這個一直糾纏不清的問題,豁然開朗起來那次,我們去了6個人,跟了12個藏族背夫。其中一個名為貢覺吐旦的小伙子給了我深刻的人生啟示。
我們一行6人。其他5人都是卓有成績的企業家。在原始森林里,我們一個個都放下面具,見到美景大聲呼喊,遇到險情心驚膽顫,走路生活相互幫助。在原始曠野中,我們6人盡情地享受著生命的歡樂。
貢覺吐旦從來沒有意識到他會有什么哲學。對他來說,那就是他的呼吸和飲食,再平常不過。我回想起來,這短短的幾天,貢覺吐旦給了我多層面的啟迪。
敬畏因果,接受死亡。在西藏同胞看來,生和死是一體的,他們是同一個現象的兩面。你的肉身只是一個皮囊,暫時作為你的心識或靈魂的寓所,就跟人出差住酒店差不多。當靈魂離開皮囊,生命還在繼續,生命有了一個更新的開始。一旦你接受了死亡,就會有很多東西立刻被接受。你的焦慮、憤怒、恐懼、仇恨、不安也跟著就走了。這時,你就有了具足的智慧,做好當下的事。現在關注生活,將來才會積聚改變生活的力量。
眾生平等。“大家都是一條命,都是來鍛煉身體的”。不管你是幾十億身家的企業家,還是一個少不更事的藏族背夫,大家眾生平等。有了眾生平等的意識,看人、看事都容易達觀。很享受貢覺吐旦的平等意識。有了這樣的意識,才可以見到權力多高的人都不會打顫,見到富可敵國的人也會感嘆他生命的負累,見到名望蓋世的人也會看到他的速朽,見到無家可歸的乞丐也會感到生命的尊嚴。有了這樣的意識,才可以少受一點中國封建官僚文化的侵害,而能守住自己成就一個自立立人的大我。
自立立人。貢覺吐旦看上去有點冷漠。我在南京國際關系學院演講在說到貢覺的時候,一位年輕的軍人站起來說,他絕對不會像貢覺吐旦這樣沒有愛心。他會義不容辭地沖下去接應那個遇到困難的人。這里沒有對錯。下去接應有下去接應的道理,不下去接應有不下去接應的道理。不存在誰對誰錯,都在傳遞一種生命的情懷。
后來那位企業家登上山,看到我們很激動也很開心,一個個擁抱我們。他沒有絲毫對我們沒有等他或沒有接應他的不滿。從他夸張的動作中,分明炫示他為自己終于克服了巨大的困難而登頂感覺自豪。這種自豪是貢覺吐旦給他的。如果真是有人下去接應他了,他會失去成就感和樂趣。他能在人生的舞臺上走到今天,那是碰到了數不清的困難。每當困難降臨,他都坦然接受,并在沉靜中找出化解的招數。這就是他的生活權利,沒有人可以去改變。
生命力和生命的光環。貢覺吐旦一下子就把人生與財富和地位區別開來。西藏廣袤的大自然給了貢覺吐旦一種堅定的信念:在生命的天平上,財富和地位沒有任何作用。看上去它們威力無比,實際上半點生命也買不回來。這是西藏之旅貢覺吐旦給我最強烈的震撼。
在城市的喧囂中,我們自以為抓住了一切的核心——權力和財富,以為那會為我們的生命帶來滋養。但是在追求財富和權力的同時,我們卻忽視了或損害了那種原生的生命力!那些英年早逝的企業家、體育偶像以及顯要人物,他們的光環足夠多,他們的財富和權力足以讓他們享受到世界上最好的醫療。但是,卻不可挽回地逝去了。
這一切都是我們不懂生命。過分害怕死亡的人,會變得害怕生命。于是他們開始搜索那些不死的東西,一座大的皇宮,摩天大樓,超大的企業規模,無數的金錢,無上的名望,以及所有那些不會死的東西。而實際上所有這些東西都是過眼煙云,轉瞬即逝。因為他們跟生命力半點關系也沒有。相反,他們可能是生命的一種負累,甚至可能是生命的殺手。
在布滿原始森林的大山里,在大自然的嚴峻環境里,任何財富、名位、權力都無足輕重。在這里只崇尚鮮活、頑強的生命力!那些企業家可以有驕人的事業和財富,但是在這里,卻不得不獨自面對生命力的考驗!
生命是一個找尋,不是一個欲望,不是一個想要成為比爾?蓋茨或奧巴馬的野心。而是茫茫天地間去找出“我是誰”。我一直在找尋。久思不得其解的問題,讓貢覺吐旦給一語道破:人的生命力和生命的光環是全然的兩回事;生命的光環再多,可能一丁點也換不來生命力!
貢覺吐旦的生命力視角,不只是可以看人生,更可以看公司。公司也是生命。一個公司在初創時,大都有著充沛的激情和熱忱,每個業務現場都有著旺盛的創造力。然而,隨著規模的擴大,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也隨之開始滋生,公司就漸漸失去了活力,走上衰退之路。公司的一個個業務現場,不再有頭拱地解決問題的大頭兵了,而學會了逐級把問題上交。一層層高管看到問題,說了就等于做了,強調了就等于落實了。創始人面對親手建立的組織,往往束手無策。
束手無策的不只是中國公司。這是世界公司史上難于逾越的一個怪圈。從通用汽車到日本航空,一連串大公司的破產,讓正在忙著并購的人們警醒:公司的生命力與公司規模沒有什么關系!公司的真正生命力,不在于公司的規模,而在于一個個業務現場,還有沒有突破能力,可以給公司帶來豐厚的利潤。說起來很容易,但是真正能夠看到他們之間的區別,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戴志康的天問
企業家經歷了破冰時代的原始積累,創建了傲人的企業帝國,攀登上人生的高峰。在創造財富的勞動過程中,他們“頭拱地”往前走,品味到了充實與幸福。可是面對財富的金山,如何消化和傳承,卻讓他們有點找不到北了。
當然,他們之中有清醒者。上海證大集團董事長戴志康就是這樣的清醒者之一。戴志康1994年創建上海證大,1995 年借“3?27”國債事件完成原始積累,之后在資本市場風生水起,1999年高潮時全身退出股市轉戰房地產開發。有人稱他為行業的路標。“戴志康在哪里,那個行業必火。”他用8年時間將自己的財富由零變為10個億,再用6年時間將財富由10個億增至100個億。
他收藏了世界級的現代雕塑“大拇指”和“LOVE”,他創造了“現代中式”的建筑風格,他和許多中國當代藝術家過從甚密,他投資創辦了國內首屈一指的民營藝術館上海證大現代藝術館……別人問及他的身份時,他總是強調說,“我只是個商人,”但是,他又一直強調,“我從來不是個純粹的商人。”
戴志康替天發問。當年,面對“明暗不分混沌一片”,屈原發出了震撼古今的天問。當今,面對成功的陷阱、富士康12跳、礦難、金融危機、砍殺兒童、房價糾結等一波波迷迷蒙蒙現象,商人戴志康跳出利益的糾葛,心存敬畏,在新作《用社會注意方法應對房價過高》中,發出新“天問”:“我的財富是否可以保住并增長,還可以翻幾個跟頭,多長時間可以讓我們翻跟頭?財富是否可以使自己的日子過得更好?幸福在哪里?”“我天天那么辛苦,忙得昏天黑地,我比以前更幸福了嗎?”“財富不斷地增長,到底帶給我們什么?財富從哪里來?會到哪里去?”“財富到底是什么?什么東西是人類的財富?中國人再努力30年,我們積累的財富是什么?我們到底積累什么?”“邏輯不是那個天,邏輯上面有更重要的東西,邏輯后邊是什么?”“劉翔和姚明是體育明星,是最有肌肉的人,應該說是最健康的。但是,他們兩個總是被不健康、不平衡困擾。他們到底是健康平衡的人還是不健康不平衡的人?”“一味增長,就是像姚明、劉翔,已經不可能再得冠軍了,還非得讓他去跑,過了這個時間了,對不對?”“有必要總是講經濟增長嗎?”“美好世界在哪里?美好世界什么樣?”
用“老天”的眼,來看混沌的現實,戴志康有了別樣的清明。他平心靜氣,用最平實的語言,把一個個看似無解的復雜事物,化解成一兩個簡單的問題。一下子便讓人豁然開朗。
用劉翔的亞健康來形容中國公司和中國經濟,尤其是用拼了命也去拿冠軍的魯莽,來言狀中國公司盲目追求規模的生存現狀,令人叫絕。戴志康站在了一個意識的高處,俯瞰著他過往的人生。
有時,天堂與地獄之間,就是一層紙。或許恰恰是因為我們通常沒有像戴志康那樣對比邏輯更高的那個“真北”(終極目標)傾注激情,在邏輯的演繹中錯失了整體。
心懷真北。注意力在哪,認知就到哪。戴志康關注人的幸福,關注美好世界,關注“真北”(True North)。“真北”是由Dr. David Cochran提出的一套方法論。分為終極目標(True North),目的(Functional Requirement),手段(Physical Solution),以及達成的尺度(Measure)。對分析復雜事物最大的誤區,就是掉進尺度或手段出不來。在戴志康的一個個天問中,注入了“真北”,便有了一種無人能及的力量。
戴志康看到美國鄉下人,那么肥,開著皮卡,吃著肥大牛排,喝著冰水,健身房運動。牛肉是過分的碳排放,制冰又是碳排放,到跑步機又是碳排放。經濟增長帶來的物質財富,只能使這個人群更腐朽和不健康,或者更不幸福。有必要總是講經濟增長嗎?
戴志康自問自答:“我們不能把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定階段的東西推而廣之,說全世界都要這個,不管什么時候都要那樣,這好像不一定有道理”。是應該從戴志康的“真北”,從人類和地球的命運出發,從“老天”的視野出發,問一問:有必要總是講經濟增長嗎?有必要對生命的光環過于癡迷、而忽略掉真實的生命嗎?有必要為了規模和利潤的極度膨脹而淡忘了人的生存和發展嗎?
心懷“真北”,戴志康超越了生命力與光環的糾結和困擾。更重要的是,我們會找到“美好的世界”。一如戴志康所說:“我的幸福來自勞動創造本身的過程,而不是消耗勞動的成果”。“上帝創造了物質,人類創造了精神和文化藝術。如果要尋找生活更大的意義,我們應該在勞動過程當中創造文化,創造藝術”。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