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企業家:逆境中盔甲騎士在尋找自己的救贖 | |||||||||
|---|---|---|---|---|---|---|---|---|---|
| http://whmsebhyy.com 2006年04月11日 17:49 《經理人》 | |||||||||
|
 “騎士忘記了,成功不是盔甲創造的,而是盔甲中的自己創造的。”李嘉誠悟出不少經商思維 文/王育琨 羅伯特·費希爾的《盔甲騎士》是探索生命本質的鉆石般的杰作。問世20余年經久不
每個人的盔甲 一直以拯救他人為己任的騎士,居然自己已經陷入了嚴峻的生存危機。 造成生命危難的,正是幫助他確立功名的盔甲。這套盔甲是國王賞賜的禮物,是用一種非常稀有、和太陽一樣閃亮的金屬所制成的。有些人發誓,曾看見太陽從東邊升起,從北邊落下。事實上他們看到的,不過是騎士而已。騎士非常喜歡穿上盔甲。他習慣了人們的詫異和贊揚,習慣了盔甲帶來的安全感,習慣了盔甲所塑造的神秘空間,習慣了盔甲給他帶來的榮譽和安全,習慣了盔甲塑造的另一個自我,那個可以隨時躲避世人包括他妻兒的自我。可是直到有一天,因為三年看不到他的真面目,他的愛妻要帶著兒子離他而去,騎士才意識到脫下盔甲的緊迫性。隨著而來的問題比想象中還嚴重。由于盔甲已經生銹,他請力大的鐵匠用斧子去砍他的盔甲,結果導致盔甲變形。他已經無法正常睡眠,已經不能正常進食,甚至不能正常喝水。他的生命已經受到了切實的威脅。于是,他不得不離開家門,這回不是去拯救公主或世人,而是去尋找自己的救贖,踏上了求生之路。 騎士的難題,與我們那些正在經受磨難的企業家之命運何其相似!企業家,尤其是那些成功的企業家,影響了數不勝數的事件,榮譽、秘籍、成功、果斷、進取等等素質加身,讓他們有了一覽眾山小的豪邁,同時也落下了沒有同路人的孤獨與落寞。他們不是常人,不可以隨意向人訴說苦悶,從而排解掉任何一點點危險。企業家的定位使他們超越了那些常人的情感。任何的苦悶和無奈,只有自己消化,沒有人可以緩解或分擔。久而久之一種巨大的不安全感開始向他襲來,形成了他們懷疑一切人的心理過程。他們沒有傾訴對象,甚至佛或上帝也不與他們同在,所有的難題只能在一個狹小的空間里化解。于是他們紛紛尋找已有的或現成的盔甲,或是日夜由生猛的保安護衛,或是有壓頂的業務纏身,或是進入不知為誰忙亂的債滾債的泥沼中,或是干脆就患上抑郁癥,陷入了深刻的生存危機。據中國企業家協會發布的《中國企業發展報告》稱,近二十年中,我國已有1200多名企業家因種種心理障礙走上了自殺之路。至于非正常死亡的數目,就更是驚人。 盔甲騎士,可以跟眾多智者交流,他們可以帶他走上一條求生之路。而我們的企業家,則沒有他那么幸運。他們沒有智者和法師指點,也很少得到被他們偶爾火爆傷害了的親人們的諒解。固然,虛榮心、膽大妄為、虛偽的羞愧、豪賭的果斷、無盡的貪欲、信仰的迷失等等,在很大程度上是造成這一切的原因。但是又有誰能說,他曾探究過這些受到創傷的人們的內心深處,并了解過他們隱藏在內心深處而不為外人所知的奧秘呢? 在那漫長的歲月里,他們的家人、朋友、公司同事、社會的智者等等,本來是能夠發現、捕捉、探聽出這些人心靈中的某種奧秘,以理解和緩沖這些人內心的煩惱和痛苦的。但他們卻沒有這樣做,根本就沒有這樣做過。企業家們艱難攀登上了眾人向往的無限風光的峰頂,還沒來得及陶醉登頂的喜悅,旋即被那里寒冷的水霧、稀薄的空氣、不見底的懸崖、沒有熱水飲食等的窘境所迫,只想拐下山來。可是,卻找不到插足的地方。而與此同時,一種不平衡的情緒同時在醞釀、生成與膨脹。企業家們的出類拔萃,成為一些人的眼中釘,他們要在思想上、理論上、輿情上把他們摧毀,有時甚至包括他們的肉身。好像企業家應該承受高風險,應該為出類拔萃埋單,應該為取得財富付出代價。人們忽視了這些企業家也是人,也有著脆弱的情感,也有著承受的極限。 2400年前,柏拉圖在《斐多篇》說出了千古難解的話:“真正愛好哲學的人,無不追求著死亡和死,這很可能不為他人所理解。”危難、風險與壓力,使企業家或多或少成為看破生死之門的哲學家。死亡有自己的真理,自己的明顯性,自己的可能性與不可能性。他們不容忍我們的尋常觀念,我們也不能理解它們。只有特殊的人,在精神極度興奮的罕見時刻,才會聽見和理解神秘的死亡語言。 企業家危難的哲理,要比人們想象的更為深奧。 尋找本我之路 世上的盔甲都是相似的。讓我們跟隨騎士踏上尋求去掉盔甲之路,去尋找本我。 一旦離開了自己的城堡,騎士發現吃喝都成了個大問題。他所能找到可吃的東西,只有偶而出現的野莓子,自己捏碎,塞進面盔里。惟一的喝水的方法,就是把頭放進小河里,讓他的頭盔里充滿水,有兩次,他差一點沒給淹死。經歷了幾個月的磨難,他接近了一個又一個真實:以前一直認為自己聰明絕頂,現在卻得千方百計地想在樹林里活下去,他覺得自己一點也不聰明,很多事都不懂,甚至分辨不清東西南北;是懼怕,讓他在當初穿上了盔甲,而不是什么征戰需要;一直認為他是世人的中心,最少也是妻子與兒子的主心骨和依賴,實際上妻子和兒子并不需要他。這一系列真相終于讓他做了一件多年來沒有做過的事—— 痛哭。哭泣,這種與騎士稟賦全然不同的軟弱代名詞,卻正是騎士脫離盔甲的第一步。騎士終于明白,“不能再像以前那樣的生活和思考。” 能夠直面真相,并且在不確定性之中果斷選擇決策,一直是企業家成功的要素。而誰又知道,這兩大長處常常又會成為企業家的真正短板。懼怕,正是我們那些果敢企業家的另一面。他們全副武裝。一種對人性根深蒂固的疑懼,一種對真相莫名其妙的害怕,已經緊緊地固住了他們。他們深知懷璧其罪。于是,他們更愿意呆在自己熟悉的空間里,一如苗建中龜縮在由防盜門和攝像鏡頭把持著的家里。 1998年5月,德州晶華集團董事長苗建中的弟弟苗建國被一名“黑社會”成員用鋼管砸死在德州街頭。之后苗立志為弟報仇,歷經兩年時間,終于協助公安人員將德州的“黑社會”老大王鐵流捉拿歸案。王鐵流后來被處以極刑,作惡德州20年的王氏黑幫由此瓦解,但苗因此一直擔心王的余黨報復。疑懼與恐懼交織,使他很少出門,通常都躲在家里辦公。2005年12月1日12點半,苗被發現上吊身亡,一個字的遺書也沒有留下。警方明確認定他是因患抑郁癥自殺。據警方調查,當天上午,苗還與三個客戶通過電話。三人均反映苗總通話時語氣平和,和往常并無二樣,談的都是工作上的問題。出事前一個小時,苗還在電話中詳細地指導一位開礦山的客戶如何布局生產場地、如何提高開采效率。沒有人可以在電話的聲音中捕捉到真正的苗建中。人們低估了弟弟的橫死對苗建中的影響。他不會讓人們看到這一點。他發現掩飾自己最好的方法是與人隔絕。一個虛擬的網絡世界,幫他了解著社會,研讀MBA,卻能同時割斷無味的打擾。神秘感成為他銳利的武器。他不愿意出門,已經看透了厭煩了各種嘴臉。他學會了用聲音塑造的平靜,以至于在生命的最后關頭,他還能夠壓得住,讓人聽上去,宛如通常的平靜。可是,那是萬念俱灰的平靜呀! 做企業的成功,帶給他無上的榮譽和無盡的責任,同時也帶給他如履薄冰的緊張與精神崩潰的臨界點。為著千千萬萬個苗建中,我們還要跟隨騎士繼續上路。 “沉默之堡” 騎士要過的第一關是“沉默之堡”。那是一座全然寂靜的城堡,甚至連壁爐里的火,都沒有發出劈哩叭啦的聲音,只是無聲無息的燒著。他必須一個人通過一間比一間狹小的房間。起初騎士不習慣,大呼小叫給自己壯膽,漸漸地他發現了沉默之堡的真實用意: 當一個人安靜的獨處時,你應該認真的去聆聽,要聆聽自己的心。通常的情況下,我們設置障礙,來保護我們所謂的自我。有一天卻發現,自己給關在自造的障礙后面出不來了。我們被時間、被一堆又一堆的事情推著走,很少停下腳步,聽聽自己內心深處的聲音。“這真的是我想要的嗎?”我們應該這樣問問自己,不該只是盲目地操作著邏輯上的下一步。 悟透了這個道理,騎士不再去想任何事情,也沒有和自己說話,他靜靜地坐下,傾聽寂靜。在這個像墳墓般的房間里,他感到自己的痛苦和孤獨。很快的,他也能感覺到妻子的痛苦和孤獨。這么多年來,他逼她住在另一座沉默之堡里,他開始嚎啕大哭。武士不知道他哭了多久,不過眼淚從他的面盔里迫涌而出,直到整個房間開始淹水。頭盔被淚水消融了,密封的墻上也出現一扇門,武士穿越了沉默之堡。 我們的企業家卻沒有騎士這樣的自由。他們的肩膀上擔待著成千上萬人的衣食住行,沒有他們尋找沉默之堡的空檔。從德州晶華集團資產由5億多元迅速擴張到36億元的發展軌跡中,我們至少可以看到這一深層問題:“龍頭企業”這頂帽子拘押了苗建中。在政府有關部門的“協調”下,晶華集團最終收購了與自己主業無關、由德州市發改委主持投資的凱元熱電廠。由于煤價上漲等因素,電廠虧損嚴重,政府無力承擔這個大包袱。要讓整個電廠按原規劃建成,還需晶華集團投入約20億元,并且該電廠的市場前景并不明朗,讓晶華背上沉重的包袱。“龍頭企業”、“無限責任”、“我幫你貸款你幫我擔責”,這一切使得苗建中成為真正的盔甲騎士,搞不清本原的自己是什么樣子的。他根本找不到時間和空間來省察自己和世象。哪怕是他強行把自己封閉在家里,每天還是要處理五六十件公文,接無數電話。每件公文都事關資金審批調撥,不能大意。 山西鑫龍稀土磁業(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趙恩龍,是被責任壓垮的另一個典型。2004年,趙恩龍大約向銀行借貸達4億元,到2004年年底,巨額貸款無法歸還,經多方協調達成一個口頭協議:由趙恩龍出面籌措款項先歸還銀行,平賬后,銀行再將此款貸給趙恩龍,趙再還給借款單位和個人。但是,在趙將款打入銀行后,銀行卻未能按口頭約定再貸款給趙恩龍。失信的趙恩龍只能跟秘書躲避在辦公樓吃住,以免把騷擾帶回家里。 2005年1月1日早晨6點40多分,在人們迎接新年到來的時候,他卻乘秘書下樓洗漱的空檔,從辦公室4樓跳下,以死永遠躲避那些借款人。據警方在現場發現的趙的一封遺書,上面提到,政策變化快,負擔過重,銀行的貸款無法如期歸還等;雖然自己一心想干成一番事業,但現在銀行的貸款無法如期歸還;借了朋友一些錢,不要說兌現當時約定的利息,就是本錢也無法歸還,上門討債的人又非常多等等。據秘書長張江濤反映,企業運轉極端艱難,趙恩龍的思想壓力非常大。現實中的他被一種東西裹擁著往前走,從事了過多自己顧不過來的事。偏偏他又是一個好人,趙恩龍給他認識的朋友留下的大多是“夠意思、人緣好”的印象。他從不拖欠工人的工資,自己生活非常儉樸,用的是八九百塊的手機。在一次全體職工大會上大老板說到傷心的地方竟然哭起來,他也感覺到部下工作不是很賣力,但他沒有辦法,好多事情他都是親自去辦。死前一天他特把做農民的姐夫找來敘敘家常,他反復念叨,“生意難做人難用”,真愿意跟著姐夫回家種地。姐夫對他仰視慣了,并沒有去體會這些家常話的含義。 可是,趙恩龍已經沒有機會回家種地。債主們不讓,企業的員工也不讓。他理解這個現實。他沒有騎士一樣的自由度,說脫下盔甲馬上就可以聽憑意志脫下盔甲。如果趙恩龍的周圍不是聚集著那么多混事的、逼債的、吹捧的和仰視的,如果在他決定盲目擴張之際,能夠有一個沉默之堡讓他傾聽一下內在的本我,或許不會發生那樣的悲劇。他的姐姐懷疑,他的死是否真能夠去挽救那些牽連其中的人。為著避免類似的悲劇,我們還要跟隨騎士前行。 “知識之堡” 騎士穿越沉默之堡后,抵達了一座“知識之堡”。那是一座黑暗無光的城堡,隨著內省的知識一點一點增加,城堡就會一點一點的變亮。有用的知識即是指引前路之光。在黑暗中,騎士開始了他的覺察。一個想法突然靈光大作閃過他的腦海—— 他實際上沒有愛,只是一直把需要當成了愛;他需要妻子和兒子的愛,他需要所有被他從恐龍爪里救出的公主的愛,以及所有他上戰場所保衛的人的愛,因為他不愛自己。這真是令人震驚的發現,他不能真正的愛自己,當然也就不能真正的愛別人。“良知”的復歸,使得周邊的一切都明亮起來。他帶著點不情愿,站在鏡子前面。本以為會看見一個高大的人,有著一雙悲傷的眼睛,一個大鼻子,從脖子以下都包在盔甲里。出人意料之外,他看見一個迷人的、活力充沛的人,有著一雙閃爍著熱情和愛的眼睛。盔甲后邊的本我,原來活力充沛、閃爍著熱情和愛的光芒!看來他根本不需要去證明任何事,他的本我就是心地好、善良,又充滿了愛。 只有需要而沒有愛的中國企業家,不在少數。金華集團副總裁徐凱就是一個代表。2005年1月3日,他在自殺前一天坐上出租車后跟司機敞開了心扉,他說在感情上得不到真愛,在他身邊的女人都是為了他的錢。他由于工作的原因住在賓館,感到很孤獨,沒有意思,想結束生命。出租司機認為他說說而已,可是后來還真看到了報紙上有關他自殺的新聞。徐凱曾經是個“天南地北”、口才極佳而且學識淵博的人,喜歡歷史,對紅軍長征中的大小戰役連日期都記得清清楚楚,“能從中東講到歐洲,再講到非洲”。可是 2004年以來,公司架構上的調整使徐凱開始成了悠閑階層,他開始大把大把掉頭發,動輒唉聲嘆氣,不習慣說話,“封閉自己”。他長年住酒店,沒有家的概念,只能找朋友吃個飯聊聊天,自己卻常常處于孤獨、恐懼與空虛之中。2004年甚至很少找人吃飯聊天了。就是在2004年12月12日為他特別舉行的生日宴會上,徐凱依然表現出精神恍惚,發呆,注意力不集中,對別人的敬酒視而不見。孤獨、空虛而恐懼一刻不肯離開他。12月31日,徐凱的病情檢查報告出來。除了已知的高血壓、前列腺炎,還查出糖尿病Ⅱ型、乙型肝炎和嚴重的抑郁癥等。他當時就哭了。徐凱沒有留下遺書,這個世界沒有任何一點他掛心的事。 徐凱沒有愛。見多識廣的他當然懂得,愛別無他求,只求成全自己。他曾經出于畏懼和無聊去尋求過愛,曾經在“天南地北”中搜索過愛,曾經在艱苦奮斗的甘苦中建立過愛,曾經激情飽滿地投入工作實現過愛,可是最后他卻被愛徹底拋棄。徐凱患上抑郁癥的時間,是在他工作比較消閑的時候。工作本來是他愛的載體,一旦意識到企業不真正需要他了,他便徹底絕望了。沒有愛的世界,是一片冰冷的死寂。 “志勇之堡” 騎士不知道1200多名中國企業家受盔甲所累紛紛倒下。騎士的盔甲大部分都被他的淚水銹掉了,他感覺到多年未有的輕松和年輕,也比從前更喜歡自己。于是,踏著和年輕人一樣的堅定步伐,向最后一座城堡—— 志勇之堡出發。 “志勇之堡”,顧名思義就是要有志氣和勇氣。而在故事里,有一只能解讀別人心思的恐龍,它有巨大的身軀、以及會噴出藍色火焰的嘴巴,這令騎士感到無限的恐懼和疑慮。其實,這只恐龍是不存在的,是騎士因為恐懼不安而形成的幻象。“無退路時,易做決定。”于是,騎士深呼吸了一口氣,再一次向恐龍大步前進。他不斷地向自己說:“疑慮和害怕是幻相,疑慮和害怕是幻相。”恐龍一次又一次朝武士射出巨大、劈啪作響的火焰,可是不論它怎么努力,武士身上就是不著火。恐龍非常困惑,不曉得它已經失去了力量,因為武士不再相信它的存在。“自知之明可以殺死疑懼之龍”,而自知之明即是真理,且真理比寶劍更來得銳利。 我們的成功企業家,多經受了常人所不能及的磨難,見識了一次次的眾叛親離,在人性的混戰中,他們曾經勝出,創造了不同一般的業績。可是,過去的搏殺在他們心里同時留下了很深的創傷。無論是沉靜的苗建中,還是慘烈的趙恩龍,抑或是飄忽不定的徐凱,對人性的恐懼和疑慮,無疑是他們共同的隱秘。一種對環境徹底的悲觀和絕望,讓他們毅然走上了一條不歸路。 是人就會迷失,關鍵看是否能夠適時從迷失中醒來。騎士也迷失,他也缺乏勇氣。可是騎士并不是孤獨前行,每當危難或是準備放棄的時候,總有智者在他身邊出現,總能有輕松幽默的開導,讓他豁然醒悟。我們企業家的環境,遠沒有騎士之環境來得寬松和諧。他們甚至沒有可以信賴的搭檔。反思起來,周邊的環境沒有使他們確立對“良知”的信賴,才讓他們丟失了面對危難的“志氣”和“勇氣”。通向生活的原則、源泉和根本的途徑是人們在痛苦與無聊中的覺察與獲得的新啟示,而缺失了“良知”的環境,將是一片冷漠的死寂,會窒息人們的新啟示的萌芽。他們身邊不長青草,也就引不來松鼠和飛鳥。 “真理之巔” 最后,正當快到山頂的時候,騎士給一塊巨大的巖石擋住,巨石上刻著幾句碑文:“雖我擁有此宇宙,無有一物為我留,因我不可知未知,如我不愿棄已知。”他吊在峭壁上,深吸一口氣,念叨著碑文,突然有了個很嚇人的想法:他現在為了寶貴的生命,抓住不放的巖石,對他來說也是“已知”,這是不是表示,他必須放手,讓自己墮入不可知的深淵,才可以得到“未知”呢? 想到這里,他的力量開始消失,他抓住巖石的手指也開始迸出鮮血。由于相信自己快死了,他放了手,向下落去,掉入記憶中無盡的深處。當一種不熟悉的平靜感突然充滿全身,奇怪的事發生了,他開始向上掉出深淵。突然,他發現自己站在山頂上。于是,他徹底明了巖石上碑文全部的意義:放掉那些令人害怕的東西,放掉所有已經知道和擁有的東西,樂意擁抱無限的未知才使一個人真正自由;我們真正該享受的是那些不曾體會過的未知數。騎士不會再穿著盔甲,向四面八方騎去,好證明自己心地好、善良、又充滿了愛。他就是小溪,就是明月,就是太陽。現在,他可以同時是這些東西,而且更多,因為真正的愛,讓他與自己、與他人和宇宙合為一體。 這里是全書的眼。痛苦、無聊與去執,是騎士不斷獲得嶄新啟示的路徑,也是他到達圓滿空性境界的三種推動力量。許多人能夠跳出“痛苦”的深淵,甚至能夠渡過“無聊”的沼澤,卻唯獨做不到去執,尤其是在重大的轉折點上,更放不下已經形成的認知和習慣。在緊要關頭,人們往往把遼闊圈起來,深陷在已知的狹窄小徑上。世上還有著1000條沒有被人走過的路,還有1000座神秘島,還有1000種的潛能,還有著1000種的豐裕和可能,只有那些具備空性思維的人,才有可能開發出來。空性說到底,就是去執隨緣。這些道理,或許誰都理解,可是要在實踐中篤行,卻不是簡單的事。一如盔甲騎士須經歷“沉默之堡”、“知識之堡”、“志勇之堡”、“真理之巔”的考驗。每一道門檻,都需要徹底顛覆對自己的認知。人們也必須發現自我并跳出自我,從更高的層面上去關照和省察自我。 國學大師梁漱溟在晚年口述《這個世界會好嗎》中指出,“人類不是渺小,是悲慘;悲慘在于受制于他自己(制與受制是一)。深深地進入了解自己,而對自己有辦法,才得避免和超出了不智與下等。這是最深淵的學問,最高明最偉大的能力或本領。”梁漱溟對發明“良知”一詞的王陽明尊崇有加。他認為個人的和社會的“良知”是通向“最深淵的學問和最高明最偉大能力”之最重要的途徑。在梁漱溟那里,“良知”的意義伸得很遠,它是跟上帝、宇宙、佛、超自然、絕對理念等并列的。梁漱溟的論斷為無數企業家的奮斗歷程所證實。孫宏斌是其中的一個代表。 這個當年激情似火的熱血青年,突然遭受無妄的事變,獲罪入獄。我們可以想象他的憤怒與痛苦,以及接著下來面對鐵窗的無聊。在昏暗窒悶的囚室里,孫宏斌卻利用三年多難得的時間,發現了一個巨大的真實:被殺者對其被殺并非全無責任,被劫者對其被劫并非無可責難。他曾輕狂而無心地錯待了別人,從而也錯待了自己。他意識到了自己那所謂自主和自由的荒唐。那種自由實際上正是最堅固的鎖鏈,鎖住了他的正午。在柳傳志冷酷無情的外表中,他讀出了那脆弱而頑強的人性。他勇敢地接受了這個巨大的真實。 與生活講和,當面向柳傳志承認錯誤,并獲得了柳的諒解。一件事物好壞,發展的潛力與潛能,是問題還是新契機,關鍵看主體是否能專注凝神、敞開心胸來化轉。“隨緣”,并不是被動的隨波逐流,而是去除蔽障、主動地去把握諸種潛在可能的心態與思維。空性法則,讓孫宏斌超越了無妄與災難強加于自己的東西。而他把過去抹平的“回歸零”的渴求,正是與騎士一樣在緊要關頭的一個卓絕之舉。由此開始,那1000座神秘島開始在他眼前展現。 孫宏斌的故事,揭示了一條簡單而深刻的道理:歡樂與憂愁總是結伴而行。從淚水注滿的同一眼井中,歡樂也泉涌。當我們欣喜時,深究自己的心靈,或會發現如今帶來歡樂的,正是當初帶給我們痛苦和憂愁的。當我們悲哀時,再審視自己的心靈,或會發現如今帶來憂愁的,正是當初帶給我們歡樂的。孫宏斌自我解嘲,在順馳許多人都比他有能力,可是屬他心態最好。在起伏不平的商業保持一種好的心態,沒有點空性思維不行。 先知紀伯倫曾經用“先驅”這個詞,概括了人之觀人的角度,對我們理解騎士“為自己出發”大有裨益:“你是你自身的先驅,你建造的塔只是你‘大我’的根基,你的‘大我’,又將成為新的根基。”“你們的善寓于你們對自己‘大我’的渴求中;你們每個人都有這種渴求。但你們中有些人的渴望,是咆哮著奔向大海的激流,載著山巒的秘密和森林的歌曲。而在其他人那里,這渴望是一道平緩的溪水,在抵達海岸前,就已在蜿蜒或回轉中松懈下來。但渴望豐裕的人不要對清心寡欲的人說:‘你們何以如此遲緩而躊躇呢?’因為真正的善者不會問無家可歸的人:‘你的房屋怎么樣了?’”是的,生命的式樣是多重的,當我們闊步而堅定地向目標前進時,我們是善的;當我們為饑餓困境折磨蹣跚而行時,我們也不是惡的。 “過來人”李嘉誠,一下子就抓住了《盔甲騎士》的魂。他說,騎士忘記了,成功不是盔甲創造的,而是盔甲中的自己創造的。可貴的是,一旦騎士意識到問題所在,他很有勇氣,敢于四處求教,尋找新知識、新方法,鼓起勇氣,克服疑懼,終于成功地擺脫了束縛他的盔甲,重新尋回了自我。“更新求變,就是使自己不被盔甲禁錮束縛的關鍵,我們要像故事中的騎士一樣,要有智慧,能客觀地認清各種困境,鼓起勇氣,直面世界的挑戰;要有毅力,去克服重重障礙,勤于反思,追求新知,才能營造一個和諧、有價值的社會,締造出未來新的傳奇。” 確實,我們的企業家,甚或我們每一個人,需要像盔甲騎士那樣歷經痛苦、無聊、去執之涅,不斷獲得嶄新的啟示,就可以達到空性圓滿的境界。而且,只要前行在“夢與醉”的路上,追尋著我們渴望中的“大我”就是一種善。 |
| 新浪首頁 > 財經縱橫 > 管理 > 正文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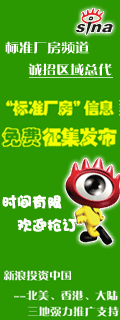 |
| 熱 點 專 題 | ||||
| ||||
| 企 業 服 務 |
| 股市黑馬:今日牛股! |
| 小女子開店50天賺30萬 |
| 名人代言親子裝賺錢快 |
| 新型建材 月進10萬 |
| 女人錢,怎么賺 (圖) |
| 06年賺錢項目排行榜! |
| 介入教育事業年賺百萬 |
| 我愛美麗招商!加盟! |
| 品牌折扣店!月賺30萬 |
| 泌尿頑疾——大解放! |
| 拒絕結腸炎!! 圖 |
| 頸椎病患者!我來晚了 |
| 特色治失眠抑郁精神病 |
| 糖尿病——重大發現! |
| 高血壓!有了新發現! |
|
|
|
| ||||||||||||||||||||||||||||||||||||
|
新浪網財經縱橫網友意見留言板 電話:010-82628888-5174 歡迎批評指正 新浪簡介 | About Sina | 廣告服務 | 聯系我們 | 招聘信息 | 網站律師 | SINA English | 會員注冊 | 產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2006 SINA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