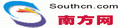民工荒 誰在慌
初春時節民工荒,從2004年開始已成為保留節目,除了去年。
去年的新聞是金融危機后,企業紛紛金蟬脫殼關門“走廠”,剩下一堆憤怒而無奈的工人。
最后一根稻草就這樣壓在了已日趨脆弱的農民工供應鏈上。
隨著人口出生的逐漸減少,這根供應鏈條將無可回避地走向細弱。盡管這一拐點會出現在哪一年研究者尚在爭論之中,但一個顯而易見的共識是,中國的廉價勞動力再也不是想象中的源源不斷取之不盡,而是越來越有限供應。
加速這一趨勢的是,長久以來,這個龐大而卑微的群體共同制造著中國經濟的奇跡,卻無法得到足夠的關懷與安全感。
當內陸經濟日益蓬勃,尤其是在4萬億刺激計劃之后一派熱火朝天,勞動力需求大為增加,而沿海的工資僅憑一兩百元的微弱優勢難再具有足夠的吸引力時,即使出口已經從萬戶蕭疏轉而復蘇回暖,但那些漂泊異鄉的農民工還是開始了用腳投票,以毫不留戀的姿態離開。
對工人的爭奪,正發生在工廠與工廠之間,內地與沿海之間。而80后90后新生代農民工們,已經在新的人生觀指引下,呈現出了比父輩們更為多元的選擇。
本期南方周末為讀者呈上兩篇相關報道。可以看到,內地城市如何開始“圍追堵截”留住農民工。也可以看到,即使在民工荒鬧得人心惶惶的沿海,并不是所有工廠都為此發愁。
民工荒,是資本與勞動力進行工資博弈的信號,更是企業與企業進行競爭力決戰的號角。
□本報記者黃河實習生羅瓊梅嶺發自東莞廣州
又聞民工荒,而且似乎一年比一年兇猛———不少媒體根據一些城市勞動部門的數據簡單計算說,珠三角眼下缺工200萬人,比過往的任何一年都更為嚴峻。
而此時,雖然出口在不斷回暖,但統計數據表明全年中國出口依然是負增長,這說明訂單并未達到金融危機之前的水平。
出口訂單并不比此前更多,為什么會出現規模更大的民工荒?它的背后,是中國經濟正在悄然發生的怎樣的深刻變化?
民工荒是個“偽命題”
短短一個星期內他們就招到了300名普工,“全是女工”,“簡直比國足踢贏巴西隊還讓人吃驚!”
并不是所有人都難以招工,宇龍通信公司的人力資源經理陳華平就比較輕松。
短短一個星期內,他們就招到了300名普工,“全是女工”。智通人才市場的李秋明總經理一臉羨慕地在旁說道,要招300名男工不難,但在普工這塊要一次招300名女工,“簡直比國足踢贏巴西隊還讓人吃驚!”沒有任何秘密,最重要的武器便是工資。
1月,宇龍通信將生產基地從深圳搬到東莞松山湖科技產業園,僅僅帶著幾名資深員工準備培訓當地招來的新工人,結果卻發現100多人的招工計劃只來了27個。宇龍通信不得不開出了1600元到2400元的普工薪酬———這被他們稱為“深圳待遇”,比當地許多企業要高出一大截。“能跟我們比的只有華為”。
當時,他們開出的底薪是1000元,而隔壁一家公司的月薪是770元。招聘的牌子剛打出去,馬上就有員工跑過來。第二天,隔壁公司的底薪就漲到了800元。
宇龍通信如此“財大氣粗”,底氣在于3G市場的火爆。
這家以“酷派”智能手機在國內3G市場中嶄露頭角的通信制造商,在金融海嘯期間迎來市場高速擴張期。此前每年的手機產量僅為20萬部左右,但到了2008年10月份以后,隨著3G市場的開發和營銷模式的拓展,這個數字變成了50萬部,而每一部手機帶來的利潤空間,也遠遠超過那些鞋子、內衣微薄的出口利潤。市場紅火,工人就成了賺錢的關鍵。
目前,公司共有工程技術人員1000多名,生產線工人1300多人。為了留住他們,公司“下足了血本”:在松山湖生產基地的280畝廠區中,廠房面積只占10多畝,其他的土地公司打算建足球場、籃球場以及閱覽室等設施;而在員工的公寓里,獨立衛生間、太陽能熱水器和寬帶網絡一應俱全,“宿舍里本來打算裝電扇,員工說太熱,結果老板一句話全部換成了空調。”
工人的“報復”
金融危機只不過是最后一根稻草。長久以來,數以百萬的農民工為經濟作出了巨大貢獻,卻長期得不到足夠的關懷。當出現了更多選擇機會時,他們中的許多人便以毫不留戀的姿態迅速離開。
不是每家企業都像宇龍通信這么輕松。李秋明證實了這一點
李是東莞智通人才市場長安公司總經理,正是他們替宇龍通信安排了招聘會。“從我們的統計數據來看,今年春節后前來應聘的員工數量比往年同期少了10%至20%,而招工企業的數量卻比2009年大幅增加,因此缺工現象比較明顯。”在2008年以前的招工季節里,智通人才市場每場招聘會上的入場企業都在五六百家左右。在2009年春節后,入場企業最多的一場只有297家,不到過去的一半。
即使是好不容易找到了工作的工人,有的也不得不忍受著企業苛刻的工資待遇。李秋明觀察到,金融危機之后,有少數企業惡意壓縮員工待遇以縮減開支,因為工作不好找,許多工人只能忍著,但隨著就業漸漸好轉,“許多員工義無反顧的離開了這些企業,讓那些公司不得不用更高的價格在市場上重新招人”。
其實金融危機只不過是最后一根稻草。
長久以來,數以百萬的農民工為經濟作出了巨大貢獻,卻長期得不到社會的足夠關懷,始終徘徊在城市的邊緣。當危機爆發時,他們中的許多人便以毫不留戀的姿態迅速離開了這座城市。
隨著經濟復蘇,當訂單重新飛來,工廠們不得不開始搶奪工人。待遇在迅速提高,比如在東莞,過去普工的底薪基本上是按東莞最低工資770元設定,而自去年年中開始,已經有企業主動提到1000元甚至1200元。門檻也開始放寬:過去只招30歲以下員工的企業,現在也將標準放寬到了45歲以下;過去有的企業非女工不要,現在也“男女兼容”了。
這樣的變化,已經讓那些利潤微薄的企業嘗到了痛苦。
鞋廠老板李小建苦笑著給記者算了一筆賬:這個行業的平均利潤只有微薄的五六個點上下,如果工資上漲30%,利潤就要再下降一個點,再加上改善員工福利等投入,“投資鞋廠恐怕還不如把錢存在銀行里,起碼省了辛苦”。
但即使這樣,在多年從事人力資源招聘的李秋明看來,僅靠簡單的加薪和放寬招工條件并不能真正解決日益明顯的結構性的勞動力資源短缺現象。他說,從人力管理的成本而言,留住老員工比招聘新人的成本要低得多。但如何留住員工,卻并不容易。“給工人信心更重要。”3月1日,福建一家中型鞋廠的董事長告訴記者。
因為數年前就開始向研發和設計轉型,金融危機中他們公司逆市擴張,價格和訂單量分別比上一年漲了20%和50%。到元宵后,原有的3000多工人中已有超過90%返回工廠,令周邊那些招不到工人急得跳腳的同行眼紅不已。
他感慨道,“不能給他們信心,工人就會用腳來報復”。
翻過一山又一山
“出口企業經歷了三次波折,第一次是人民幣匯率上升,死了20%的企業;第二波是第二次基本工資上調,又死掉20%;然后是金融海嘯———從2005年到現在,對我們企業而言,就是一輪輪的考驗,是翻過一山又一山。”
工人的“報復”,早已不是這些出口企業經歷的第一個坎。“出口企業經歷了三次波折,第一次是人民幣匯率上升,死了20%的企業;第二波是第二次基本工資上調,又死掉20%;然后是金融海嘯———從2005年到現在,對我們企業而言,就是一輪輪的考驗,是翻過一山又一山。”在說這段話時,身為“80后”的杜倍純臉上有著與其年齡不相稱的嚴肅。她的父親已在這片紅海中打拼了十多年,她上小學時就玩父親廠里生產的掌上游戲機,后來又用上了廠里的學習機,再后來是VCD、DVD,直到近年開始生產的液晶電視和上網本。
他們的產品全部外銷。最早做歐美市場,一個產品能出二三十萬臺的貨,但當2006年他們開始推出自己的獨立品牌時,卻發現只能賣到中東、拉美、東南非去。
失去了規模優勢,他們被迫要開發不同的產品以適應不同的市場,研發能力由此得到鍛煉。另一方面,雖然市場規模縮小,但單件產品的利潤率卻由于競爭對手較少而大幅上升,從而有效地支撐了產品研發的推進。杜倍純回憶,在從歐美市場轉向其他市場的階段,“也是廠里技術變化最快的時候”。
這一技術路徑的轉變,也帶來了工廠人力資源成本結構的變化———從占25%左右提高到占35%左右,越來越多的錢花在人身上了。為了適應這一變化,工廠也在進行新的變革,比如過去全部由人工操作的生產工序,漸漸轉變為半人力半機械化的操作模式。
從制造到智造
他和同事們一直致力于向許多人———甚至包括溫家寶、李克強等國家高層———重復一個論斷:鞋業不是勞動密集型的“夕陽產業”,而是一個高附加值的“時尚工業”。
如何翻過最新的這座山?張鴻的回答是,從制造到智造。
張是位于東莞的鞋業總部基地的副總經理。他和同事們一直致力于向許多人———甚至包括溫家寶、李克強等國家高層———重復一個論斷:鞋業不是勞動密集型的“夕陽產業”,而是一個高附加值的“時尚工業”。“一雙高檔皮鞋價值七八千元人民幣,但成本只有幾百元,利潤比電腦高得太多了。”張鴻指著自己腳上的一雙歐式皮鞋說,一個人可以幾年只用一臺電腦,但穿鞋肯定不只一雙。
但在幾年前,他們的這個觀點不僅外人聽不懂,就連業內的企業家也不買賬。那時候的老板們只想著訂單,一雙鞋賺幾塊錢就很滿足了,直到現在生意越來越艱難,利潤越來越低,才有更多的人開始思考未來。“我們現在跟企業客戶溝通時,更多的是強調企業競爭要轉向‘智造’而非‘制造’。”張鴻表示,所謂“智造”,并不僅僅是品牌和宣傳,更多的是通過市場研發和專業細分而帶來的產品附加值最大化。
而在這一過程中,企業和政府都充分意識到了品牌價值的重要性。“今天的107國道兩旁,最多的就是鞋業廣告,而過去幾乎沒有企業做這類廣告的。”張鴻說。
新浪聲明:此消息系轉載自新浪合作媒體,新浪網登載此文出于傳遞更多信息之目的,并不意味著贊同其觀點或證實其描述。文章內容僅供參考,不構成投資建議。投資者據此操作,風險自擔。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