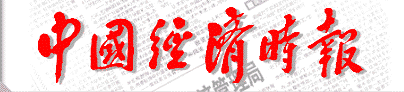|
|
學者稱國內消費需求應成經濟增長可靠動力
時紅秀
無論從自身工業化進程還是從全球化分工地位看,我們消費能力的擴張是以生產能力更快擴張為前提的。中國由一個“自己生產供別人消費”的國家,過渡到“讓別人生產而自己消費”、并成為“消費大于生產”意義上的“消費型國家”,從發展階段來判斷,我們要走的路還很長。在此之前,消費與投資之間的關系受到的制約是客觀的,并不會取決于我們的主觀愿望。
在經濟運行中,投資、消費和凈出口這“三駕馬車”之間不協調,一直是影響中國經濟持續平穩增長的潛在因素。具體地說,投資仍是拉動經濟增長的主力,尤其是地方政府推動下的投資拉動,既不利于耕地保護和生態維護,也因在成本—收益比較上不敏感,使得宏觀調控中市場化的政策工具作用甚微。而消費需求作為內需中的最終需求長期低迷,使得經濟增長更多地依賴出口,如果外部市場動蕩,那么國內投資只能形成產能過剩。也就是說,經濟中的一大塊被“投資”使用了,卻沒能形成有效供給,經濟失衡在所難免。近幾年來外需發展很強勁,2008年上半年貿易順差超過1.8萬億美元,居世界之首。伴隨著美國次貸危機和國際金融動蕩的擴展,今年上半年我國東南沿海出口企業出現大面積的效益滑坡。
一、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在加大
2007年,全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長16.8%,加快3.1個百分點。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速與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速之差縮小了2.2個百分點。消費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39.7%,同比上升0.5個百分點;投資的貢獻率則有所下降,為38.8%,同比下降2.5個百分點。7年來在拉動經濟增長的投資、消費和凈出口“三駕馬車”中,消費貢獻首次超過投資貢獻。今年上半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51043億元,同比增長21.4%,比上年同期加快6個百分點。這無疑將增強中國經濟增長的穩定性和持續性。
我國消費品市場規模越來越大。正如人們近來談論的,中國在世界上在手機、旅游、寬帶等產品或服務消費方面是第一大市場,在黃金飾品、汽車等產品消費方面為第二大市場,在奢侈品消費方面為第三大市場,等等,說明中國人的消費能力確實得到了較大的提高。相對于早期的“低生產、低消費”和隨后一個時期持續的“高生產、低消費”格局,“高生產、高消費”的格局正逐漸出現。也就是說,中國百姓開始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這正是科學發展觀的應有之義。
改革開放近30年來,投資與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是交替變化的。1978年、1993年—1996年和2001年—2006年這11年里,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高于消費的貢獻率,其余18個年份里消費的貢獻率高于投資的貢獻率。至于凈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波動幅度更大。20世紀90年代以來,1990年凈出口貢獻率曾超過50%,1993年又跌至-38%,1997年又達到44%,1999年至2004年平均在7%左右,2005年以來穩定在20%-24%之間。當然,這種大幅波動與一定時期國內產業結構和經濟運行狀況有關,但它也說明外部市場風險較大,而一個大國經濟對外部市場不能過于依賴。
經濟增長的源泉是分工。分工水平依賴于市場的容量。亞當·斯密的這一洞見,在今天仍有深意。這就是說,只要由最終需求即消費規模所反映的市場規模足夠大,分工將不斷地深化下去,最終會使技術創新內生出來。近代資本主義國家長期對外擴張,目的無非是兩個:一是搶奪資源,降低要素投入的代價;二是搶奪市場,擴大市場空間。這些國家現在人口規模都不大,卻一直引領工業技術創新的方向,原因就在于此。一句話,一個國家能否從專業化分工中得益,取決于參加分工的人口數,取決于該人口所具有的最終需求水平——兩者構成了一國的市場容量。因此我們看到,在計劃經濟中,人口眾多可能對經濟增長造成壓力,但在市場經濟中,人口規模卻可能為經濟增長提供基礎。新經濟史學派干脆指出,西方國家之所以在近代興起,有兩個至關重要的條件:一是具備有效率的制度即市場機制來協調分工;二是人口快速增長擴大市場規模。經濟發展史一再表明,只要有市場機制,只要處于工業化加速過程,一個國家和地區,即使人口密度已經很高了,但仍然會出現勞動力短缺和人口流入。正因為如此,近年來人們開始反思,產生于計劃經濟時代的中國人口政策,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是否需要調整。在中國參與全球經濟一體化過程中,外國資本垂涎欲滴的,就是我們巨大的人口規模所蘊含的市場容量。一個13億人口的大國,有穩定的社會秩序、統一的貨幣、相對完善的產權制度,如果確保市場機制“管用”的話,自身的消費力量就是推動經濟增長的巨大引擎。
二、要素稟賦和國際分工影響投資與消費的關系
縱向地看,在經濟發展史上,一個大國經濟體的工業化進程加快,總是伴隨著重化工業和基礎設施的大規模擴張,這樣就不可避免地引起投資規模在一定時期內持續高速擴張。即使進入21世紀,我們要走新型工業化道路,在經濟中知識經濟和第三產業權重加大,但對于像中國這樣一個傳統的農業大國,重化工業和基礎設施仍是建立現代化經濟必不可少的物質基礎。也就是說,投資擴張在未來中國經濟發展中仍將占有重要地位。
橫向地看,一國經濟能否實現由自身消費為主要動力,還受制于這個國家參與國際分工的程度,受制于這個國家在國際分工環節中所處的地位。人們常拿發達經濟體作參照,其消費幾乎占GDP的70%-80%,而我國平均比發達國家低20多個百分點。但在國際分工鏈條中,生產什么、生產多少和消費什么、消費多少,決定于一個國家所處的地位。這地位可不是說變就能變的。它背后蘊含的,是國家之間資源稟賦、資本、技術、制度等綜合競爭力量的比較。我們現在的局面是“Made in China”滿天飛,很多發達國家的消費品由我們生產,正所謂“世界工廠”。這是由目前我國要素稟賦所決定的。這種要素稟賦還決定了我們在國際分工中分享收益的地位。關于在世界消費品生產中中國的“貢獻”與“收益”關系,幾年前有人以中國向美國出口“芭比娃娃”為例說明:“芭比娃娃”是中國制造并出口的玩具,在美國海關的進口價為2美元,而到美國市場上零售價為9.99美元,即有近8美元作為“智力附加值”跟我們沒關系。在其余2美元中,1美元開支于運輸和管理費,65美分支付原材料進口的成本,中國人得到的加工費只有35美分。也就是說,在這一國際分工鏈條中,我們分享的收益只占3.5%。但即使是這3.5%的收益分享比例,也為中國帶來了數以千億計的外來投資,更為中國帶來了數以千萬計的就業機會。只要我們能夠長期參與國際分工,隨著中國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我們的消費能力遲早會得到提高。
總之,無論從自身工業化進程還是從全球化分工地位看,我們消費能力的擴張是以生產能力更快擴張為前提的。中國由一個“自己生產供別人消費”的國家,過渡到“讓別人生產而自己消費”、并成為“消費大于生產”意義上的“消費型國家”,從發展階段來判斷,我們要走的路還很長。在此之前,消費與投資之間的關系受到的制約是客觀的,并不會取決于我們的主觀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