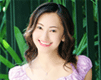一段充滿可能性的歷史 | |||||||||
|---|---|---|---|---|---|---|---|---|---|
| http://whmsebhyy.com 2005年09月17日 17:16 經濟觀察報 | |||||||||
|
丁三/文 1944年7月22日,當一架C-47運輸機在延安降落時,機上的9名美國人可能不會想到,他們不僅開始參與一段充滿可能性的歷史,而且,他們中的許多人,也由此開始了自己命運的變化。
這9個美國人是“美軍延安觀察組”(USAOG-US Army Observer Group)的第一批成員。觀察組,這個美利堅合眾國與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官方聯絡機關,共存在了963天。它曾給20世紀的中美關系增添了另外一種可能。 “迪克西使團” 觀察組中的一些人意識到,華盛頓如果繼續因為意識形態而偏袒重慶,那么,美國將失去延安,也將失去中國。延安改變著他們的中國觀點。但此時,在煙波詭異的重慶,一些重大的變化卻悄悄發生著—— 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觀察組是“史迪威精神”的產物,它的誕生更與史迪威本人息息相關。所謂“史迪威精神”,指的是西方世界的一種與其說是“親共”、不如說是“反國民黨”的態度。抗戰期間,許多生活在中國的西方軍人、外交官、記者,認為重慶太腐敗,認為國民黨不過是一股守舊腐化的,代表官僚、地主、軍閥的勢力。于是,他們開始把目光投向“西北一角”,投向了中國共產黨。史迪威正是其中最有影響的人物之一。 自1942年親歷中國遠征軍的慘敗后,史迪威就毫不掩飾他對重慶的深惡痛絕。這一年湘豫桂的大潰敗,更使他把重慶政府看作一具木乃伊。為此,他游說華盛頓,一方面希望白宮向重慶施壓,讓蔣介石把軍隊的指揮權交給他;另一方面,他試圖了解延安的態度和軍事潛力。在這一背景下,兩名出生在中國四川的年輕外交官,謝偉思和戴維斯,分別向華盛頓提出向延安派遣觀察組的建議。 1944年6月,來華訪問的美國副總統華萊士,向蔣介石提出了這個要求。因湘豫桂大潰敗而丟盡顏面的蔣介石,終于勉強同意了。 觀察組以52歲的包瑞德上校為組長,以35歲的美國駐華使館二秘謝偉思為政治顧問。喜歡以典故命名的美國人,把觀察組稱為“迪克西使團”。“迪克西”是美國人對南北戰爭中南方邦聯的稱謂,農業傾向、氣質固執、有“叛亂者”的意味……這就是許多美國人對中國共產黨的最初理解。 延安生活就這樣開始了。觀察組的日常工作,包括氣象觀測、情報合作、救援失事的美國飛行員等,是同盟國協作的組成部分。但幾乎所有的人都心知肚明,這些都是表象的、皮毛的。考察組負有更重大深遠的使命:考察延安的戰爭潛力,以服務于二戰,這是史迪威的需要;考察延安的政治潛力和走向,以服務于美國的遠東及世界戰略,這是華盛頓的需要;甚至還有一個“中國之路”的命題:中國一直是西方的一個謎團,它太大、太有凝聚力,因此沒有成為印度那樣的殖民地;它又太弱、太守舊,因此一直沒有走上日本那樣的西化道路。如果延安取代似乎隨時要崩潰的重慶,它將走向何方呢?是蘇俄那樣的道路?是傳統中國?還是西方式的代議制國家?…… 與此相對應,延安表現出了巨大的熱忱:給予他們各種工作上的便利,甚至給予對延安來說極其高昂的每月7美元津貼。即使這樣,那仍是一段簡樸、干凈、有些清教徒味道的生活,但,正因此,它卻感動了這群美國年輕人。觀察組的一個成員夸張地正話反說:“延安惟一的不好,就是在重慶我們可以輕易找到妓女,在延安卻怎么都找不到。” 中國式的古老、厚實、悲壯,滲透著這些美國小伙子的天真、樂觀和自信。絕大部分人都有著這樣的延安印象:延安人人有飯吃,每一個青年都以參軍為榮,整個社會朝氣蓬勃。絕大多數人都認識到:延安將引領未來中國,也將牽動世界格局。其中的一些人,如謝偉思、戴維斯、盧登等,甚至超越了“史迪威精神”,他們意識到,對一個瀕臨絕境達百余年的國家來說,奢談形式民主是多么可笑。華盛頓如果繼續因為意識形態而偏袒重慶的話,那么,美國將失去延安,也將失去中國。 延安改變著他們的中國觀點。但此時,在煙波詭異的重慶,一些重大的變化卻悄悄發生著。 史迪威危機 在許多人看來,史迪威的被召回是中美關系的一次倒退。它對“迪克西使團”的打擊更是致命的:沒有了史迪威的觀察組,還能執行它推動華盛頓與延安關系的核心使命嗎?失去了史迪威的考察組,還能走多遠呢? 派出觀察組的當月,一切似乎都還很順利:在羅斯福的壓力下,蔣介石同意把軍隊交給史迪威,延安更滿口允諾。但幾乎一轉身,蔣介石就翻臉了。 依舊是7月,蔣介石要求羅斯福派一位“富有遠見、有政治能力和想像力的人”來中國。言下之意,是史迪威對政治一竅不通,而中國的問題不能單純地在軍事立場上看待。幾經猶豫,羅斯福作出一個折中的決定,挑選赫爾利少將充任調停“蔣-史”矛盾的私人特使。 歷史證明了,由赫爾利充當這個“調停人”,是一個大錯特錯的決定。 1944年8月18日,赫爾利走出了他的第一步。在莫斯科機場,他直截了當地問俄國外長莫洛托夫:蘇俄如何看待中國共產黨?莫洛托夫表示,俄國不關心中國的內部事務。赫爾利由此認為,缺乏蘇聯支持的中共,不可能有對抗蔣介石的決心和實力。這成了他此后中國使命的一個壓倒性信念。 赫爾利之行,一開始就偏離了航向:他的使命不是調停“蔣-史”矛盾嗎?他為什么關心蘇俄對中共的態度呢?他后來又為什么把手越伸越長,乃至調停起國共關系來了呢?對此,觀察組的發起人之一戴維斯在《抓住龍尾》一書中認為,赫爾利張揚的個性,使他一開始就不滿足于原有使命。 9月6日,赫爾利到達重慶,第二天就把蘇聯的態度告訴蔣介石。一種政治默契很可能由此達成了:蔣介石要以赫爾利替代史迪威,一是消除自己的威脅,二是通過赫爾利來保證美國的軍援;而赫爾利可以從“蔣-史”調停人,搖身一變而為“國-共”調停人,由此進入歷史。 9月19日,當白宮要求蔣介石把軍權交給史迪威時,蔣介石兇狠地還手一擊,他回復白宮:如果逼迫他,將導致“災難性的后果”。其話外音是他將與日本單獨媾和。這個對白宮的致命一擊,使羅斯福在10月18日無可奈何地表示,他將召回史迪威,而以資歷很淺、對赫爾利一味妥協的魏德邁將軍取代。 在許多人看來,史迪威的被召回是中美關系的一次倒退。它對“迪克西使團”的打擊更是致命的:沒有了史迪威的觀察組,還能執行它推動華盛頓與延安關系的核心使命嗎? 失去了史迪威的考察組,還能走多遠呢?但,對赫爾利來說,這卻是他中國使命和地位的一次質的飛躍。接著,11月1日,他的又一個重大機會出現了:美國駐華大使、“中國通”高思因為對赫爾利的不滿,提出辭職。 赫爾利這個人 赫爾利以處理一把青菜的交易方式,來處理中國的命運。被戲辱的、富于自尊的延安,從此不再信任赫爾利了,他們在當年12月開始尋找和華盛頓直接接觸的途徑—— 早在史迪威離職前后,戴維斯就擔心赫爾利會取代高思。但,白宮沒有把這個小外交官的警告放在眼里。11月7日,掌握了美國對華政策全權的赫爾利來到延安。就是這次延安之行,他被定格為一個小丑,一個空前絕后的笑話。 來延安的第二天,赫爾利給了毛澤東一份聲明,說那是他和蔣介石的“共同意見“。聲明的核心是要共產黨交出軍隊。延安當然不同意,于是提出了關于“聯合政府”的另五點意見。 讓整個延安目瞪口呆的事件發生了:和赫爾利主張恰恰相反的延安五點意見,僅僅隔了一夜,就被赫爾利自己全盤通過了!赫爾利在共產黨的五點意見里簽上了名字。他還自鳴得意地說,空白的部分,要留給蔣介石簽字。 赫爾利以處理一把青菜的交易的態度,來處理中國的命運。但事情還沒完,回重慶后,當蔣介石也斷然拒絕時,赫爾利立即反悔了。 這時的赫爾利如同無賴,他威脅延安:不許向外界、向新聞媒體公開他已在五點意見上簽字的事實。當毛澤東為此怒氣沖沖,表示可能公開這份文件時,赫爾利大聲咆哮:“媽的!他耍我!” 即使在這樣的局面下,赫爾利在11月29日給羅斯福的信里,仍然荒謬地寫到,“國民政府與共產黨之間的協議可能需要兩個星期……(他們都)急于達成協議……最近的耽擱主要是因為天氣……” 可笑嗎?這就是1944年、在中美關系和國共關系上負主要責任的一個美國特使。但可笑的又何止這些?《延安使命》寫到:赫爾利第一次到延安時,曾莫名其妙地對周恩來大叫:“喂,你在這兒是干什么的?” 一個叫艾奇遜的外交官曾希望白宮給予中共平等的待遇。他深謀遠慮地談到,這“可以讓共產黨站在我們這邊,而不會將他們推入蘇聯的懷抱”。赫爾利卻在這份電報稿上畫了一把手槍,并咆哮著:“我知道是誰起草了這份電報,是謝偉思!我最后要做的一件事就是懲罰這個狗娘養的!”…… 不僅在延安,在重慶的美國人,普遍認為他是“一個脾氣暴躁、自相矛盾的自大狂”;外交官和軍人給了他各種各樣的綽號,“吹牛大王”、“紙老虎”、“想成為偉人的草包”、“公牛”。一些歷史學家也認為他是“一個裝模作樣的傻瓜,一個演起來像大人物的無能者”。他對上司、對同事的無數撒謊例證在文件里經常被發現……被戲辱的、富于自尊的延安,從此不再信任赫爾利了,他們在當年12月開始尋找和華盛頓直接接觸的途徑。 兩封信和一份報告的命運 1945年8月,華盛頓又一次暴露了它對遠東局勢驚人的無知。它的一個歷史性的巨大失誤,決定了中美兩國從此漸行漸遠,一直到30年后才得以恢復對話—— 1944年12月初,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共同約見了觀察組成員、海軍中尉赫伯特·希契。他們委托他把一封信交給在華盛頓的歐內斯特·金海軍上將。為慎重起見,希契中尉耗費了十幾天功夫,起草了一份延安報告后才動身回美。之后,他分別拜訪了海軍部長詹姆斯·佛列斯特爾和國務院的約翰·文森特。他們兩人都看了這封毛澤東的信。 1945年1月6日,希契列席了參謀長聯席會議。在這個會議上,希契表達了他與考察組對中國局勢的深刻洞察。 他談到,占中國人口82%的農民,特別是華北農民,絕大多數都支持共產黨;他認為,不管美國花多少錢支持國民黨,都無法阻止蔣政權的崩潰;他因此建議,華盛頓“最好能重新審視一下我們的對華政策”。 但希契吃驚地發現,聽眾對他的話“反應平平”。更可怕的是,當失望的希契希望早些回到延安時,他得到的回答卻是,“我們不知道還會不會讓你返回中國”。不久他就被派往了菲律賓。很久以后,希契才知道,與戴笠有密切關系的、“中美合作所”的邁爾斯把這個情報給了重慶。傾向于重慶的“合作所”,比代表傾向于延安的“考察組”,在華盛頓有著更多的、主流性的支持。 第一次“直接接觸”的努力,就這樣無疾而終了。與此同時,1945年1月9日,毛澤東通過“迪克西使團”代理團長雷·克勞姆萊少校,尋求另一個“直接接觸”的途徑的努力也落空了。魏德邁把他和周恩來希望訪問白宮的信,扣押在了重慶。 接著,是事實上造成華盛頓與延安決裂的“2-28報告”事件。 1945年2月28日,由謝偉思執筆,一群年輕的美國外交官們撰寫了一份給國務院的正式報告,即“2-28報告”。報告要求華盛頓援助延安,認為這才是避免中國崩潰的惟一前途。但不久后,謝偉思等人卻被以“泄露國家機密”的罪名逮捕了。延安做出了強烈反應,《解放日報》的社論說,謝偉思等人的被捕不是泄露了什么機密,而是因為他們曾激烈反對國務院某些派系支持中國反動派的政策。 這些事件,讓延安憤怒了:延安只要求公平,但重慶和華盛頓都不愿意給它公平。只要公平,延安就可以毫不費力地贏得大多數選票,讓重慶垮臺。因此,重慶的算盤只能是讓延安先交出軍隊,而對此,毛澤東憤怒地說:這是要他們把“雙手綁在背后”再對話。 重慶這么做,是因為它的虛弱。美國這樣做的目的又在哪里呢?毛澤東似乎百思不得其解。1945年9月,阿諾德·達迪安離開延安的前夕,毛澤東問達迪安,既然華盛頓知道大多數的中國人都支持延安,為什么它的態度還這么消極呢?達迪安解釋說,美國長期有反共產主義的傳統,并且認為中國的共產主義與蘇聯的沒有什么區別。 既然如此,美國為什么還主張國共和談呢?毛澤東沒有問。而在60年后,我們或許能看得更清晰些:在冷戰即將揭幕的背景下,美國試圖以脆弱的國民黨為領導,同時利用共產黨的活力和領導社會的能力,以形成一個牽制蘇聯的力量。但這種以腐朽牽制新生、融合冰與火的算盤,無疑是一廂情愿的。它反映了美國對華政策的驚人天真,對這個以五谷與土地、社稷與倫理為象征的國家的驚人無知。在接下去的長長歲月里,華盛頓無數次地談論著“失去中國”的歷史責任。 1945年8月,華盛頓又一次暴露了它對遠東局勢驚人的無知。它的一個歷史性的巨大失誤,決定了中美兩國從此漸行漸遠,一直到30年后才得以恢復對話。 大轉折 1947年,經歷了963個日子后,“迪克西使團”最后的三名成員離開了延安。正如延安早就估計到的那樣,觀察組是“和平的最后保證”,他們一撤退,國民黨軍隊就開始進攻延安。全面內戰爆發了—— 1945年夏天,當歐洲的冷戰鐵幕已經拉開的時分,在遠東,美國卻頻頻敦促蘇聯對日作戰。美國的估計是:70萬關東軍有著巨大的戰斗力,由美軍主攻的話,巨大傷亡不可避免。它試圖讓蘇聯承擔代價,而坐收漁利。這是一個典型的“卞莊刺虎”之計。 但這卻是一個驚人的誤算:關東軍的力量早已枯竭了。蘇聯紅軍以摧枯拉朽的態勢贏得了滿洲、朝鮮和日本的北方島嶼。這種戰略轉折,使接下去的國共和談有了鮮明的爭取民主黨派、知識分子等中間力量的色彩,使和談本身變成了一張純粹的“民意牌”。 1947年,經歷了963個日子后,“迪克西使團”最后的三名成員離開了延安。正如延安早就估計到的那樣,觀察組是“和平的最后保證”,他們一撤退,國民黨軍隊就開始進攻延安。全面內戰爆發了。而在內戰基本定局的1949年春,毛澤東再次派遣黃華前往南京,拜訪黃華的老師司徒雷登。這個尋求獨立自主外交方針的最后努力,因冷戰的愈演愈烈,幾無懸念地流產了。它換取的,是兩篇針鋒相對的著名文字,《白皮書》和《別了,司徒雷登》。此后,新生的、危機四伏的新中國,只能別無選擇地一邊倒,并因此介入朝鮮戰爭。雖然50年代末事實上中蘇就已經決裂了,但一直到70年代、當中國重工業體系基本形成后,北京才重新對華盛頓打開了自己的大門。 |
| 新浪首頁 > 財經縱橫 > 國內財經 > 正文 |
|
| 熱 點 專 題 | ||||
| ||||
| 企 業 服 務 |
| 股票:今日黑馬 |
| 投資3萬元年利100萬! |
| 治口臭口腔潰瘍新突破 |
| 高血壓治療上的飛躍! |
| 揭開牛仔淘金的秘密! |
| 名品服飾 一折供貨 |
| 韓國兒童名品折扣店 |
| 50個好賺錢的精品項目 |
| 兒童EQ教育最新資訊! |
| 中國1000個賺錢好項目 |
| 房地產火爆 建材賺錢 |
| 經營愛情,賺浪漫錢! |
| 中華通典 驚世之作 |
| 治療高血壓不花冤枉錢 |
| 新韓國快餐年賺百萬 |
|
|
|
| ||||||||||||||||||||||||||||||||||||||
|
新浪網財經縱橫網友意見留言板 電話:010-82628888-5174 歡迎批評指正 新浪簡介 | About Sina | 廣告服務 | 聯系我們 | 招聘信息 | 網站律師 | SINA English | 會員注冊 | 產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5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