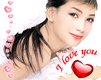|
本報記者 李明偉 上海報道
“因為一個病就可能讓他傾家蕩產,一個病就可能讓他幾十年的積累化為烏有。”國務院研究室綜合司司長陳文玲語氣沉重:在5、6月份的調研中,陳走訪了中部6個省,發現有35%~40%的人脫貧后,因病重新返貧。
9月5日,前一輪醫改討論熱潮中的兩大主角——國務院和衛生部的兩位人士同時現身中歐商學院“2005中國健康產業高峰論壇”。一位是陳文玲,她強調自己不代表所在部門,但是這并不能阻止人們對她特殊身份的重視;另一位則是被中歐副院長張維炯稱為“衛生部部長高強委派的專職代表”的衛生部政策法規司政策研究二處副處長雷海潮。
兩人一前一后率先在論壇發言。
陳文玲認為新一輪醫改必須要各方面聯動、一體化設計、共同推進,其中尤其要做到三個分離:公益性醫院和盈利性醫院分離、逐步實行醫藥分離和管辦分離;雷海潮則透露,衛生部聯同幾個部委已經起草“關于城市醫療服務體系改革試點指導意見”,并幾易其稿,目前正報國務院待批。
二人都認同,“使每一個人都能享受到最基本的醫療服務是政府的責任”,有所差異的是如何做到這一點。陳文玲提出:政府應該集中財政撥款辦好公益性醫院;雷海潮則認為:今后中國政府將進一步加強公共財政對衛生和健康方面的投入,來扭轉政府在衛生投入方面比例不斷下降的局面。
“看病難,看病貴”,歸根到底,是“錢”的問題,這些錢到底應該“誰來出”“出多少”正在成為各方爭議的焦點。
支出比例:個人劇增 政府急減
依據雷海潮的研究,從上個世紀70年代末到2003年,我國每年人均衛生支出總費用從約20元增加到500元,增長了24倍;1978年時,我國衛生總費用占GDP的比例只有3%,到2003年達到了6.1%,算下來,已經超過7118億元。
這說明老百姓兜里的錢越來越多地被用于衛生醫療支出,尤其是1995年以后,這種支出增長超過了人們收入的增長幅度,雷用“與GDP的彈性系數遠遠大于1”來說明這個問題。
從另一個角度能更加清晰地看清楚老百姓所承擔的“增長壓力”。
衛生總費用主要來自三個方面:居民個人花費、公共財政支出的花費、以企業為基礎的社會花費。雷海潮發現,居民個人花費在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只占衛生總費用的20%左右,到2003年,這個比例飆升到了56%;相對應的,政府的衛生支出則從1978年的超過30%下降到了2003年的17%,余下的社會花費也是從當初的近50%下降到了2003年的27%。
這些數據說明,在過去20多年里衛生費用的增加中,多數費用的增長是由老百姓個人承擔的,雷海潮據此表示:“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這樣看來也不難解釋。”
一直以來,我國從來沒有放棄醫療衛生事業的“公益”性質,并為此發展了城鄉醫療保險,但是從現狀看,我國醫保所覆蓋的人群“仍然非常有限”。1998年和2003年,衛生部有相關部門連續兩次開展以入戶為基礎的家庭衛生服務調查,從人群看,城市里沒有任何保險的人群比例反而在上升,從1998年的44.1%擴大到了2003年的44.8%,農村有所下降,從1998年的87.4%下降到2003年的79.1%,但是仍然處在一個非常高的比例。這再一次說明,老百姓看病基本上是自己掏腰包。
另外,即使是被醫保所覆蓋的人群,也面臨著一個問題。1999年以來,基本醫療保險方面的資金沉淀過多,據衛生部計算,基本醫療保險實施六年以來,每年資金的沉淀率高達24%~36%左右,2001年達到36%,這意味著參保職工100塊錢的資金有36塊錢在帳戶當中沉淀下來。在當前居民“看病難、看病貴”的情況下,卻出現這么高的資金結余顯然也是不合理的。
“公益”的異化
醫院等醫療機構的收費越來越高,似乎是老百姓“看病難、看病貴”的主要因素。
當陳文玲在會場上尖銳的指出:性質上是“公益性”的醫院卻“95%以上都變成了盈利性的商業運作模式”時,全場一片肅然——這是中央政府部門官員第一次這么公開、嚴厲地給醫院運作模式定性。
但從另一個角度看,我們國家現在所辦的所有醫院都“仍然是公益性的”——它們可以“占地不花錢、不交稅,政府仍然給財政補貼”,除此外還得享三大財源:一塊是藥品收入,前幾年最高時達到70%以上,這幾年經過一系列調整還在55%以上;另一塊是日益增長的高額檢查費,這已經開始成為醫院的主要收入來源;第三塊是高支耗材,也成為醫院收入的主要來源。
依靠這些支持和收入,醫院舊貌換新顏,陳文玲感嘆:“原來醫院大樓都是最破、最舊的,現在很多很多地方的醫院大樓已經和金融機構的和一些最富有的行業相媲美了。”
上海流通經濟研究所所長汪亮一直在研究醫改,他直指這是醫療衛生事業的“異化”,而其根源則在于醫改本身的“異化”——“改革的宏觀目標出現偏差,不是定在政府作為公共產品的提供者,而是想通過改革來為政府減輕負擔,減輕財政壓力。”
曾任衛生部醫政司司長、現任中華醫院管理學會副會長、民營醫院分會主任委員的于宗河對此也有同感,他清晰地記得醫院是如何一步步走上“創收”之路的。
1984年8月,衛生部起草《關于衛生工作改革若干政策問題的報告》,其中明確提出要“放寬政策,簡政放權,多方集資”;緊接著,一系列政策和來自醫院自身創新的“補償機制”開始不斷涌現:分解收費、“以輔養主”、“以藥養醫”、承包科室、興辦“院中院”,等等,形式不一而足,但宗旨就一個:創收。
“創收”還表現為有意的隱性“浪費”。曾任世界衛生組織副總干事特別代表的陳潔教授記得這樣一個場景:一次陪同世界銀行代表到醫院考察,發現一個小孩一邊在吊鹽水一邊又在吃蘋果,世界銀行代表大為驚異:“能吃蘋果就表明能攝取營養,不需要吊鹽水。”
經費補償機制
現任教于復旦大學公共衛生學院的陳潔教授認為,醫院走上“創收”的路子不能全怪醫院,歸根到底還是“經費補償機制出了問題”。于宗河也認為:下一步醫改的關鍵在于“用什么經濟政策去支持”,“歸納到一個問題,就是籌資機制”。
那么到底這已經超過7000億元的衛生總費用應該誰來出、怎么出呢?一種觀點認為主要還是要由政府承擔起來,“老百姓已經交過稅了,從道理上講不該再給一分錢”;另一種觀點認為應該用“市場化”的方式來解決,通過各種資本大量興辦醫院來形成競爭,從而實現降價和提升醫護質量。
于宗河偏向前一種觀點:“還是要以政府為主導,動員全社會資源,拿出GDP的5%~6%就夠了。”于認為,醫療衛生事業的改革不同于經濟體制改革中的企業改革,不能也是搞“市場”;醫療事業也不同于房地產市場,不應該成為“暴利的”,即使是民營醫院。
但是于也很清楚地知道,國家財政不可能支撐這么大盤子的衛生費用,算下來國家將比現在多支出5倍,這是不現實的。
與相關研究機構和政府部門都有接觸的于宗河設計了如下的解決思路:
第一,個人支付20%。于認為,為了防止“小病大治”等浪費,讓老百姓承擔20%也有一定道理,政府需要做好宣傳和解釋;
第二,政府在現在17%的基礎上,逐步將比例提高到20%,而這個撥款不光來自中央政府,各級政府都必須承擔一定比例,除非貧困地區;
第三,醫保在現在24%基礎上,隨著醫保面的拓寬和商業性醫保的發展,可將比例逐步提高到30%;
第四,剩下的30%分成兩個部分,一部分是通過加強管理減少浪費,以前的測算是在衛生支出中將近20%是以亂開藥、亂檢查、“小病大治”等方式被浪費掉了;另外10%則通過社會捐助、慈善事業等方式來籌集,也可引入民間資本興辦盈利性醫院,其賺錢的部分通過稅收方式截取并轉回公益性衛生事業部分。
“有退有進”的路徑
汪亮的觀點與于宗河類似,他提出了基于現實狀況的“有進有退”的改革路徑。
其提出的三個概念和相應承擔者是:
第一,“公共衛生醫療”,這是廣覆蓋的、每個居民都可以享受的基本的醫療衛生保障,由政府集中財政承擔全部投資并委托管理,其主體由三部分構成:目前所有的社區醫院、部分二級醫院、部分三級醫院。
所有的社區醫院構成一個有效的前沿衛生網絡系統,承擔常見病防治、婦嬰保健、傳染病防控等;二級、三級醫院大部分逐步退出,由社會來接手,但是政府依然要辦好幾家必須的二級、三級醫院,比如每個地方一家綜合性醫院、幾家專科性醫院(如精神預防中心、婦嬰保健院)等,與社區醫院形成轉診機制,從而實現小病到社區醫院,大病可轉診的體系。
第二,“公益性醫療”,由慈善機構來投資并運作,不以盈利為目的,尤其關注社會弱勢群體的醫療衛生救助。
第三,“經營性醫療”,由社會資本以市場方式運作,滿足基本醫療需求之外的那些個性化、特殊性的需求。對于這部分醫院所產生的利潤進行征稅,并把稅收返還到第一部分的公共衛生醫療事業中去。
汪認為,那些航運、郵電、鐵路、防治等行業性醫院,實屬“重復建設”,應該改制,交由社會來承辦。
與陳文玲的觀點相同,汪認為醫改的重要保證是要實現“管辦分離”,那些非經營性的國有資產的管理要同步改革,必須打破衛生部門既管人又管資產導致改革難以推進的現象,路徑就是將這些資產交由國資委管理,衛生部門承擔市場環境的建設和維護,而在醫院的具體管理上,則由國資委公開招標,交由那些專業的第三方機構經營管理。
陳文玲在發言時指責:“一些地方的衛生部門實際上還是國有醫院的總院長,還在代表醫院招標、采購,代表自己原來所隸屬的醫院,甚至維護某些既得的利益。”
于宗河認為,以前醫改“不成功”的關鍵還在于“落實不好”,其實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類似問題已經引起社會極大關注,中央政府于1996年時以空前檔次和規模召開的全國衛生工作大會,明確了衛生事業的“國家實行一定福利政策的公益事業”性質,并具體提出了40條決定,“如果這些決定都得到落實,就不會有今天這些問題了。”
陳潔也建議,新一輪醫改,如果能成立直屬國務院的醫療衛生事業改革委員會,以此來領導和協調改革,“可能效果會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