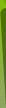上海不同收入市民的區域分化 | |||||||||
|---|---|---|---|---|---|---|---|---|---|
| http://whmsebhyy.com 2005年01月25日 22:51 外灘畫報 | |||||||||
|
眼看著自己這套3室2廳的房子,單價已經漲到了每平方米1萬4千元,張薇暗暗慶幸5年前把房子買在中山公園附近真是明智之舉。 “這里是市中心,離地鐵二號線和三號線很近,到哪里都很方便,這是我們搬過來最大的原因。”這個30歲出頭的保險公司職員,7年里搬了兩次家,2003年7月她和家人把位于徐匯區與閔行區交界的梅隴地區的舊式公房賣了,搬進了長寧區虹橋新城,開始了“上只角
如今,張薇一家的年收入在40萬左右,他們完全有能力選擇自己喜歡的生活區域。然而在1998年的時候他們還沒有這個概念。 那時,張薇和先生楊玉春剛剛結婚,單位里分配給楊玉春一套在徐匯區梅隴11村的2室1廳作為婚房。“我當時覺得2室1廳蠻溫馨的,兩個人生活正好”。后來,楊玉春的收入不斷地增加,加上中心城區不斷有新樓盤開出,改變了張薇的看法。 “隨著商業樓盤的開發,高收入階層開始考慮重新布局自己的住房環境,老上海‘上只角’的遺傳因素又重新顯現出來了。”上海大學社會學系顧駿教授對這種遷回中心城區的行為歸結為城市舊城改造和樓盤開發的結果:“凡是大面積開發高檔樓盤的區,進駐的高收入人群越是多,長寧區就是個很好的例子,古北地區和中山公園沿線都漸漸形成了成熟的社區。” “上海這兩年來的整體規劃和城區建設,自然而然地把低收入人群遷移出了中心城區,根據收入高低在城市里形成不同的聚集區,就使居住出現了階層分布。”華東師范大學教授、中國城市社區研究中心主任劉君德表示。 遺傳“上只角” 在老上海語言里,“上只角”、“下只角”代表了區域分化。“上只角”就是指城市西區的高級住宅區,“下只角”自然指的是那些低級住宅區,兩只“角”的房租可以相差三四倍甚至十倍以上。 上海“地傾西南”的狀況,是由歷史原因形成的。解放前,上海原來的公共租界是在南京路一帶。法租界是在淮海路一帶,而東北的楊浦、閘北、寶山都是工廠區。 上海城市以蘇州河為界的“上只角”和“下只角”之分的陰影,“成了社會學的遺傳因子,至今還在有些人的頭腦里生根發芽”。 在浦東開發開放以前,“寧要浦西一張床,不要浦東一間房”的觀念使得很多的浦西“上只角”人一家三代住在十幾個平方米的閣樓里。按照芝加哥大學教授E.伯吉斯著名的同心圓理論,城市的發展更像一組同心圓,這組同心圓的核心就是中央商務區(CBD)。伯吉斯認為中心區域的周圍是一些低收入家庭的住所,或難以提供足夠利潤的商業活動場所。 1995年以后,上海中心城區(黃浦、盧灣、靜安區)改造速度明顯加快,近郊區和中心區的邊緣區域(楊浦、虹口、閘北、普陀、長寧、徐匯區)住宅小區建設發展飛快,大批居民由中心區內核心區域的原居住地遷往近郊區和中心區邊緣區域的大規模新建居住小區。 上海社科院人口與發展研究所研究員沈安安認為,影響上海人口分布的因素很多,政府的政策和規劃,進行工業布局的調整是影響上海人口再分布的一個重要原因。 為實現將上海建成國際經濟、金融、貿易中心的戰略目標,上海開始了產業結構和工業布局的大調整,中心城區的工業產值比重從1990年53%下降到1997年的28%左右,而郊區則從47%上升到72%。企業的大批外遷帶動了部分企業職工居住地的改變。 “而房地產價格的總體水平和土地的級差價格決定了商貿、居住、工業等功能用地的聚散程度”。上海不可避免地出現了“郊區化”,隨著內環線、南北高架等道路設施的建設以及中心城區功能的大置換和城市邊緣新城區住宅的大規模建設,中心城區過密的人口迅速向邊緣城區擴散。 郊區化的異變 雖然上海中心區的人口密度由于市政動遷不斷大幅下降,但仍然沒有改變人口向中心區高度集聚的分布格局。 沈安安的研究表明,目前9個中心城區2000年“五普”時的人口密度達23944人/平方公里,是全市區平均人口密度的9倍左右。 各中心區域的人口分布也呈現不同的變化,“近兩年來大力開發房地產的中心區域,如盧灣、長寧,通過高檔樓盤的開發,已經開始吸引高收入人群重新回到市區,而樓盤開發較少的靜安區則仍然維持原有的面貌。”顧駿認為。 高收入人群往往在中心城區和邊緣城區都有住宅,平時他們就選擇交通方便的中心住宅居住,比如張薇一家就在閘北區投資了一套1室1廳的房子作為出租。“關鍵中山公園附近的交通方便”。楊玉春打算再過5年可能去近郊買一套別墅,作為“世世代代居住的地方”。可是對此,張薇覺得還沒到時候,她參觀了朋友在郊區買的別墅:“那里冷冷清清的,花了十幾萬裝了防盜系統,還養了一條狗,沒有什么居住的氛圍。如果每天要趕去上班太累了。” “國際上的‘住宅郊區化’是指,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中產階級和高收入階層向郊區轉移,尋求更高質量的生活空間。而我們現在是大量通過拆遷等手段,進行低收入人群的‘郊區化’。這樣引起的分化,也將帶來不少矛盾。”劉君德對此表示擔憂,“在郊區大量建造住宅區,而附近沒有合適的工業工作區,郊區的低收入人群要負擔交通成本,到市區上班造成了交通高峰的擁擠情況,出現了不少社會問題。” “其實我們沒有必要走資本主義國家的老路,更多考慮老百姓利益的規劃和政策制定,是我們現在應該重點研究的。”劉君德說。 缺位的社區意識 像張薇一家這樣的較高收入的家庭,在上海越來越多,“現在中國在轉型階段,出現了一批專業人士,社會作用越來越重要,教育對一個人的地位也越來越重要。”上海社科院社會學所所長盧漢龍表示。 盧漢龍認為,他們還不算是真正意義上的中產階層,因為中產階層不是僅僅根據收入來界定的,傳統意義上的中產階層有他們的生活方式、階層認同和文化認同。“上海的中產階層還只是處于萌芽階段,因為他們還是缺乏文化意識”。 特別是在社區意識的覺醒上,中國的“中產階層”還只是“一只果肉飽滿而表皮粗糙的梨子”。他們開始重視和自己住在一起的是怎樣的人,是否一樣具有高水平的物質生活方式,但是卻沒有形成根本的社區自治意識。 劉君德認為在城市規劃中應整體考慮的功能分布、交通、產業、文化等,“要使居民產生對自己居住社區和區域的文化認同,最重要的是自下而上的管理方式,讓他們產生歸屬感”。 劉君德舉了一個加拿大多倫多社區的例子,政府引導白人、華人和黑人住在一個大型的社區內,高收入人群按照正常的市場價格購買社區內的房屋,而低收入人群政府提供補貼住面積較小的房屋。3-5年的實驗下來,各種人群都能和睦相處,文化程度不高或者收入較少的人群逐漸克服了自己的生活習慣,在高收入人群的幫助下,他們找到了更好的工作,各方人士自治管理社區,發展良好。 “在政府做好整體規劃之前,我們還很缺乏自治的能力,街道應該盡快放下經濟權力,恢復其本來的功能,專心地進行社區管理和治理,大力培養市民的社區意識。”劉君德說。 相關鏈接:
|
| 新浪首頁 > 財經縱橫 > 國內財經 > 正文 |
|
| ||||
| 熱 點 專 題 | ||||
| ||||
| |||||||||||||||||
| |||||||||||||||||||||||||||||||||||||||||||||||||||||||||||||||||
|
新浪網財經縱橫網友意見留言板 電話:010-82628888-5174 歡迎批評指正 新浪簡介 | About Sina | 廣告服務 | 聯系我們 | 招聘信息 | 網站律師 | SINA English | 會員注冊 | 產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5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