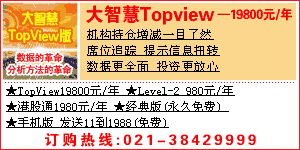|
|
|
經濟人理性與公共知識分子http://www.sina.com.cn 2007年11月12日 21:27 《管理學家》
經濟人理性與公共知識分子 作者:馬龍行 經濟人理性的濫觴 有人說,經濟學是一門科學,經濟人理性是現代經濟學的公理。既然是公理,本身就無須證明,更重要的是不允許有例外。如果拿中國的經濟學家們做一下驗證,我們就會知道此言不虛。中國經濟學家熱衷于“學而優則仕”,熱衷于驗證“書中自有顏如玉,書中自有黃金屋”的古訓,等等,都是經濟人理性的明證。如果有人認為這是中國經濟學家良好的職業道德—他們在自覺地維護著經濟人理性,存在著主觀故意,是方法論中應該排除的當事人或者說叫利益攸關者,那么,這種主觀故意本身就證明了中國經濟學家的經濟人理性。維護經濟人理性的基礎,就是維護整個現代經濟學宏偉大廈,就是維護這棟大廈的主人們經濟學家的利益。經濟學鼻祖亞當?斯密認為:“……我們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飲料,不是出自屠戶、釀酒師或面包師的恩惠,而是出于他們自利的打算。”聰明的中國人,自然是學到了祖師爺的精髓。 但是,也有個別冥頑不化者。天真的鄒恒甫先生似乎有些孩子氣,幾個月來像堂?吉訶德一樣大戰風車,批評以張維迎為代表的經濟學家們不務正業只為稻粱謀,企圖以個人之力對抗中國經濟學家整個群體。網上雙方各有一批擁躉為心目中偶像和英雄論戰,雖然說現在有一方好像占了上風,但聯系到現實中完全相反的雙方力量對比,孰是孰非,依然讓人有如霧里看花。 真相究竟是什么? 我們可以說鄒恒甫本人也是在實踐經濟人理性,這沒有錯,但只是公理劃下來的套套邏輯,說了等于沒說,沒有事實可以驗證的含義,沒有解釋力。就像你可以說一個人自殺,是經濟人理性,是因為死亡對他來說更便宜,他可以不用還畢生也還不清的債務,他可以不用忍受自己認為比死亡更可怕的痛苦和恐懼,等等。只是,我們還是可以質疑:生還是死,只是一個問題嗎? 人是上帝照著自己的形象造的,是萬物之靈,是大地的主宰,替上帝管理這個世界。人墮落之后,自己的欲望成了自己的“上帝”。根據馬斯洛的理論,人的欲望(需求)由低到高依次分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實現需求五類。人們在轉向較高層次的需求之前,總是盡力先滿足低層次的需求。生理需求是人們最原始、最基本的需求,若不滿足,則有生命危險。當一個人存在多種需求時,總是缺乏食物的饑餓需求占有最大的優勢;當一個人被生理需求所控制時,尊重的需求、自我實現的需求等都會被推后。有人認為,中國人都窮怕了,所以生理需求的滿足尤其重要,中國經濟學家自然也在其中。鄒恒甫是因為在萬惡的資本主義社會時間久了,腐敗慣了,所以他的生理需求才顯得不是那么迫切。假以時日,中國的經濟學家自然會上升到滿足自我實現需求的高級階段。有人根本不同意這個觀點,認為不但是在誤讀馬斯洛關于自我實現需求的定義,而且是在強奸中國經濟學家的民意。君不見,中國經濟學家們正在努力把個人的能力發揮到最大程度,以滿足自我實現的需求。 有人說:存在即合理。存在的一切事物都可以找到其存在的理由,可以找到合理的解釋。關鍵在于“理”是不確定的,我們不知道哪個“理”才是合理的。法西斯從人類普適性價值觀上講是不合理的,但它既然存在過,就說明它符合事物發生的規律,它消亡,也是在事物消亡的規律中消亡。所以,如果我們混淆了事實判斷和價值判斷,我們永遠不可能弄清楚事實的真相。 有人主張用“看不見的手”進行調解,用市場來解決發展中的一切問題。且不論市場原教旨主義的對錯,市場本身在實現資源的最優配置過程中就有缺陷。在自由的市場經濟中,資本會集中并導致壟斷,壟斷自然不會是效率最高的生產方式。中國的經濟學家們利用手中的話語權和學官的權力,壟斷了對中國經濟現象的闡釋權;他們利用政府與企業,壟斷了資源在經濟學家中的配置權,以“劣幣驅逐良幣”。看不見的手發揮作用,是以西方良好的道德法律制度為前提的,在中國這樣一個制度缺失、道德淪喪的時代,難道我們只能在等待人們的良心發現與坐以待斃中進行選擇? 有人論證說,經濟學家追財逐色爭名奪利的個體經濟人理性,將導致集體的非理性,最終將導致每個經濟學家的利益受損。經濟學家的名聲在大眾中越來越臭,有人甚至斷言,近幾年來,經濟學家在事實上正在被邊緣化。有網友更是大膽預測,十年后中國的經濟學家將會被社會遺棄而被迫退出中國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歷史舞臺。其實,用不著我們為中國經濟學家的利益擔憂,他們更清楚個人理性與集體理性的辯證關系,也比我們更加關心自己的利益。事實證明,他們實現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手段也是高明之極。也許,他們的心里在想:人生不過百年,在我之后,哪怕他洪水滔天…… 直覺告訴我們問題的存在,雖然我們可能永遠也找不到讓所有人都信服的解釋。但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受傷的是誰? 孫大午先生說:富人不是靠經濟學家致富的,但經濟學家致富都是靠富人。我們并不完全認同孫先生的觀點,在我們看來,經濟學家與富人更多地是在共同富裕。在這個以金錢為主要量度來衡量人的能力的時代,事實告訴我們,創富的英雄們絕對不是活雷鋒,更不是傻子。那種把富人當傻瓜的說法,我們只能認為要么是置事實于不顧,要么是一種酸葡萄心態。富人和經濟學家,更多地可能是出于彼此的需要而結成了致富共同體。在這個亂世快錢的時代,期望企業進行規范化的商業運作與管理的想法,只能被人認為是不懂企業、一廂情愿的書生之見。所以,批評企業沒有弄清楚經濟學家與管理學家的區別,認為是企業請錯了人的人,根本就沒有弄清楚企業的需求,“子非魚,安知魚之需”?企業可能需要管理學家,但更需要的是經濟學家。忽略經濟學家們的專業知識所能給富人及其企業帶來的些微創富幫助,即使是他們的話語權和身上經濟學家光環,通過富人的個人能量及其企業的放大作用,都可以帶來許多有形無形的好處。有人痛心疾首地認為,由此產生的交易費用,都是社會成本,減弱了公眾的社會福利。但也有人認為,這是社會轉型期的必要潤滑劑,能夠促進改革。無論如何,公眾都是被蒙蔽的對象,都是弱者,也只能做弱者,因為他們沒有維護自己權益的渠道。我們討論“經濟學家離企業應該有多遠”的問題,結論卻傾向于斷定這是一個偽命題。雙方當事人雖然各懷鬼胎,但都樂在其中。 呼喚公共知識分子 對于中國經濟學家,鄒恒甫先生的期望很清晰。按照鄒先生的建議,經濟學家們回歸象牙塔,做陽春白雪的學術,以中國人的聰明智慧和猶如過江之鯽巨大基數,等到一大批中國經濟學家在美國一流經濟學雜志上發表文章如履平地之時,那露出水面的冰山一角,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將是水到渠成之事。毫無疑問,鄒先生是愛國的,鄒先生的期望是美好的,鄒先生作為經濟學家中的一員是非常看重自己的職業的。但是,鄒先生的期望,顯然不是所有經濟學家的共識,更不是公眾的迫切需要。中國社會,有人曾經發現這樣一個有趣的現象:經商的眼紅讀書的,讀書的眼紅當官的,當官的眼紅經商的。乍一想,事實似乎并非如此。如今的三種人都是志得意滿順風順水的,哪有紅眼病的征兆?再一想,款博、學官、官商已經到處泛濫,哪還分得清是三種人,分明是一種人嘛,自然談不上誰眼紅誰。可是,相對于三種人融為一體后的個個腦滿腸肥,公眾并沒有切身感受到GDP數字上的快速增長。作為沉默的大多數,由于傳統上對知識的尊敬,他們更需要的是一個為他們說話的明事理的“文化人”,也就是知識分子。 在《現代漢語詞典》中,“知識分子”被定義為:“具有較高文化水平、從事腦力勞動的人。如科學工作者、教師、醫生、記者、工程師等。”公共知識分子則被認為是超階級的、代表社會良知的、理所當然的公共事務的介入者和公共利益的守望者。人類社會的每個階層都傾向于擴張自己的權利和利益,在西方是通過先哲設計的互相制衡的基本制度,亙古以來人類對上帝的敬畏,以及公共知識分子的獨立聲音,從制度、法律、宗教、道德、輿論等各個方面來規范和約束人們的行為。 在信仰缺失、制度不完善的中國,在一個轉型期社會里,公眾都有一種強烈的需求,需求專家對于某些事項做出解釋,“到底發生了什么”,“一些事件對于我們來說意味著什么”。媒體越來越發達,人們對專家的依賴似乎也越來越強烈。公共知識分子為了社會公共利益而發出的獨立聲音,彌足珍貴。經濟學被譽為“社會科學皇冠上的明珠”,中國經濟學家在發揮“經濟學帝國主義”的威力,對各種各樣的社會公共事務發表意見,自然而然地承載了許多中國大眾對于公共知識分子的美好期望。誠然,經濟學家有選擇做不做公共知識分子的自由;誠然,在道德上,為公眾利益代言的經濟學家并不一定比為某個利益集團代言的同行更優越;誠然,經濟學家是科學家,應該首先尊重的是科學事實;但是,請你首先表明或者界定清楚自己的角色。經濟學家不是通才,不是“十全老人”,定位為科學家者,就應該在面對大眾媒體的公共問題時免開金口。自詡為公共知識分子者,就不能處處為了一己之私利。濫竽充數者的道德自然被人們的質疑。 在中國經濟學家中,也不乏公共知識分子的代表。在2003年的孫志剛事件中,很多經濟學家發出了自己獨立的積極聲音。事實說明,公共知識分子的角色與經濟學家的科學家身份并不一定沖突。現在不是非常年代,無論是經濟上還是政治上,知識分子已經有了自己的生存空間,缺少的只是心靈的凈化。 經管分家 作者:莫士 “在管理領域,經濟學家要清楚自身的局限,不要‘手里有把錘子,看什么都像釘子’。”中歐國際工商學院肖知興教授的話似乎為喧囂的經濟學界澆了一盆涼水。 經濟學的繁榮伴隨的是市場經濟的發展。20世紀90年代初,伴隨著經濟發展的提速、各類資本市場逐漸滲入日常生活,經濟學開始走出大學校園,成為“顯學”。當發財的夢想開始與普通人緊密相連時,當“看不見的手”取代“看得見的手”成為市場主流時,能夠把握市場脈搏的經濟學家成為大眾眼中的明星。人們首先知道了老一輩的吳敬璉、厲以寧、董輔 ,后來又知道了中生代“京城四少”那一輩的鐘朋榮、劉偉、樊綱、魏杰、林毅夫、楊帆等,再后來便是新生代如日中天的張維迎、郎咸平。 “存在即合理 (existence in possible)”,時下經濟學家的“熱銷”自然證明了其生逢其時。大眾頂禮膜拜、企業奉為上賓、媒體連篇累牘,經濟學家已經成為全民娛樂時代不可或缺的元素。但是,透過光環的層層暈環,我們發現喧囂背后的悖論。 經濟無處不在,經濟學無處不在,經濟學家卻不能無處不在。這就如同物理定律影響萬物,物理學家卻不可指點江山一樣。世界本身就是一體,各學科的區分是專業分工的結果,如果各學科中所謂的專家屢屢越俎代庖,恐怕難免貽笑大方。 經濟學之于管理學,如同牛頓力學與量子物理,前者宏觀,后者微觀;前者僅僅將企業視為經濟規律下既定的變量,后者卻將企業視為研究的全部;前者力圖求得社會利益的最大化,后者卻在追求單個企業的最大利潤。 但是,從市場營銷到企業戰略,從人力資源到組織管理,似乎在所有管理領域指點江山的都是所謂的“主流經濟學家”。 究其原因,不外乎以下數條。 其中之一在于當今中國社會管理學家的稀缺。相比于經濟學的嚴謹理論與坐而論道,管理學無疑更偏重于實踐操作。無論是早期的泰羅、法約爾,還是今天的德魯克、韋爾奇,他們所擁有的不是嚴謹的數學推理、精妙的模型,而是在企業中長久的觀察、實驗,如同經驗方程相比于理論方程。所以,相比于經濟學家,管理學家更難成長,也更難以復制自己的成功。正因為如此,當一大批經濟學家能夠在改革開放后留洋學有所成時,管理學家的成長周期卻遠未達標。 此外,中國獨有的國情讓經濟學家能夠更為企業所倚重。由于中國的市場經濟脫胎于計劃經濟,所以政府指令的影響力與不可預測性都超過了西方國家。而在西方的管理學家眼中,政府的法令即便不是既定變量,也不是他考慮的主要因素,他最重要的使命是考慮在市場與企業的交互作用下,企業利潤的最大化。但是,當今中國急劇變化的市場卻無法給予中國管理學家如此穩定的市場環境。因此,對于中國企業而言,改變自身的收益可能遠遠小于改變環境的收益,所以它們將主流經濟學家奉為上賓,期望借助他們的力量影響政府決策。我們看到活躍于各大企業的經濟學家無不擁有強烈的政府背景,曾任人大經濟系主任、國資局科研所所長的魏杰,曾任職中央辦公廳的鐘朋榮,曾任職于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的樊綱……林林總總,不一而足。 雖然種種原因造成了現今中國經濟學家的熱銷與管理學家的難產,但是如此劍走偏鋒的形式終究不是常態。中國經濟最終將完全與國際市場接軌,中國企業也已經開始與國際對手正面過招。寄希望將國內市場不規范的做法應用在國際市場上,無疑將會頭破血流。所以,當開放的廣度與深度不斷擴大時,中國的經管分家亦當開始,各司其職,才是現代社會的常態。
不支持Flash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