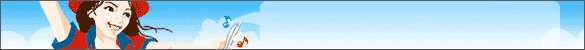|
-薛小和/文
父親從小天資聰慧,小學(xué)時(shí)學(xué)習(xí)成績(jī)很好,尤其是數(shù)學(xué)成績(jī)突出。16歲時(shí)因家境敗落輟學(xué)到杭州鐵路車(chē)站當(dāng)練習(xí)生,期間,父親憑借自己良好的數(shù)學(xué)基礎(chǔ),只用了3個(gè)月的時(shí)間就學(xué)完了原定6個(gè)月學(xué)完的會(huì)計(jì)業(yè)務(wù),車(chē)站的老會(huì)計(jì)因?yàn)橐恢睕](méi)有培養(yǎng)出能代替他的人,已經(jīng)多年沒(méi)有休假了,看見(jiàn)父親掌握會(huì)計(jì)業(yè)務(wù)的速度又驚又喜,放心地把工作交給父親休假去
了。
多年來(lái),父親被稱(chēng)作中國(guó)經(jīng)濟(jì)學(xué)界的泰斗,但他只有初中文化水平,他的經(jīng)濟(jì)學(xué)知識(shí)一方面是在三年的牢獄生活中從書(shū)本上自學(xué)來(lái)的,另一方面是1930年代追隨陳翰笙先生做農(nóng)村調(diào)查時(shí)從實(shí)際中摸索出來(lái)的。
父親是中國(guó)經(jīng)濟(jì)問(wèn)題的專(zhuān)家。一位曾在英國(guó)攻讀經(jīng)濟(jì)學(xué)的博士對(duì)福特基金會(huì)的美國(guó)人說(shuō),你要想了解中國(guó)的經(jīng)濟(jì)問(wèn)題,你就必須讀薛暮橋的《中國(guó)社會(huì)主義經(jīng)濟(jì)問(wèn)題研究》。父親對(duì)中國(guó)經(jīng)濟(jì)問(wèn)題的了解,完全來(lái)自于實(shí)際工作和不斷的調(diào)查。
父親是一個(gè)以思考為生活方式的人,工作時(shí)思考,寫(xiě)文章時(shí)思考,理發(fā)、散步時(shí)也在思考,就是在被批判、住牛棚時(shí)也不放棄思考。但由于歷史的限制,他頑強(qiáng)的思考并未為他創(chuàng)造出一個(gè)思想體系,當(dāng)他知道在他的有生之年不能實(shí)現(xiàn)這個(gè)創(chuàng)造以后,他就自我批判,就尋求,就吸收。他不怕否定自己,當(dāng)時(shí)代證明他的看法與現(xiàn)實(shí)相悖時(shí)他就一次又一次的重新起步,重新思考。當(dāng)然,思考的結(jié)果有變化也有執(zhí)著,在變化和執(zhí)著中他始終把握著分寸,這個(gè)分寸的界限就是最大多數(shù)中國(guó)人民的利益。
我曾經(jīng)問(wèn)過(guò)父親,你認(rèn)為你的身份究竟是共產(chǎn)黨員,還是學(xué)者。父親回答說(shuō):“我很想做個(gè)學(xué)者,但我首先是個(gè)共產(chǎn)黨員。”確實(shí),父親自1927年加入共產(chǎn)黨那天起,特別是30年代后有了學(xué)者身份、40年代后成為黨的高級(jí)干部以后,一直是給自己這樣定位的。這種定位使他70多年來(lái),始終把黨和人民、國(guó)家的利益放在首位,無(wú)論自己的命運(yùn)如何,都與黨的事業(yè)榮辱與共。但是,在信念堅(jiān)定的同時(shí),這種定位也給他造成很多矛盾,特別是當(dāng)他的理論觀點(diǎn)與黨的正式文件不協(xié)調(diào)的時(shí)候,這種矛盾甚至?xí)䦟?dǎo)致痛苦。
1982年5-9月間,按照當(dāng)時(shí)領(lǐng)導(dǎo)的意見(jiàn),為配合黨的十二大的理論準(zhǔn)備工作,國(guó)務(wù)院經(jīng)濟(jì)研究中心會(huì)同國(guó)家體改委組織了一次關(guān)于經(jīng)濟(jì)體制改革的大型理論討論會(huì),討論社會(huì)主義經(jīng)濟(jì)體制改革的指導(dǎo)方針。參加討論會(huì)的有300多人,累計(jì)召開(kāi)大小討論會(huì)不下70次,討論歷時(shí)4個(gè)月。會(huì)議開(kāi)始時(shí)是在十二大以前,9月份十二大召開(kāi)后,這個(gè)討論會(huì)于9月底結(jié)束。理論界的同志都知道這是一個(gè)非常敏感的時(shí)期。眾所周知,父親的理論觀點(diǎn)是主張社會(huì)主義經(jīng)濟(jì)應(yīng)當(dāng)是商品經(jīng)濟(jì)的,而當(dāng)時(shí)的中央精神是:“計(jì)劃經(jīng)濟(jì)為主、市場(chǎng)調(diào)節(jié)為輔。”父親知道自己是黨的高級(jí)干部,應(yīng)當(dāng)與中央保持一致,所以在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huì)以前,凡是公開(kāi)發(fā)表的文章都遵守了中央當(dāng)時(shí)的提法,自己的一些不同意見(jiàn)只是在允許的范圍內(nèi)以補(bǔ)充解釋的形式提出。但即便如此,在1981年中央書(shū)記處研究室整理的一份材料中,他還是因?yàn)閺?qiáng)調(diào)市場(chǎng)調(diào)節(jié)而被列為第四類(lèi)人中,同時(shí)在小范圍內(nèi)受到批評(píng)。在這種情況下,父親受命組織這個(gè)討論會(huì)感到非常為難。當(dāng)然,為難歸為難,對(duì)于父親這樣的老共產(chǎn)黨員來(lái)說(shuō)他只有一種選擇:在5月4日的動(dòng)員報(bào)告中,父親為自己的主張做了自我批評(píng),表示“這個(gè)說(shuō)法有毛病”,但他同時(shí)向大家提出一系列需要討論的問(wèn)題,希望大家敞開(kāi)討論。
我猜想這種矛盾決不止一次,這只是比較典型的一次,應(yīng)該還有更痛苦的。記得在“文革”后的1978年初,當(dāng)時(shí)“四人幫”雖已打倒,但黨在經(jīng)濟(jì)工作方面的指導(dǎo)思想并沒(méi)有改變。在2、3月間,父親去參加五屆人大,聽(tīng)罷當(dāng)時(shí)國(guó)家計(jì)委領(lǐng)導(dǎo)在人大做的計(jì)劃報(bào)告,父親回到家中非常生氣,以致拍著椅子的扶手失聲痛哭起來(lái)。他說(shuō),國(guó)民經(jīng)濟(jì)已經(jīng)到了崩潰的邊緣,這個(gè)報(bào)告還是陷在分錢(qián)分物的數(shù)字里,不講政策,不圖指導(dǎo)方針的改變。我當(dāng)時(shí)在工廠做工,父親說(shuō)的不大懂,不知該怎樣安慰他。以父親那樣平和、內(nèi)向、長(zhǎng)于忍耐的性格,急到痛哭的地步真是急到了極致了。因?yàn)榧保浴拔母铩焙笠换謴?fù)工作,他就到基層去調(diào)查,摸清國(guó)民經(jīng)濟(jì)的情況,因?yàn)榧保粚萌腥珪?huì)一閉幕,他就到處做報(bào)告、寫(xiě)文章,呼吁改革舊的經(jīng)濟(jì)體制。70年代末80年代初,雖然那時(shí)黨內(nèi)政治生活開(kāi)始正常了,但父親還是因?yàn)樗母母镏鲝埵艿搅藥状闻u(píng),有黨組的正式批評(píng),也有多年的老領(lǐng)導(dǎo)的不滿(mǎn)甚至拒之門(mén)外。在這種情況下,父親盡可能地堅(jiān)持了他的主張,很多時(shí)候是在忍耐和等待中堅(jiān)持的。
在紀(jì)律和個(gè)人觀點(diǎn)的矛盾之間,父親無(wú)論如何退守,都盡量堅(jiān)守著一條底線,那就是實(shí)事求是。父親是通過(guò)社會(huì)調(diào)查邁入經(jīng)濟(jì)學(xué)的大門(mén)的,所以,幾十年來(lái)他已養(yǎng)成了從實(shí)際出發(fā)、實(shí)事求是的思考方式和研究作風(fēng)。閱讀他的報(bào)告和文章可以看出,文章的行文也就是他的思考路線幾乎成了一個(gè)定式,講一個(gè)問(wèn)題先講現(xiàn)在的實(shí)際情況,再講關(guān)于這個(gè)問(wèn)題的歷史及政策演變過(guò)程,然后提出自己的意見(jiàn)。比如,他在1982年7月給張勁夫同志的信中,對(duì)《物價(jià)管理?xiàng)l例》中僅把“穩(wěn)定物價(jià)”放在首要地位,不提合理調(diào)整物價(jià)提出不同意見(jiàn)。他先分析了當(dāng)時(shí)的財(cái)政、物價(jià)情況,理解“穩(wěn)定物價(jià)確已成為全國(guó)人民的共同要求”的原因,再敘述了從1950年以來(lái)我國(guó)物價(jià)政策是怎樣在“穩(wěn)定”和“調(diào)整”二者之間把握的,在物價(jià)上漲時(shí)著重于“穩(wěn)定”,在物價(jià)趨穩(wěn)時(shí)著重于“調(diào)整”,指出:“《條例》不是《暫行辦法》,應(yīng)該看得遠(yuǎn)一點(diǎn),說(shuō)得全一點(diǎn)。”“不提合理調(diào)整物價(jià)是不完全的。”
與許多習(xí)慣于從理論推導(dǎo)中得出結(jié)論的經(jīng)濟(jì)學(xué)家不一樣,父親更習(xí)慣于從經(jīng)濟(jì)運(yùn)行的過(guò)程中得出自己的觀點(diǎn)。他不太注重概念,遣詞用句也不大準(zhǔn)確,他注重的是實(shí)際運(yùn)行過(guò)程和結(jié)果,注重從實(shí)際中總結(jié)出規(guī)律性的東西。70年代末80年代初,他到處呼吁改革,幾乎都是從20多年經(jīng)濟(jì)工作的經(jīng)驗(yàn)教訓(xùn)講起,他從20多年的曲曲折折中得出一定要按照客觀經(jīng)濟(jì)規(guī)律辦事的結(jié)論,深感進(jìn)行經(jīng)濟(jì)體制改革的迫切性;80年代中他反對(duì)通貨膨脹政策,也是歷數(shù)近七八年的宏觀經(jīng)濟(jì)數(shù)據(jù),甚至追溯到“大躍進(jìn)”時(shí)期和山東解放戰(zhàn)爭(zhēng)時(shí)期的情況,提出應(yīng)該“管住貨幣、放開(kāi)物價(jià)”而不是“管住物價(jià)、放開(kāi)貨幣”。
學(xué)者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共產(chǎn)黨人則要改變世界。由于父親將自己定位于一個(gè)共產(chǎn)黨員,所以他對(duì)社會(huì)經(jīng)濟(jì)現(xiàn)實(shí)總是保持介入的狀態(tài),始終致力于改革經(jīng)濟(jì)體制、推動(dòng)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事業(yè)。有人很奇怪,父親這樣一個(gè)老計(jì)委,怎么能如此堅(jiān)定地主張商品經(jīng)濟(jì),其實(shí)并不奇怪。作為一個(gè)共產(chǎn)黨人,當(dāng)他為之獻(xiàn)身的事業(yè)竟然走到與其初衷完全相反的道路上去,并且由他和整個(gè)國(guó)家一起吞下自己參與種下的苦果,給他造成的刺激會(huì)更深,促使他反省的動(dòng)力會(huì)更大,推動(dòng)他改革的愿望會(huì)更迫切,他對(duì)改革目標(biāo)的認(rèn)識(shí)也容易達(dá)到常人難以達(dá)到的高度。
父親像所有他們同時(shí)代的共產(chǎn)黨人一樣,由于歷史的局限性,由于他們個(gè)人經(jīng)歷、觀念、性格上的局限性,也犯過(guò)不少的錯(cuò)誤。父親就說(shuō)過(guò):“任何一個(gè)經(jīng)濟(jì)學(xué)家不可能完全超越時(shí)代的限制,我也不能例外。現(xiàn)在看來(lái),建國(guó)以后我在各個(gè)時(shí)期寫(xiě)的文章中的觀點(diǎn),有一些就是不正確的,甚至是錯(cuò)誤的。這些不正確的觀點(diǎn),有些是當(dāng)時(shí)屈從于政治壓力,不能暢所欲言造成的,有些是受教條主義和極‘左’思想的影響造成的。”他雖然是杰出的時(shí)代人物,但他從來(lái)對(duì)自己都有非常清醒、冷靜的認(rèn)識(shí)。
在我看來(lái),父親固然是共產(chǎn)黨人,但他更是智者,在他身上有著較強(qiáng)的知識(shí)分子特性:
——他始終保持著獨(dú)立思考的習(xí)慣,雖然有時(shí)他處于“沉默”或“失語(yǔ)”的狀態(tài),但他對(duì)事物從來(lái)都有著自己獨(dú)立的見(jiàn)解和判斷;
——他有著相當(dāng)濃厚的民主思想,他對(duì)很多問(wèn)題的解決辦法都帶有明顯的多元化傾向;
——他有著強(qiáng)烈的社會(huì)責(zé)任感,但他不是舉重若輕的戰(zhàn)略家,他只是利用自己的專(zhuān)業(yè)知識(shí)為國(guó)家和人民謀福利的實(shí)干家;
——他不大懂政治,更不玩弄政治,不會(huì)拉幫結(jié)派,不會(huì)阿諛?lè)畛校粫?huì)整人;
——他淡泊名利,忍辱負(fù)重,當(dāng)受到不公正的批評(píng)時(shí),絕不會(huì)認(rèn)為自己比黨高明,他對(duì)黨的服從并不一定是對(duì)權(quán)力的屈從,而是對(duì)真理(當(dāng)時(shí)認(rèn)為是真理)的認(rèn)同,或是以大局為重的自我犧牲,事后,他也絕不會(huì)為個(gè)人恩怨去算歷史舊賬;
在中國(guó)社會(huì)幾千年的歷史中,亦儒亦吏、亦官亦學(xué)一直是一個(gè)傳統(tǒng)。但在我國(guó)第一代的領(lǐng)導(dǎo)干部中,這樣的人并不多。父親就是身上帶有濃厚知識(shí)分子特性的共產(chǎn)黨人。共產(chǎn)黨人的黨性與知識(shí)分子特性在他身上的融合,有時(shí)引發(fā)矛盾,有時(shí)生成痛苦,但可能更多的時(shí)候是一種升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