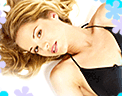秦暉:切實保障農民地權 發展鄉村社會民間組織 | |||||||||
|---|---|---|---|---|---|---|---|---|---|
| http://whmsebhyy.com 2005年12月03日 17:15 《財經時報》 | |||||||||
|
地權是農民公民權益的最低保障,但不是農村社保的藥方。應發展鄉村社會民間組織,以民間組織的合作、互助保障,彌補政府保障之不足 秦暉 土地權是多層次的,到底哪些層次的權利應歸農戶,哪些歸社區(集體),哪些歸國家
當前地權政策的主導方向應當是切實保障農民的地權,不一定是“所有權”,但至少是現行政策已允許給予的那些層次的權利。 地權:農民公民權的“底線” 在當前條件下侵犯農民的公民權益,往往是通過侵犯農民的合法土地權益表現出來的,因而保障農民地權不受侵犯是維護農民公民權的一個重要“底線”。在這個意義上,地權與其說是“最低福利保障”不如說是“最低權利保障”。如果農民簽訂的承包合同可以被權勢者隨意撕毀,農民可以被隨意趕出他們享有合法權利的那塊土地,那么他們還有什么權利是不可侵犯的? 目前我國的公民保障機制并不健全,公共權力的運作機制不夠規范,尤其農民更是權利易受侵犯的弱勢群體,我國目前推行的村民民主自治計劃的提法本身,也表明了鄉村民主仍在建設之中,在這種情況下,給農民的公民權設置一些保障的“底線”,劃定一些行政權力不宜進入的領域,是十分重要的。哪怕是以犧牲一部分“土地配置最優化”效益為代價也是值得的、利大于弊的。 而以所謂規模效益為理由來侵犯農民權利則必須避免。如果擴大干預農民地權確屬必要,也應當在公共權力運作機制改革后、在法治狀態下再來考慮這類問題。 此外,盡管保障農民地權未必會導致農地資源配置的優化,但它在經濟上仍有正面作用。如受保障的地權可以作為抵押,有利于建立農村信用體系,彌補如今日益突出的鄉村金融服務真空等等。 把推動農業規模經營作為變革土地制度的目的是不合適的。在我國目前的條件下,農地配置優化,或者說農地規模經營的主要限制條件在于,農民非農化就業前景不明。這一前景如果沒有很大的擴展,無論什么樣的規模經營都不可能有多少發展空間,不管是通過土地“私有化”以市場方式搞規模經營,還是通過“反私有化”以行政方式搞規模經營。 駁斥“土地保障論” 目前條件下我國多數農區農業經營的不經濟,已使土地喪失了產生“農業利潤”的資本功能,而成為一種生存保障手段。 現在有一種看法認為,農民可以用自己耕作的份地為自己提供“保障”,“社會”要做的只是行使權力禁止農民自由處置份地、削減農民持有份地的年限、強制農民承擔“保障”自己的義務。把“社會保障”不是看作政府的義務、公民的權利,而是看作政府的權力、公民的義務,這是一種顛倒的看法。這等于是政府讓農戶自己保障自己。 在社會無法承擔“社會保障”義務的情況下,農民依靠自己的土地維持生存是很自然的。問題是,這些土地真能提供“保障”嗎? 人們往往想當然地認為,農民流離失所、形成流民群乃至發生“農民戰爭”都是因為沒有土地,有了土地就有了“保障”。事實上,歷代農民戰爭發生時的社會危機中,常見的并不是很多農民無法獲得土地,而是相反的情景:沉重的負擔、惡劣的吏治以及種種天災人禍使農民有地不種、棄地而逃。 今天,在東部富裕地區農民的社會保障在很大程度上不太依靠土地(土地在這里更多是資本),而西部貧困地區,土地也無法提供社會保障,土地在這里更多地成了負擔。換言之,無論歷史還是現實,無論現實中的富裕地區還是貧困地區,“土地社會保障論”都是難以成立的。 從理論上講,社會保障是某種社會組織的事,而不是某種要素的事,因而“國家保障”與“土地保障”并不構成一種并列的選擇關系。國家(政府)財政如果無法承擔保障義務,替代的選擇可能是社區、企業、家族、教會、非盈利組織等等來承擔這一義務,而絕不可能是“土地”來承擔,正如不可能是“資金”、“勞力”來承擔一樣。 我國如今仍然是不發達國家,社會發展水平與經濟發展水平一樣還比較低,社會保障網尚不能惠及多數農民并不是什么難以理解的事。實事求是地承認這一點并不丟人,而如果自欺欺人地把事情說成是:我們沒有“國家福利”,但有“土地福利”,卻有可能使人誤以為我們的農民已有了“另一類型”的社會保障,從而取消了建立農村社會保障體系的任務。 同時,從上述社會保障的定義也可以看出,我國農村社會保障的缺乏不僅與經濟發展水平不高有關,更與社會組織資源的貧乏有關。官辦的組織無力或無法提供社會保障(即所謂國家保障缺乏),民間的組織又沒有,無怪乎只有“土地保障”即農戶自我保障了。 解決農村社會保障問題,要靠發展經濟增加財政實力,同時要以開明的態度鼓勵鄉村社會各種民間組織,以民間組織合作、互助彌補政府保障不足。 (作者為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 |
| 新浪首頁 > 財經縱橫 > 經濟學人 > 經濟學人--秦暉 > 正文 |
|
| 熱 點 專 題 | ||||
| ||||
| 企 業 服 務 |
| 股票:今日黑馬 |
| 12月大黑馬免費送!! |
| 投資3萬元年利100萬! |
| 美國保佳教您賺百萬! |
| 中國1000個賺錢好項目 |
| 開男士品牌名店賺瘋了 |
| 名品服飾 一折供貨 |
| 腎病、尿毒癥怎么辦? |
| 特色治失眠抑郁精神病 |
| 瑜珈美容俱樂部太賺錢 |
| 高血壓治療上的飛躍! |
| 開個咖啡店賺了幾百萬 |
| 拯救男人,還你健康! |
| 法國美容 浪漫賺錢! |
| 好男人更強,更自信! |
|
|
|
| |||||||||||||||||||||||||||||||||||||||||||||||||
|
新浪網財經縱橫網友意見留言板 電話:010-82628888-5174 歡迎批評指正 新浪簡介 | About Sina | 廣告服務 | 聯系我們 | 招聘信息 | 網站律師 | SINA English | 會員注冊 | 產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5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