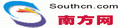|
|
全球化中的中國競爭力:2001年以來的中國奇跡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2月21日 11:46 南方周末
作者: 秦暉 -短短十余年間,中國制造的商品洪流般充滿世界,世界各地的資本潮水般涌進中國。中國成為“世界工廠”似乎指日可待。持續多年的高速增長增強了國力,也使許多國人日益自信。如果說1989年的電視政論片 《河殤》還在憂患中國的“球籍”,那么2006年又一部熱門政論片則在預言“大國崛起”了。 -1992年后的十五年來中國所取得的進步是巨大的。但是另一方面,這十五年積累的問題之多也不容忽視。十五年來,中國借助鐵腕體制降低“制度變遷的交易成本”,避免了一些民主轉軌國家疲于應付的各階層頻繁博弈的“拖累”,實現了空前快速的原始積累。 -這些年來,一方面規范化法治化的競爭規則正在形成,由此人們的自由得以增進;另一方面當代福利國家的種種進步也使中國的公共服務建設加快。可以說,文明世界的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不是斯大林主義)都在全球化中對我們有所促進,這也就是我們支持改革開放的原因。 全球化中的中國奇跡:“資本內逃”與“三順差” 1992年以來的第二輪改革,給中國帶來的變化舉世有目共睹。而2001年的兩件大事標志著改革開放進入了某種意義上的又一個新階段:這一年“入世”的成功使中國大踏步地進入全球化過程,而“9·11”事件及隨后的全球反恐使西方注意力聚焦于伊斯蘭地區,淡化了中美矛盾,促進了雙方合作并改善了中國的國際政治環境。兩者都對中國市場經濟的發展起了空前的推動作用。 新階段除了延續1992年以來的進程外,還有幾個明顯特點:第一是經濟加速,而且這種加速具有明顯的外向型特征。有數字為證:“入世”后中國的外貿總額五年呈三倍之增,從2000年的4743億美元飛速增加到2005年的14221億美元,2007年更達 21738億美元。而順差更是出現爆炸式增長:2004年為 320億美元,2005年 1019億,2006年達1775億,到了2007年更增長到令人目眩的2622億。不僅絕對值增長越來越快,相對增長率也越來越高:2007年與2001年相比6年增長11.6倍,而最近三年竟增加了8倍還多!(whmsebhyy.com/roll/20080111/13301925575.shtml 刊中國新聞網報道;《海關總署:2007年我國外貿順差達2622億美元》,《上海證券報》2008年1月12日)而流入中國的FDI則連續多年居世界第一(按有的統計口徑則僅次于美國)。2007年中國的經濟不僅外貿依存度(外貿額與GDP之比)已經很高,外貿順差率(順差與外貿總額之比)也已高達12.1%,而戰后時代曾經維持外貿順差額全球第一時間最長(長達21年)的德國,其順差率最高的一年也就是這個水平。(1988年為12.7%,見《帕爾格雷夫世界歷史統計 歐洲卷(1750-1993)》,經濟科學出版社2002年,616頁)除了石油輸出國之類“天然順差國”外,在世界主要貿易大國中這種情況很少見。 更耐人尋味的是:入世前我國的雙順差總額(貿易順差與FDI之和)經常高于外匯儲備增加額,人們普遍認為這意味著當時存在嚴重的“資本外逃”,并為此憂心忡忡。但入世后這些年情況完全倒轉:盡管雙順差總額高速增長,但外匯儲備的爆炸式增長更厲害,外匯儲備增加額反過來顯著高于雙順差總額。許多人認為這是國際投機資本(“熱錢”)隱蔽地涌入中國的結果,并由此產生了另一種擔心。然而,我覺得“熱錢”固然有,甚至那些非法聚斂的資本也可能仍在“外逃”——只是資本流入額更大,但是,那些流入的資本未必都是熱錢。事實上,“熱錢”冷錢都是資本,都尋求贏利最大化,兩者并無絕對的界限。如果“熱錢”流入后一直不撤走(由于人民幣升值與資本漲價兩大預期持續存在,這是完全可能的),也要尋求長期投資可能。而更重要的是,在外資爭相涌入中國的情況下,中國已經提高了進入的門檻,并不是只要并非熱錢就都歡迎。于是在國際資本過剩、理想投資場所不足而中國又有下文將述及的諸多引資“優勢”的情況下,即便長期投資者也可能“前門進不來進后門”,從而表現為外匯儲備增加額中高于雙順差之和的那些“誤差和遺漏”項。如果說這也是資本的一種“逃”術,那就不是中國資本“外逃”,而是外國資本(為躲避他們的工會、福利制度等 “民主社會主義”的壓力,或者為規避民主制下的“交易成本”)而“內逃”中國了。 中國資本“外逃”意味著腐敗與非法聚斂,外國熱錢流入則意味著金融風險,這兩種問題今天無疑仍然存在。但是如果長期投資者也踴躍到了“前門進不來進后門”的程度,那就意味著中國的確成了他們心目中的投資樂園。這些并非純投機的資本不是“惡意炒家”,(當然是在“惡意收購”這類語詞的意義上。資本進來不是為了搞慈善,即便“善意收購”也是為了賺錢,這是沒有問題的)他們是確實想在中國長期賺錢的。他們如此看好中國,至少從經濟增長的角度看當然是積極現象,說明中國的市場經濟建設的確有顯著成果。而在整個外匯儲備增加額與雙順差總額的平衡賬上,從入世前大量資本“外逃”造成赤字“遺漏”,到如今更多的資本“內逃”帶來反向的巨額黑字“遺漏”,在入世前中國已經存在的“雙順差”(經常項目順差與資本項目順差)基礎上,入世后又出現了“三順差”(國際收支總平衡賬的 “誤差與遺漏”項也由負數變成了正數),這可以說是新階段的第二個特點。經常項目順差意味著商品輸出,資本項目順差意味著資本輸入,而“誤差與遺漏”順差則意味著前兩者比賬面反映的更大,尤其是資本輸入可能不只像某些年份有的統計口徑說的那樣“僅次于美國”,而是不亞于美國。于是,人們似乎有理由認為那些“唱衰中國”的人已經輸了,而看好中國的觀點得到了證實。——當然,這只是在經濟增長(或者說GDP增長)這個角度看。 “共識破裂”:改革爭論的激化 短短十余年間,中國制造的商品洪流般充滿世界,世界各地的資本潮水般涌進中國。中國成為“世界工廠”似乎指日可待。持續多年的高速增長增強了國力,也使許多國人日益自信。如果說1989年的電視政論片《河殤》還在憂患中國的“球籍”,那么2006年又一部熱門政論片則在預言“大國崛起”了。兩部片子,真可謂給人滄桑之感! 隨著外向型增量的膨脹,經濟的“游戲規則”也繼續變革。2001年以來,在“改革”方面中國確立了“市場經濟”目標,在“開放”方面中國實現了加入WTO的愿望。盡管這個“市場經濟”前面還有“社會主義”這個意識形態限制詞,但現在世界上絕大部分國家的市場經濟也是有限制詞(“社會市場經濟”、“福利市場經濟”等等)的,而且除了官府的壟斷與特權仍然嚴重外,中國如今對“市場經濟”的其他“限制”(公共福利、勞工權利、社會保障、非營利部門發展、環保限制乃至宗教傳統的約束等等)絕不比所謂“發達市場經濟國家”多。以至于像張五常先生等人最近稱贊“中國比美國更自由”,而李嘉誠先生在疾呼警惕“民主化造成福利社會”之余似乎并不擔心民主的闕如會妨礙市場利好。另一方面,中國加入WTO雖然有過渡期特殊條款的保護,但這過渡期并不長,中國在全球化中“與國際接軌”的速度應當說是相當快的。 無疑,1992年后的十五年來中國所取得的進步是巨大的。但是另一方面,這十五年積累的問題之多也不容忽視。十五年來,中國借助鐵腕體制降低“制度變遷的交易成本”,避免了一些民主轉軌國家疲于應付的各階層頻繁博弈的“拖累”,實現了空前快速的原始積累。然而社會公正問題也越來越突出。我國如今不僅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數不斷升高,而且更重要的是因壟斷和特權造成的升高沒有說得過去的理由,使得大眾的不公平感比同等基尼系數下的國家更高。我國如今不僅存在著公共品供給的不足,而且還疊加了“公共品缺少公共性”的體制弊病:早在改革前的舊體制下,收入高者享受更高的公共福利,而收入低者公共福利就享受得更少,“二次分配”不是緩解了,而是加劇了初始分配的不平等。這個弊病在如今單向度的市場化改革中不僅沒有被克服,反有加劇的趨勢。體制缺陷形成的“擴權容易問責難,卸責容易限權難”,使得“放權讓利”的改革變成了“棄責爭利”,公共服務部門放棄服務責任,利用公共資源大肆“創收”,同時卻憑借壟斷權力排除來自民間的競爭…… 這一切終于沖破了“不爭論”的樊籬,導致了近年來相當尖銳的“改革論爭”,這成為新階段的第三個特點:先是在對“掌勺者私占大飯鍋”的批評持續多年之后,以“郎咸平旋風”為契機發生了激烈的國企改革爭論,接著“醫改報告”又引發了以醫療、教育問題為中心的公共品供應改革爭論,以及以物權法和農民問題為中心的經濟社會改革爭論,等等。這些爭論把1997年那場“自由主義與新左派”的“主義”之爭深化為一系列的“問題”辯論,它們的種種現實利益背景已經穿透意識形態的表象而凸顯出來,從而使爭論變得相當激烈,以至于有人驚呼“改革共識已經破裂”。顯然,這些年來,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并沒有像有些人設想的那樣“把餅做大”就能緩解“分餅不公”的矛盾,而是出現了經濟發展與內部外部矛盾同步持續深化的現象。“上訪潮”持續攀升,“群體性事件”大幅度增加。1992年這輪改革初起時,人們曾試圖把體制合法性建立在經濟增長上,當時常說東歐垮了而我們沒垮,就是因為我們經濟搞得好。但是現在,經濟高增長和社會不穩定同時發展的現象使人對此說日益懷疑。如果說在意識形態上“不爭論”不失為鄧小平的智慧之舉,那么在利益矛盾方面不允許博弈,就有極大的風險。 “尺蠖效應”與改革的調整 然而在現有體制下人們如何進行博弈呢?這些年來改革政策乃至改革戰略不是沒有調整,甚至可以說調整之頻繁舉世罕見,以至民間有“初一十五不一樣”之譏。然而似乎怎么調整都不對勁,這就是所謂的“尺蠖效應”:就像那一放一縮卻只朝著一個方向移 動的尺蠖,我們的政策一“左”,老百姓的自由就減少,但福利卻難以增加;政策一“右”,老百姓的福利就收縮,但自由卻難以擴大。一講“小政府”官員就推卸了責任,但權力卻依然難以限制;一講“大政府”官員就擴大權力,但責任卻仍舊難以追問。“右手”大動,公共資產就快速“流失”,但老百姓的私產并無多少保障;換上“左手”,老百姓的私產就受到侵犯,但公共財富仍然看守不住。“一個蘿卜兩頭切,左右都是他得”。于是客觀上的“尺蠖效應”的進一步突出,成為新階段的第四個特點。 就拿前一陣成為輿論熱點的“醫療改革”來說吧,當初說是醫療福利萎縮和“過分市場化”使人看不起病,出路似乎在于加大政府壟斷;然而不久就有權威消息披露:中國如今的公費醫療開支竟有80%花在領導干部身上,這樣的“福利”,究竟是誰之福,誰之利?增加這樣的“公共品”,能改善老百姓的醫療嗎?再如:“郎旋風”之后中國開始反對所謂“新自由主義”,一時似乎風向轉“左”,沒收陜西石油民企、在重化工等基礎領域搞排擠民資的“新國有化”、劃定國有壟斷行業等“大政府”政策紛紛出臺,然而與此同時,新一波“股改”卻采取了本質上近乎“國有股白送人”的私有化方式,其“右”的程度遠遠超過“郎旋風”之前的一切國有股減持方案。吳敬璉先生略表批評之意,立即招來一陣罵聲。也是,前些年為了國企“圈錢解困”,長期大熊市把高位跟進的廣大散戶小股民坑得夠嗆。如果當初聽吳先生的,在國企未改革不急于設局圈錢,那樣就不會有這么多人被坑。既然被坑了,在股指已跌去三四成時用現今的股改方式來補償,也算是補償了被坑的股民群眾。然而那時不補,愣是讓股指從2300多點跌到900多點,大部分小股民已經無法承受巨虧,被迫“斷腕”退場,只剩下實力雄厚的大莊家等著“抄底”了——這時“國有股白送”的改革才大舉出臺,客觀上給抄底者奉送了3000億元的凈值財富!(《股權分置改革使流通股東財富增3000億?》,北京普藍諾財經顧問中心:《每日財經專訊》第1237期,2006年7月20日)真叫來得恰到時候!郎咸平也好,鞏獻田也好,這時卻不吭聲了。如此尺蠖般的一收一放,國有資產也送掉了,小股民的私產也虧掉了,只有那些有來頭的抄底者兩頭通吃,既發了“國有化”的財,也發了“私有化”的財,你說這是“左”還是“右”呢? 中國的很多調整都表現出這種客觀上的“尺蠖效應”:今天強調加快城市化,便大舉剝奪農民地權“圈地造城”,但農民進城后卻得不到平等待遇;明天強調控制城市化和“復興農村”,便限制、取消農民遷徙權,但官府依然可以圈他們的地。今天說土地緊缺要“保護耕地”,于是就打擊“小產權”,嚴禁農民賣地,但官府依然想“征”就“征”;明天又說土地寬松可以放手開發,于是官府掀起圈地大潮,但農民土地仍然不許入市……顯然,形成這種怪圈的原因就在于那種“權既不受限,責亦不可問”的體制。在這種體制下即使政策設計者出于好心,實行起來卻往往“扭曲”,跳不出“權家通贏”的圈子。而憲政下的“天平效應”(政策趨左會增加人民福利,趨右則增加人民自由)則很難發生。 而中國與世界的雙向互動擴大,尤其是中國對世界產生了前所未有的影響力,則是新階段第五個、也是最重要的特點。
【 新浪財經吧 】
不支持Flash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