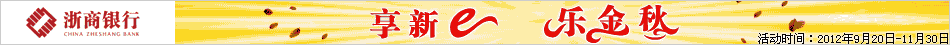正規信貸蕭條高利貸繁榮 放貸者自述月息超10%
夏心愉 高亞寧
“沒有水喝,就一定有人愿意飲鴆止渴。”在對《第一財經日報(微博)》談及高利貸存在的“合理性”時,金某一針見血。“這幾個月,我這里生意好得不得了,資金進出價格都翻倍。”他說。
曾在商業銀行工作近20年的金某現在是上海一家“投資公司”的總經理,從事的業務正是高利貸。
在金某看來,“4萬億”刺激政策過后,商業銀行今年開始進入“利潤回吐期”,不良反彈定會造成銀行對風險行業急收信貸,而這恰好能為民間借貸提供大量市場需求。看準了這一“掘金”時機,金某因此毅然從銀行中層領導崗位“跳槽”。
與金某的判斷類似,有業內分析人士認為,即便是在央行近期連續兩次降息之后,企業的信貸環境也仍將十分緊張。而正是這種正規信貸的“蕭條”,很大程度上造就了高利貸的“繁榮”。
放款月息能超10%
金某自稱是資金的“搬運工”。“‘高利貸’生意,說穿了就是資金的倒賣,只是賣價高過法律允許范疇。”在他看來,“做高利貸和做銀行思路一樣,都是資金的低買高賣,一求息差最大化,二求風險最小化。”
由此,他的公司運作總體有兩大任務,一是在發起人自有類似“股本金”基礎上再從民間集資,這些資金一般以“債”的形式而非“股”的形式進入,即作為公司借款,借據上寫明期限和利息;二是向急缺資金的企業放貸,“貸款模式越來越接近銀行模式,只是風險容忍度不同”。
資金如何定價?據金某透露,今年以來,隨著銀行對風險行業頻繁預警,越來越多的企業(包括他在銀行時期的老客戶)從正規融資渠道貸不到款,因此“投奔”他;而從6月開始,隨著半年末銀行還款高峰期來臨,客戶愿意接受的利息更高了。
“法律規定的‘銀行同期基準利率4倍’的紅線,在我們行業里,根本不叫‘高利’。”金某坦言,即使對于“優質客戶”,他的基準放息也收到月息3分。而對于那些“風險客戶”,月息還是3分;但在上個月,金某開始在借款期限上偷換概念——“1天按3天,甚至最高1天按5天計算”。
本報記者順著金某“客戶”的其他資金端采訪發現,近期,來自浙江、廣東一帶的資金方開價折合月息接近10%,甚至短期借貸超過10%的現象已經不算罕見。而這些救急資金,大多用于應急銀行轉貸及訂單短期墊資。
以極端的“1天按5天計”的價格推算,實際月息是15%,即年化180%。不過金某稱,沒有客戶會以如此高息長期借貸,他的公司也不可能相信客戶有支付年息180%的能力。“高價資金都是短期救急使用,借款期限一般不超過1個月。”金某舉例稱,“比如用于銀行轉貸。”
水漲船高。下游越來越大的需求也促使金某急需上游資金補充。他承認,近階段,公司融入資金的成本也幾乎翻倍。“給予投資方的回報現價是月息2分,而且可以不固定投資期限,100萬起投,投滿1個月后,隨時可以拿息撤資。”
本報記者觀察發現,除了能吸引社會閑散資金外,還有一些原本投資二級市場的小型PE也成了金某公司的投資方。而公司已經購置用于辦公的豪裝整層物業以及半數從銀行“跳槽”出來的“團隊”,似乎也成了“散戶”投資者的定心丸。
崩盤可能性漸增
在金某看來,外界對“高利貸”不加區分地一味“痛恨”有失偏頗。他將高利貸分為兩類,一類是古已有之的純民間小規模借貸,比如給賭博者放款;而他將自己“有組織、有規模”的公司看成另一類高利貸,即存在于灰色地帶的“類金融機構”。
外界對于高利貸批判顯而易見。上海銀監局副局長談偉憲近日在一場論壇上呼吁在刑法中增設“發放高利貸罪”。他稱,沒有企業能夠承擔借入高利貸所產生的財務成本,“不管是本分經營,還是不本分經營的(企業),最終都會資不抵債破產”。
金某也并不否認他在從企業的資金危局中“吸血”,但他反復向記者強調,公司實際幫助了不少企業轉危為安。
他表示,不少客戶公司在銀行貸款到期后獲得批復可以續貸,但公司自有資金或者在項目上,或者也被拆借,需要借一筆“過橋”資金。但正規融資渠道的單一、受限監管以及“一放齊放、一收齊收”的特性,切斷了本可生存企業的資金鏈。
不難發現,金某的公司正在過的“好日子”其實始自這一波市場資金面收縮。本來,市場上不少企業以“十個瓶子九個蓋”的方式繞轉資金和銀行貸款,當銀行收貸,原本的“九個蓋”變成了“八個蓋”,金某的資金,就成了必要時的一個“臨時蓋”。
但需要注意的是,金某已經意識到銀行收貸對高利貸的雙刃作用:“銀行收貸初期,增加的是客戶;銀行持續收貸,增加的是風險。”
金某稱,近期,客戶能提供的抵押物(通常是銀行不接受的房產余值抵押、車和其他貴重物品)變少;本來一些客戶還有各自行業里實力較強的公司愿意做擔保,現在這類“擔保”也少了。
當客戶的資金鏈越繃越緊,行業整體“崩盤”的可能性越來越大,銀行出身的金某“心里有數”。他不無唏噓地告訴本報記者,有不少客戶,從他還是銀行支行長的時候就跟著他融資,幫他消化分行壓下來的貸款指標。他一路看著那些老板身家變大,看著他們集體資金告急,然后放高利貸給他們,直到現在,“利息再高也不能做了”。
壞賬攀升催生討債行業
銀行的先期分行業急速收貸帶來了高利貸的“春天”;銀行的持續收貸又帶動行業整體告急,引發高利貸的壞賬上升。而高利貸和“黑社會”自古不分家,本報從江蘇幾家民間高利貸獲悉,由于高利貸壞賬攀升,為高利貸收賬的討債公司趁勢勃發。
金某自稱公司風險可控,還不需要外部討債公司,但他對這一現象卻表示理解。他稱,高利貸的致命傷在于非法,一旦壞賬,如果訴諸正常法律途徑解決,至少高息部分將不受法律支持。
本報記者此前從浙江采訪獲悉,當地不少地方政府在牽頭處理地區資金告急行業或企業債務重組時,就從政府層面下令,將所涉民間高利融資“一刀斬斷”。當地某地方政府官員告訴記者,高利貸本屬非法,因此在處理過程中,企業欠下的高額民間利息全部被豁免,而本金部分也可打折歸還。
不過,金某雖有隱憂,卻在其實際的某次訴諸司法操作中打了“擦邊球”。對于已經發生的一筆壞賬,金某將客戶告上法庭后,對于法律不支持的高息部分,金某以一筆計價的“違約金”形式予以固定并“合法化”。
金某自鳴得意的做法在本報采訪的幾名江蘇高利貸老板看來似乎過于“文縐縐”、沒效率。兩名徐州的高利貸老板告訴記者,在當地已經有了專門為高利貸服務的討債公司,按照案子的標的和難易程度計費,“一般討債事成之后,他們分走10%~30%的錢”。
某高利貸老板稱,當地的討債公司員工多半是社會閑散人員,打砸搶都在行。“他們中的很多人原本是干拆遷的,現在討債賺頭好,就都過來了。”他稱,討債的數額幾萬、幾十萬、幾百萬都有。
“討債公司還有一個作用,就是跟蹤(債務人)。”他說,現在借錢的怕欠錢的,因為債務人一般都不止一頭欠債,“先還別家的、轉移資金的、逃跑的、自殺的太多了”。
該老板向記者倒苦水:“能好言相勸的,誰也不想把事情鬧大。”他說,在他手里借錢的,不少都是鄉親或朋友、朋友的朋友,他一般的做法是到對方家里去磨,勸說對方把僅存的資產變現,傾家蕩產還債。所謂的“好言相勸”,是承諾對方,只要自己不倒,日后會按月支付對方家庭和子女的教育開支。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