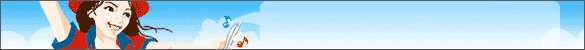|
2月21日,新華社受權播發《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若干意見》,這份2006年“中央一號文件”,為“后農業稅時代”的中國農村和農民勾畫了未來圖景和政策路徑。
有人預言,新農村建設將改變中國。
事實上,與歷次的新農村建設相比,此次新農村建設,不是對以前概念的簡單重復,而是有著非常明顯的時代特征。
走進浙江第一鎮
□本報記者 張華勇 章再亮 發自浙江紹興
鄉村形態的淡化,時于楊汛橋是最近10年的事。10年前紹興縣的這個地方,尚處于工業化初級階段,但隨著三次企業轉制,2001年之后出現了7家企業上市的井噴效應,股市流傳“楊汛橋板塊”的說法,這個鎮也因而一夜成名。
楊汛橋模式成為區別于溫州模式和蘇南模式的新“浙江經驗”。這個鎮2005年完成生產總值52.37億元,人均GDP超過1.8萬美元,連續三年蟬連“浙江省最發達100名鄉鎮”之首。
從鄉鎮集體企業、私營企業向現代企業制度的成功轉型,被認為是楊汛橋模式的靈魂。然而這個創富神話的背后,也經歷了鄉村城鎮化的一般過程,以至于被一些人認為是鄉村城鎮化的最高形態。
楊汛橋下一步的計劃是,在2010年前建成人口10萬左右的中小城市,對于這個原先由二十多個鄉村組成的松散小鎮來說,意味著社會結構也將發生深刻的突變。
“村中城”
楊汛橋鎮地處紹興縣西北部,杭州市與紹興市的中軸線上,緊鄰杭州市蕭山區,鎮域面積37.85平方公里,轄12個行政村,9個居委會,目前總人口6.8萬,其中常住人口3.3萬。其中的7個居委會是最近從“村”改為“居”的。
從任何一個角度看,這里既像“城”又不像“城”,用楊汛橋鎮黨委委員丁煥盈的話說是“不倫不類”。這里沒有核心商業區,沒有中心文化區,也沒有核心居住區,居民仍然主要依村而居。如果拋開現代化的工業園區和工廠林立的煙囪,這個鎮更像是一些村莊的集合。
一切生產和生活要素,仍然主要按村落而展開。與“城中村”現象不同,這里主要呈現為“村中城”現象,有工廠的地方,因為外來人口的集中,聚積起一些商業、服務業店鋪。
這是鄉村普遍工業化、城鎮化的結果,這些村莊最初都自發實現了工業化,依靠自身資源獲得了部分城鎮化的成功。
另一個景觀是工廠與村莊結合緊密,村莊天然作為工廠的居住區而存在,廠區與村民居住區融為一體。
城鎮基礎設施建設費用,鎮與村分擔,涉及村的,鎮里出60%,村里出40%。
楊汛橋鎮政府認為,楊汛橋鎮城鎮化滯后于工業化。鎮黨委書記趙建國說,一是楊汛橋鎮的城鎮建設投入,基本上來自財政稅收分成。此外,楊汛橋這樣一個財政收入幾乎可以與中部一個縣相當的工業化城鎮,缺乏管理和經營城鎮的權限。
超常的工業
2005年,楊汛橋鎮實現全社會總產值275.3億元,其中完成工業總產值208.44億元,經過1/4世紀的工業化,農業產值在GDP中比例只占1%。
一份未經公布的《楊汛橋發展報告》中說,除了專業化農業經營公司的員工(農業工人)和少數專業經營戶,真正以農為業、以農為生的傳統意義上的農民正在消失。工商社會,正在取代原有的農業社會。
在楊汛橋鎮,目前有各類企業1300多家,其中規模以上企業45家,企業集團11家。規模以上企業的資產規模已經超過190億元,所有者權益在80億元左右。
在這些企業的背后,涌現出以馮光成、金良順、龐寶根等為代表的一個企業家群體。2001年年底,“浙江玻璃”在香港上市,拉開了楊汛橋企業在海內外證券市場上市的序幕,到2004年,通過IPO和收購兼并,楊汛橋已擁有7家上市公司,目前還有幾家企業在準備上市。
一個小鎮擁有如此多的上市公司,在中國乃至世界,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跡。
超常發展的背后,記者注意到,楊汛橋鎮的大企業名稱里大多包含了創業者名字中的一個字,如光宇集團、寶業集團、永利集團等。
這些企業家的背后,又都差不多隱含一個共同的打工仔背景。在楊汛橋的企業家群體中,第一代企業家中的許多人,上個世紀80年代初期都有去武漢搞建筑、去江西采礦的歷史,他們曾經是木工或泥瓦匠。
楊汛橋的工業化經歷了鄉鎮企業發展的一般過程,但工業化突變的動因,卻被總結為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的“三次產權改革,奠定企業發展的制度基礎”,“海內外集體上市,創造現代企業制度建設的楊汛橋模式”。這個過程的實質,就是從集體所有制的淡出,過渡到私人產權所有制度。
楊汛橋鎮黨委書記趙建國介紹說,在企業上市的陣痛期,政府主動轉讓出了所持的股份,徹底割掉了企業紅帽子的尾巴。
經濟基礎的裂變,最終觸動積聚已久的民間力量的爆發,《楊汛橋發展報告》中說,從傳統農業經濟向現代工業經濟轉變的歷史任務,在楊汛橋鎮已經基本完成。
社會轉型
楊汛橋正在消失的不是農業,而是農村和農民。2006年楊汛橋鎮政府工作報告提供的數字顯示,2005年全鎮7家農業企業實現產值4億元,銷售收入3.9億元,利潤2480萬元。雖然這個數字相對于其工業產值,顯得杯水車薪,但絕對數量仍然令人艷羨。
農村土地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其制度設計本身,亦承擔著農村社會保障體系的功能。然而由于分散的土地經營長期的低產值、低效益,土地的社會保障功能被長期弱化,一定意義上,農村與農民也就成了貧窮、落后與高風險系數的代名詞,被一些人稱為非國民待遇。
在楊汛橋鎮,這樣的“農村”與“農民”,已經成為歷史名詞。據展望村黨支部書記唐利民介紹,展望村村民的各項福利待遇不低于城市居民。從1998年開始,凡60歲以上老年人口糧由集體免費供應,其他村民每人每年免費供應口糧170公斤;全村村民參加全社會養老保險,其中保險費由村委補助50%;村里還集體出資為全村村民投保了大病醫療保險。
楊汛橋鎮黨委書記趙建國提供的全鎮的數字為,老年村民從村鎮兩級每月可得200元的“退休工資”。而全鎮范圍的社會保障體系正在建立之中,一項計劃是建立鎮慈善基金會和慈善超市,發展社會救濟、優撫事業,實施弱勢群體救助行動。另一項計劃是拓展新型合作醫療覆蓋面。
然而由政府和集體全包全攬的社會福利模式,顯然并不適合,政府希望引入國家現有的社會保障體系,如“三險一金”制度。這一方面有賴于村民保障意識的提高,另一方面也有賴于相應機構的介入,甚至商業保險機構的介入。
一位當地官員說,楊汛橋整個社會正在融入國家的一體化進程中,然而“畢竟楊汛橋處于相對邊緣的地位,社會發展還遠沒到那一步”。
相對而言,農村戶口反而成了當地村民的優勢,擁有村里的戶口,即意味著享受村里的權益和福利。3月15日至17日,記者走訪了當地5個村(居)委會,得到的答復都是“不允許遷戶口”、“嚴格控制”之類。戶口在這里成了新的圍城。
新“二元社會”
當地政府官員有一句話說:“如果楊汛橋目前是一個工業化的小城鎮,那也是一個農民的城鎮!” 然而這句話的背后,無疑還隱含著一個不易察覺的事實:這是一個鄉村“新貴”的小城,也是一個鄉村淘金者的富貴鄉。
本地人與外地人之間,隔著一道無形的墻,截然分開成兩個很難相互滲透的社會。很難說這是完全由于戶口原因形成的,但戶口無疑再次扮演了構筑此新二元社會的重要角色。
鎮政府提供的數字顯示,楊汛橋鎮外來人口為3.5萬,比本地人口多出2000多人。外來人口的構成也日趨多元,高級技術人員、大學生、體力勞動者都有。
這些外來人口,主要為所在地企業的員工,也有相當部分在當地從事第三產業。據調查,當地跑交通運輸的,大多數為安徽阜陽籍人,開餐館的大多為四川宜賓籍人。而當地“打工仔”也以這兩個地方的人居多。
政府權威的說法是,這些外來人口中的五分之三長年住在這里,有的拖老帶幼落地已經十多年了。
記者找到當地一個湖南人群落,他們全部來自湖南鳳凰縣。最早來此地打工的田先生已在此12年,他當時16歲,后來在當地成了上門女婿。隨后其兄弟姐妹及姻親、同鄉,紛紛追隨而至,這個群落現在已發展到一百多人。
在這個群落里,田先生已經算是本地人,在工廠里作管理人員。其他人分布在各處大小工廠里,工資每天為三四十元,但是他們基本上租居在同一片區。他們形成了一個相對穩定的社會群落,差不多相當于戶籍地一個社會群落的移植。
楊汛橋鎮測算的全鎮人均GDP超過1.8萬美元,不包括外來人口。但這不等于外來人口完全沒有從經濟發展中受益,當地的一些公共設施,同樣向外來人口開放。
楊汛橋鎮已設立兩所民工子弟學校,但在解釋這一行為時,當地一位官員卻說,是為了減少民工子弟插班讀書現象,以減輕當地孩子家長對學校的抗議。
“先富村”與“新農村”
根據浙江省農調隊統計結果,2003年,浙江省最發達100個鄉鎮僅占全省1334個鄉鎮總數的7.5%,人口僅占全省全部鄉鎮總人口的19.9%,卻創造了全省全部鄉鎮44.7%的農村經濟總收入和45.8%的鄉鎮財政收入。
楊汛橋鎮正是這100個鄉鎮當中最大奇跡的創造者。浙江省農業與農村工作辦公室副主任顧益康3月20日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像楊汛橋這樣從先富起來的農村發展聚合起來的新興城鎮,今后在中國農村從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商業社會轉型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有可能比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所扮演的角色更為重要。這種在現行鄉鎮行政職能的制度框架內,靠內生增長的力量,將是未來中國農村現代化的主導力量。
顧益康還說,新農村建設應包括村莊和小集鎮兩塊,農村區域經濟和村莊,都在新農村建設的范疇之內。從根本上說,新農村繞不過局部鄉村的工業化和城鎮化命題。今后中國農村的城鎮化應超越地域概念。東部是先進工業基地,資本和人力相對集中的總趨勢不可逆轉,數千萬中西部勞動力轉移到這一新興工業地帶,也同樣不可逆轉。國家應出臺宏觀政策,加強引導,解決東部沿海城市化滯后于工業化的政策空間不足的內在矛盾,為中西部的新農村建設減輕人口壓力、騰出空間。
中國目前的鄉村城鎮化,仍主要是自發的城鎮化,還沒有走到自覺城鎮化的一步。楊汛橋鎮模式,對于新農村建設究竟意味著什么,尚未有定論。浙江大學農業現代化與農村發展研究中心林堅教授3月21日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說:新農村建設與推進農村城市化是什么關系,必須首先要回答,到了具體工作中,著力點是不一樣的。他還說,各地在新農村建設的政策目標設計上,應充分考慮差異化問題,各地肯定會走上多樣化的發展道路。“三農”問題與新農村建設,實際上與國家實現現代化是同一個概念、同一個過程,沒有一下子就解決的藥方,各地政府要相信老百姓的智慧,要有耐心積小勝為大勝。
鄉村治理與公司治理
原有的展望村行政建制下的鄉村治理,正與展望集團及其下屬的公司以及其他企業法人主導下的公司治理,發生著交叉與重疊。
像唐利民一樣,既是村干部又是企業領導的,并不止一人。據展望村黨支部張副書記說,展望有三個黨支部,其中有一個就建在展望集團,唐利民也身兼展望集團黨支部書記。
名義上展望村級行政,既管理所轄地的村民以及外來人口,同時也管理所轄地企業法人,是個全能的行政機構。然而事實上不難看出展望集團在村級管理以及公共事務上,起著主導作用。唐利民一再強調,在村公共事業上,展望集團的投入,有些甚至以捐贈的形式出現,但不難看出,受益者相當部分同時也是展望集團的員工及其親屬。
由于展望集團的強勢,村級行政與其說是管理,不如說是服務,其對企業法人的管理作用,顯得微不足道。唐利民對企業的領導,同時意味著對村的領導,或者說唐利民對村的領導,同時也意味著對企業的領導。
這就不難理解,在展望村,唐利民既作為展望集團董事長,同時也作為村黨支部書記的雙重身份。
這樣的治理結構,事實上使村級行政機構邊緣化。外來人口更多是被置于公司治理之下,村民一方面作為小股東,一方面也作為員工,事實上也主要被置于公司治理之下。
原有單一的鄉村結構,正演化為一種類城市社會結構。單位人身份超越居民身份,正成為所轄地公民的主要身份特征。這樣的社會結構,將更有賴于企業的穩定。
包括唐利民在內,所有展望人的雙重身份困境,都必然有賴于展望村行政治理結構的轉型。
在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歷史大背景下,有如展望村的一些先富村,顯然成為了另類,他們陷入了“城不城、鄉不鄉”的尷尬處境。這些現代工商業高度發達的地方,在完成了生產結構的現代化轉型后,仍然桎梏在鄉村治理的行政框架內。村莊行政身份的世襲,在這些先富村身上,必然成為一副制約治理結構現代化轉型的枷鎖。
展望村的實質,不是農村產業特征的現代化轉型。展望村最初從盤活人力資本開始,再到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引入現代產權制度和資本力量,最終由資本集結起所有的生產要素。最終,傳統意義上的鄉村形態在展望村消失了,傳統意義上的農民也消失了,展望村呈現出一種工業文明形態——一切以資本為紐帶進入工業化生產流程。
對于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而言,如果不是意味著生產關系的重新調整,將很難獲得推動農村現代化轉型的力量源泉。
[1] [2] [下一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