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管制的黃昏》跋:“管制”是否日近“黃昏”? | ||
|---|---|---|
| http://whmsebhyy.com 2003年02月11日 16:55 新浪財經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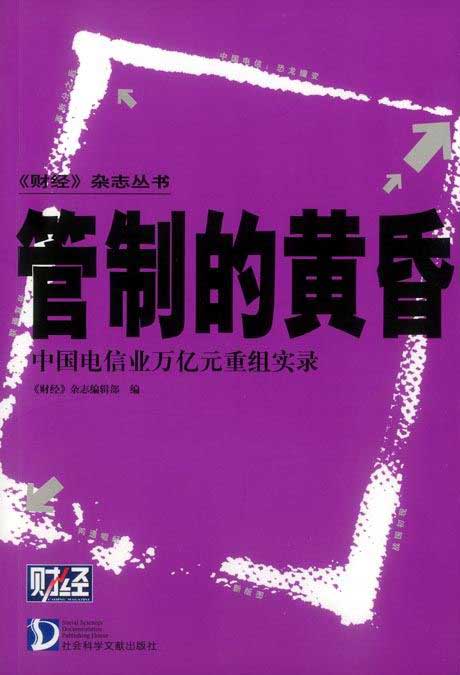 周其仁/文 這本書記錄了中國電信業從政府壟斷轉向市場開放的歷程。編者的意圖,在"編輯說明"里已經點明:僅將此書"作為對這一中國僅見的重大產業變革的忠實和完整的記錄。"當我
不容易之作 也許你會說,不容易。是的,不容易,真的很不容易。最大的不容易,是實事求是的不容易。"求是"之難,我們不去說了吧。否則面對發展電信業這樣同一個問題,無論過去、現在和將來,人們怎么總是會有那樣大相徑庭的看法和意見?但是搞清楚"實事",因此就容易嗎?比較特殊的困難,在于一個長期實行政府壟斷的經濟部門,首先是信息被高度壟斷。你要知道行業的實情嗎?你要追蹤市場的最新動態嗎?你要將撲朔迷離、牽動多方既得利益的敏感事件錄以備考嗎?甚至你僅僅要了解一些最基本的數據,比如行業的負債規模、公司的實際營運成本之類,你都不難發現,不容易,這些統統不容易。 何況免不了還要在報道中表達對電信變革的看法。要是你表達的看法--有時候只不過轉述了一家之言--偏巧與"有關方面"的看法不一致,你也許就要為此付出"從此更難知情"的代價。在滿足讀者知情權和獨立表達見解之間,有時候實在魚和熊掌不可兼得。離開這樣的局限條件,要體會"忠實和完整的記錄"字字珠璣的價值,不大可能吧? 《財經》并沒有什么特別的來頭。她在讀物市場里巨大的影響力,來自于從創辦之日起就堅持的對財經新聞的職業忠誠和專業水準。比較獨到的地方,是《財經》善于依托她的市場影響力,不斷進一步深度挖掘新聞事實。我們不妨再翻一翻本書吧:在電信這樣一個非常熱門的行業里,《財經》記者憑什么就可以"抓住"那么多的部長、老總、技術專家、投資銀行家、市場人士、種種相關機構和各類顧客,并可以直截了當地逼問"非常個人的"問題?我看來看去,以為秘訣只有一條,那就是《財經》把她來之不易的市場影響力,一次又一次用對了地方。 "史前"的教訓 當然,"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如果不是電信產業波瀾壯闊而又彎彎曲曲的變革,如果不是電信傳輸關系國民經濟信息化而又與我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應該不會有那么多的人希望一冊《管制的黃昏》在手吧? 我們無須羅列數據,就可以舉證近年我國電信業獲得了怎樣一種高速的發展。簡單一點,看一看街頭巷尾--許多內地城市也包括在內--多少普通百姓拿著手機在說話,就不會有誰對電信的偉大成就持有異議。問題是,電信的神速發展與本書的主題--電信市場打破壟斷、引入競爭的體制變革--究竟是什么關系呢? 往遠一點看,可以看得更清楚。實際上我國電信營運體制的大變革,早在1993年就開始了。那一年,中國政府決定成立聯通作為可以與原中國電信競爭的第二家國有電信公司。以此劃界,"前93體制"--整個電信市場由獨家政府電信公司壟斷--根本不可能容納電信業的高速增長,應該是清楚的。但是為什么連"93體制"--政府有意允許出現"雙寡頭壟斷競爭"的格局--還是不能解決問題,以至于還需要醞釀1998年以后又一波電信業的大重組? 要害在于,由政府主導的國有公司與國有公司之間的"市場競爭"模式,從一開始就有難以逾越的體制局限。政府的電信主管部門,一方面應該充當電信市場競爭的組織者和仲裁者,另一方面又是傳統在位國有壟斷公司的"老板"。一身兩任的角色沖突,使得1993年的改革嘗試無法開花結果。 結局并不出人意外。到1998年底,所謂"第二國有電信營運商"聯通只不過占有全部電信市場份額的1%!說新生的聯通太弱不是不可以,但我認為更為公道的結論是其對手--政企合一的原郵電部--太強。在我國國情里,要一家公司--哪怕是國有公司--與一個政府主管部門"競爭",不免幼稚得過于離譜了吧。 回顧起來,中國電信改革似乎"起大早、趕晚集"。畢竟,當年中國動手開放電信市場競爭的時候,世界上考慮這個題目的國家和地區還屈指可數。但是中國電信業早年的教訓卻醒目地提示我們:在政企不分的條件下,要把競爭引入行政壟斷行業是南轅北轍。 把這一點記為"史前教訓",是因為最近信息產業部長吳基傳先生撰文稱"我國電信業僅用三年多的時間就走過了許多發達國家需要七八年才完成的改革歷程"。1這里所謂"三年",指的是1998~2001年以分拆原中國電信為重頭戲的第二波改革。如果吳部長寫的是"正史",那1993/98年的聯通準入就成為"史前"事件了。好在將來的電信史家,應該不會漠視我國電信的市場改革自1993年起的證據。他們或許發問:如果"史前"改革就見到成效,中國電信業能夠大體沿著歐洲模式的路線從"雙寡頭競爭"進步到"多寡頭競爭",還需要后來對原中國電信再大動干戈嗎? 欲破壟斷先破迷信 歷史失去了"如果"的機會。但是,尚未解決的問題卻有幸再次被提上日程。1998年中國政府決定根本改革原郵電部體制,從郵政電信分家、成立信產部起手,完成政企分開,結束了行業主管部門又當裁判又踢球的荒誕局面。全面重組中國電信業開始了。從1999年開始,原"國家主體電信企業"中國電信先被"豎拆",后又被"橫拆",由一家電信營運商變成了四家;中國聯通得到空前"非對稱的傾斜性扶持";新組建了中國網通;準許鐵通進入公眾電信市場。更加令人矚目的是,中國電信業全面加入對外開放的行列--不但新組建的電信公司排隊走向國際資本市場,開啟了極有特色的首先與境外私人資本締約的道路,而且隨著加入世貿協定,中國政府承諾按照世貿協定的要求逐步開放國內電信營運市場。 本書忠實地記錄了這些令人目不暇接的電信業巨變。促成這么一場大規模產業重組的,是一股奇妙的"合力"--迅速集中的市場需求、新的技術可能性、全球信息產業變革的潮流、政府開放市場的決心、消費者意愿、各種專家意見和輿論壓力等等。不過,能夠把所有因素合成到一起的還是破除迷信、解放思想。道理很簡單,人的行為是頭腦指揮下的行為,不解除過去時代的思想禁錮,破除電信業的行政壟斷體制就寸步難行。 電信業向來被看成國民經濟的命脈,是所謂"戰略性的基礎產業"。這類定義充斥了含義不清的"大詞",而緊接著的推論從來也沒有得到經驗的嚴格檢驗:凡國民經濟命脈,皆不適合運用市場機制來平衡供求、配置資源。計劃經濟時代的確從來沒有給予通訊產業以任何"自由",但也從來未能使電信業真正成為國民經濟的一個強大產業部門。但是,這并不妨礙相當一些人把"戰略部門非市場競爭"奉為教條。按照這種教條,組建第二家電信公司根本就是多余的,至于允許多家電信公司展開市場競爭,更屬匪夷所思。 在中國終于確定要走市場之路后,繼續訴說電信業不宜市場機制變得不大順理成章。于是,"電信業的特殊性"得到了空前的強調。究竟什么是特殊性呢?據說是電信基礎網絡需要非常巨大的一次性固定投入,以至于市場上就只能容納下獨此一家的營運商,才能夠保證銷售數額足夠巨大的產出品來分攤全部網絡的固定投資。 這就是著名的"自然壟斷理論"了。應該是150年前經濟學家穆勒惹的禍,才使得當年學者對"為什么競爭的市場上只剩下惟一的一個供給商"的經濟分析,綿延不斷成為后來多少各國行政性壟斷受益方的護身符。人們似乎忽略了"自然壟斷"本身的含義。其一,那套理論假定技術和需求是給定的,就是說,一旦技術和需求--學者不可能在書齋里靈機一動就想像出的真實局限條件--發生變化,自然壟斷的范圍和規模也要相應變化;其二,自然壟斷說的是在市場競爭過程中最后"只剩下一個賣者",而決不是"只準存在一個賣者"。后一點誤解的結果十分嚴重,因為當政府揮舞看得見之手只允許存在一家壟斷商的時候,她實在無法知道,究竟哪一家、哪一種商業模式才是真正合適的。 更重要的是,自然壟斷理論試圖要解釋的經濟現象--市場在競爭中只剩下一家供應商--本身,從來就不曾在當年的穆勒和他的繼任者那里得到過認真地、合乎科學規格的考證。上個世紀60年代以后經濟學風氣轉變,德姆塞茨等一小批對實事不敢掉以輕心的經濟學家舊事重提,對"自然形成的壟斷包括煤氣供應、水供應、公路、運河和鐵路"刨根究底,才發現幾乎所有的"自然壟斷"皆不自然。歷久以來,這些行當就存在著多家供應商彼此之間的競爭,除非政府直接行使"非自然"的行政或政治的市場禁入,"一個市場只剩一個供應商"根本子虛烏有。結論令人尷尬:如果自然地開放市場競爭,那就根本見不到什么"自然壟斷";政府在市場禁入條件下實行的獨家經營,哪里是市場中的"自然"? 但是,這似乎并不能降低人們把"戰略產業理論"和"自然壟斷理論"直接轉化為重大政策選擇的熱情。就在醞釀我國電信第二波大重組的1998年,有關主管部門和專家提出了"由政府機構或國家主體電信公司獨家經營基礎電信網、開放電信服務競爭"的構想。按照這套構想,我國全部基礎電信網絡只能交給一家政府機構或所謂主體公司經管,以保證電信網絡的規模經濟和自然壟斷(!)特性,保證政府控制我國通訊命脈的戰略主導地位。可以開放給市場競爭的,只是不擁有電信基礎網絡的"服務"而已。 問題是,國際電信改革的普遍經驗已經可以顯示,繼續基礎電信網絡的獨家壟斷就根本談不到電信服務的市場開放。放眼四望,無論發達經濟還是發展中國家,哪里也找不到"基礎網絡政府獨家壟斷、電信服務市場開放競爭"這樣的怪物。好在開放的中國更傾向于從實際經驗、而不是從杜撰的理論中吸取力量。1998年以后的三四年間,中國電信業就在基礎電信網絡層次上實現了市場競爭,"數網競爭"已成為我國電信市場難以逆轉的體制特點。人們對此的評價當然不會一律,只是"無可奈何花落去",舊時代政府獨家壟斷電信的模式一去難以重返。 難題尚存 正如收入本書的評論文章"反壟斷也是行百里者半九十"所言,計劃經濟的壟斷實質上是國有經濟的壟斷。拿這個尺度來看問題,對我國電信業業已實現的改革進程--允許數家國有公司或國家絕對控股公司展開市場競爭--不可估價過高。本書收錄的關于2001年底中國電信集團再度被南北分拆的報道,也反映了政府用行政手段主導電信市場化改革之"悖論性不可能"。無論從哪個角度看,我們其實并沒有把握肯定我國電信改革真的在百里長跑中已經走完了九十里。 早在2001年中國電信"豎拆"落幕之際,筆者在一篇評論中就直言當時的電信業存在"結構性缺陷"。2002年中國電信再次南北分拆之后,我認為上述缺陷沒有減輕、而且好像還加重了。為了展望未來面臨的改革難題,讓我簡要地把這些看法提一下吧。 概括起來,主要是以下四點: (一)至今為止我國電信業的體制改革,基本局限在原郵電部門管轄的電信公網范圍之內,并沒有將全部專網包括廣電網絡資源通盤放入統一的信息傳輸網絡市場。已知的經濟規律是:"分立而不競爭"的割據,一定使我國電信業多受重復建設之害而不能取其利。 (二)目前的幾大電信營運商當中,只有中國聯通一家公司有權從事"全業務經營",因為只有她同時持有經營國際、國內固線長途和市話、移動通信、數據業務、尋呼和IP電話等各項牌照。其余各家均只被允許經營單項電信業務。撇開公平公正不談,這樣的分布能不能滿足市場對電信服務的要求? (三)電信業的資源分配還是行政機構主導,遠離價格機制。從頻道資源、營業牌照的獲得到電信服務費率的確定,基本上還是靠政府看得見的手分派,資源利用效率低,尋租舞弊機會多。"價格聽證"因成本數據闕如而流于形式。行業主管對"價格戰"的莫名恐懼以及對歐洲拍賣3G拍照教訓的不正確總結,似乎要使行政黑箱操作電信定價的模式長期合法化。 (四)電信業務對國內民營經濟的開放,缺乏正式的制度空間。最難以交代的事情是,世貿協定給予外資進入中國電信業的國民待遇,而中國本國的非國有國民自己并沒有如此待遇。更加麻煩的是,以下三點絕對加不起來:國家要保持對基礎電信公司的絕對控股,世貿協定承諾外資最高參股中國電信企業49%的股份,以及中外私人資本同等的國民待遇。三條當中,至少要除去一條才可能自圓其說。何去何從,有待加緊規劃、公諸天下。 以上各點有一個共同的出處:政府運用行政手段主導電信市場的開放。這本來就是一項具有內在沖突的使命。但是對一個從計劃體制出發的經濟而言,行政壟斷難道不就是政府的壟斷?要是政府不采取行政行動開放政府壟斷的市場,市場競爭從何而來?這就應了一句中國老話--解鈴還須系鈴人。問題是用行政性手法開放市場,副作用常常不小。要是政府有能力把"形成市場"這樣復雜的事情也弄得妥妥帖帖,還需要市場體制嗎? 說來不容易相信,正是矛盾百出的電信行業現狀,才教人對中國電信業的持續改革走向有點信心。這是因為,退回到政府獨家壟斷電信的機會不可說完全沒有,但怎么看勝算也不是很大。惟有行業現狀不容易維持,才需要繼續變革。 話雖如此,我還是認為本書定名為《管制的黃昏》可能是過于樂觀了。這里所講"管制",應該是指"政府為控制企業的價格、銷售和生產決策而采取得各種行動"。考慮到我國的傳統和現狀,容我實話實說,我可沒有看到政府對電信業的管制日近黃昏的跡象。最近朋友傳來權威人士的言論,大意是美歐等發達國家的網絡和電信泡沫破滅,中國電信一枝獨秀,今后更要加強管制云云。我還沒有來得及仔細研究這些言論,不過,"重新管制(re-regulation)"可能卷土重來的預報,早有研究管制的經濟學家在若干年前就發布過了。 要避免湯不湯、水不水的局面,當務之急是對中國電信未來五至十年的體制政策有一份長期規劃,作為對政府在電信市場上的行為有約束力的文件。最好借鑒世貿協定,簽出一份NTO文件--國內貿易和市場開放協定--來。這方面,多一點雅量聽聽國際業界關于我國電信業的政策風險過大、政策出臺透明程度比較低的抱怨,可能是有益的。 1999年春天,我在英國劍橋一家電信公司的櫥窗里看到陳列著一份國際電信業務的價格表。仔細看去,每分鐘打到中國大陸的電話資費是最高的,差不多要比通往鄰近的香港、臺北、漢城的資費高60%以上。幾年時間過去,中國人享受現代電信服務的條件大為改善。可惜相對而言,在今天世界主要國家的通訊資費表上,中國依然高高在上。下面是我剛從網上查到美國IP電話的廣告:大陸,每分鐘9.7美分;港臺,5.9美分。不要小看這條價格資料,它的含義實在重大。希望這最后寫下的小故事,給我們優秀的財經記者一點激勵,繼續關注電信業,直到下一個黎明。 2002年12月31日
|
| 首頁 ● 新聞 ● 體育 ● 郵箱 ● 搜索 ● 短信 ● 聊天 ● 天氣 ● 答疑 ● 導航 |
| 新浪首頁 > 財經縱橫 > 原創互動 > 正文 |
|
| 新 聞 查 詢 | |||||||||||||||||||||||||||||

| |||||||||||||||||||||||||||||
| |||||||||||||||||||||||||||||
行業信息高速路!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