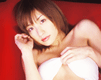|
本報記者 晏禮中 北京報道
當一輛馬車駛進潘石屹現(xiàn)代感十足的“建外SOHO”時,方蕾被警察叫走了。
馬車上拉著一枚“魚雷”。
方蕾是策展人。她向警察解釋道,那個用馬車拉“魚雷”的名叫吳玉仁的家伙不是什么“危險分子”,只是一名藝術家;“魚雷”也不是什么真的魚雷,而是件“藝術作品”。
這是“透明的盒子———有限空間的無限蔓延”藝術展開幕式上出現(xiàn)的一幕。
時間是5月23日。63年前的這一天,毛澤東發(fā)表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這次展覽是在餐廳、書店、酒吧、咖啡館、美容院、家具店、廣場、過道等非展示空間舉行的,游人、購物者及社區(qū)居民可以無限制地觀看、感受與共享藝術家的作品。”馮博一說。作為此次展覽的主要策展人,盡管他希望“這次當代藝術的展示活動能體現(xiàn)‘藝術為人民’的理念”,但對于那些喜愛“藝術”的“人民”而言,試圖完整“參觀”該展覽,只有一個字——難。
如果你非要來看看,那就來吧。
來自28位藝術家的作品散落并湮沒在“建外SOHO”100多家店鋪、廳堂和過道之中。你得先把那些參加了藝術展的店鋪找出來。按圖索驥找齊所有藝術作品的展示場地,這并不困難,只要你有足夠耐心并熱愛shopping的話。但是,要將藝術家的作品從商店里的裝飾品中分辨出來就并非易事了,昂貴的租金讓商家在店鋪裝飾上費勁心思,擺出來的東西甚至比藝術家的作品更有“想像力”。
當然,這里的“想像力”指的是在裝飾性方面。
商戶似乎只能讓藝術家的作品對自己的店鋪環(huán)境起裝飾作用,不能有沖突,否則他們就要拒絕。旅英藝術家徐仲敏本來的方案是在寫字樓的轉門上貼一張人的X光片,希望人們在進門的一剎那對自己的本體產(chǎn)生一些思考,不過,顯然樓里的業(yè)主們不愿意每天都推著“骷髏”進樓。
“結果換了一警察,湊合貼那兒了。”馮博一說自己做了那么多展覽,這次是最無奈的一次。“我可能有一點理想化,沒想到受到這么大的限制。要么是跟物業(yè)公司和商店經(jīng)理溝通,進行‘當代藝術的普及教育’,要么就是妥協(xié)之后跟藝術家商量如何改方案,但很多東西不是我跟人解釋怎么樣就能怎么樣的。”
對于那些“有幸”進入了店鋪的“作品”而言,藝術家本人的意圖已經(jīng)變得無關緊要了。在商家的眼里,這些作品的價值存在于裝飾性當中,而不是在其“意義”中。
盡管受到諸多的限制,盡管反反復復的各方面溝通讓馮博一面顯倦怠,但對他來說,這依然是一次對展覽空間的有趣嘗試。
“這次展覽不是給圈里人做的,也不會專門有人來看,發(fā)現(xiàn)它們的只是那些到餐館、咖啡館、面包店、商店去的人,我希望人們在日常生活中能夠不經(jīng)意地感受到藝術的存在。”馮博一說通過這次展覽,他最想表達一種“藝術寄生”的“第三空間”的概念。在他看來,“第三空間”的展覽方式具有某種實驗性。如果藝術家的工作室算作“第一空間”的話,美術館、畫廊、藝術中心等可謂“第二空間”,而這次策劃的非展覽空間就帶有了“第三空間”的意味。這種新的帶有差異性、流動性和不確定性的存在,不僅僅是物理空間位移的概念,更是一種生活、創(chuàng)作觀念及表述語言的生成,引發(fā)了人們對流動或變化的新展示地的思考。它將強調(diào)展覽及藝術家的作品與受眾的直接性、自然性地生成和接觸,從而削弱作品的被欣賞和被接受的傳統(tǒng)審美方式,即削弱當代藝術作品與受眾的距離感,使公眾在日常的生活中感受到當代藝術的近距離接觸,以及作品的親和力。
據(jù)說,最能體現(xiàn)“藝術為人民”這一主題的作品出現(xiàn)在一家名叫“蒂奧莎”的面包房內(nèi)。以創(chuàng)新的當代剪紙著稱的中央美術學院教授呂勝中和於飛二人合作,把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的節(jié)選文章用巧克力醬“印”在一片片面包片上,鋪滿一個大展臺,能看能吃,實實在在做到了為人民(準確地說是為消費者)服務。而另一個幽默且招人喜歡的“東西”出現(xiàn)在上島咖啡館的咖啡桌上,那是一個鐵鑄的蜂窩煤,作者是艾未未。“它沒有功能性,也沒有裝飾性,有一點幽默,有一點奇怪和不知所措。不經(jīng)意間,當代藝術和顧客傳統(tǒng)的審美思維進行了碰撞。恰恰是這樣一種碰撞,使這次特殊的展覽變得有點意思了。”馮博一解釋說。
這是我逛了一下午后,能記起來的兩件“作品”。
這也許是一個能夠很好體現(xiàn)“理想與現(xiàn)實落差”的展覽,同時也是一個能很好引發(fā)人們思考“藝術與人民”相互關系的展覽。
盡管接觸藝術作品的受眾已經(jīng)如策展人所希望的那樣,由那些懷著對藝術朝圣之心的參觀者換成了很少接觸當代藝術的“普通的大多數(shù)”,但我們也不難發(fā)現(xiàn),當藝術離開了它特有的場所,失去了它特有的表述語境時,面對的不僅是來自現(xiàn)實世界的限制和尷尬,在某種程度上,它似乎也失去了作為藝術的價值和尊嚴。同樣,我們也可以借此質(zhì)疑,在大眾面前,藝術是否需要以藝術的姿態(tài)出現(xià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