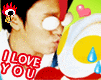| 全流通方案的法律解析 | |||||||||
|---|---|---|---|---|---|---|---|---|---|
| http://whmsebhyy.com 2004年04月20日 15:10 中國證券期貨 | |||||||||
|
文/羅培新 股權分置一直是影響中國上市公司行為和中國證券市場長遠發(fā)展的重要癥結之一。這一問題的解決,不僅事關中國證券市場能否健康發(fā)展,更直接關系到中國經濟改革能否走上一個良性運行的軌道。2004年2月2日,《國務院關于推進資本市場改革開放和穩(wěn)定發(fā)展的若干意見》強調指出,要積極穩(wěn)妥地解決股權分置問題:“穩(wěn)步解決目前上市公司股份中尚
目前,對非流通股流通問題的探索和討論多停留在技術層面,如出售方式、定價機制、轉讓時機、試點選擇等。然而,非流通股走向流通,本質上是利益的再一次重新分配,它絕不僅僅是一個技術設計和選擇的問題,更是一個規(guī)則重建以調整并保護市場各方預期的問題。在此過程中,為原來利益格局提供制度框架的相關法律法規(guī),必須進行必要的調整和刪改。否則,非流通股流通方案將面臨重重的法律障礙而難以順利推進。 基于這種認識,本文報告從法律的角度,對非流通股流通過程中涉及的法律法規(guī),進行一次全面系統(tǒng)的梳理。力求在分析法律障礙的基礎上,提供相應的法律解決方案。 非流通股流通方案關鍵語匯的法律辨析 2001年以來,社會各界對上市公司股權割裂問題進行了大量的討論,提出了各種旨在實現(xiàn)上市公司股權全流通的方案。大量的討論極大地豐富了解決全流通問題的思路,并達成了一些初步的共識。但在此過程中,也出現(xiàn)了一些對全流通的誤讀和誤解。因而,有必要首先對一些關鍵語匯,從法律的角度給出解釋,以奠定對非流通股流通問題進行法律評估的基礎。 1.“減持”與“全流通” 減持:即減少持有之意,指股份所有者減少其所持股份的行為。國有股減持是國資委行使國有資產出資人權利,減少其所持國有股份的行為。流通股股東拋售其所持股份,也屬減持行為,不過這里通常被“轉讓”所替代。“減持”強調過程,而“轉讓”則側重于股份產權的移轉結果。對某一類股份“減持”到零,就完成了對該類股份的“轉讓”。 全流通:指上市公司所有股份,包括原本未能在交易所掛牌交易的股份,都能夠在交易所掛牌交易。 全流通與減持的關系:減持不等于全流通,減持可以在交易所市場進行,也可以在場外進行。被減持的股份并不必然獲得流通權;然而,非流通股如果獲得了全流通權利,也就自動獲得了隨時在交易所市場減持的權利。 2.“同股同權”缺乏現(xiàn)實基礎 同股同權:指相同類型的股份,代表著內容相同的權利。根據(jù)《公司法》的一般原理,只有股份所代表的權利和義務具有同質性,才能盡可能地降低表決成本。這項《公司法》原理有著堅實的經濟學基礎,最直接地體現(xiàn)為“集體行動成本”——產權人在利益上存在異質性而產生的額外成本。舉例而言,在一個十八層樓高的大樓里,電梯給住在一層的人們帶來的方便和益處,遠不及給住在十八層的人們帶來的益處大。所以,因為樓層的不同,對于要不要多付加班工資以加快電梯維修進度,各方會持不同意見。這樣,各位業(yè)主對維修電梯這一事項的表決傾向,會隨著樓層的不同而呈現(xiàn)出較大的異質性。這種異質性,會拉長決策的過程,增加決策成本,甚至引起參與方的總體福利下降。由此對效率的損害,就表現(xiàn)為“集體行動的成本”(Henry Hansmann,2001)。 股份公司最初“一股一票”、“每股代表相同權利”的設計,正著意于避免利益異質而帶來過高的表決成本。我國《公司法》第129條規(guī)定,股份有限公司的資本劃分為等額的股份;第130條規(guī)定,股份的發(fā)行,必須同股同權,同股同利。同次發(fā)行的股票,每股的發(fā)行條件和價格應當相同。任何單位或者個人所認購的股份,每股應當支付相同價額。 從這些規(guī)定看,我國《公司法》是按照最標準的公司經濟結構來設計制度規(guī)則的,“同股同權”也因此在《公司法》框架內獲得了邏輯意義。然而,眾所周知的事實是,割裂的股權結構,使得非流通股與流通股盡管屬同次發(fā)行的股票,但發(fā)行價格和條件均不相同。“同股同權”在股票發(fā)行之初即缺乏現(xiàn)實基礎。 本文的參考文獻 [1] Frank H. Easterbrook, Daniel R. Fischel, The Economic Structure of Corporate Law,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2] Joel Seligman, A Brief History of Delaware's General Corporation Law of 1899, 1 Del. J. Corp. L. (1976). [3] Adolf A. Berle & Gardiner C. Means, The Modern Corporation and Private Property,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91). [4] Edward S. Adams, John H. Matheson, Corporations and Other Business Associations: Statues, Rules and Forms, 1997 Edition, by West Publishing Co.(1997) [5] Louis Loss, Joel Seligman, Fundamentals of Securities Regulation, 3rd editi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95). [6] Jeffrey Gordon, Ties That Bond: Dual Class Common Stock and the Problem of Shareholder Choice, 76 Calif. L. Rev. (1988) [7] Brudney & Chirelstein, Fair Shares in Corporate Mergers and Takeovers, 88 Harv. L. Rev. 297 (1974). [8] Brudney, Corporate Governance, Agency Costs, and the Rhetoric of Contract, 85 Colum. L. Rev. 1403 (1985). [9][美]羅伯特·C·克拉克,《公司法則》,胡平、林長遠、徐慶恒、陳亮翻譯,李靜冰譯校,工商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 [10][美]亨利·漢斯曼(Henry Hansmann):《企業(yè)所有權論》,于靜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11][美]《美國公司法選譯》(Delaware Corporation Law),姜鳳紋譯,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出版社1981年版。 [12]《特拉華州法典》第8章第144節(jié)(a)(2)。 [13][加拿大]布萊恩R柴芬斯:《公司法:理論、結構和運作》,林華偉、魏譯,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14]江平主編:《公司法教程》,法律出版社1987年版。 [15]江平主編:《法人制度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 [16]顧功耘主編:《公司法律評論》(2002年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11月版。 [17]何美歡著:《公眾公司及其股權證券》(上中下),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 [18]冀遠等:《國有股減持新轉折:先行試點,按每股凈資產定價》,《經濟觀察報》2003年11月24日。 [19]王中魁:《權證乃解決非流通股的一劑良藥》,2001年12月19日,《證券日報》。 3.“類別股東表決制度”缺乏法律規(guī)定 類別股,是指在公司的股權設置中,存在兩個以上不同種類、不同權利的股份。這些股份因認購時間和價格不同、認購者身份各異、交易場所有別,而在流通性、價格、權利及義務上有所區(qū)別。在國外,普通股和優(yōu)先股是兩種最基本的類別股。“普通股”可按表決力大小、“優(yōu)先股”可按性質的不同,進行更為細致的區(qū)分,圖示如下: 不同“類別股”的存在,是各國《公司法》為滿足投資者對于風險和盈利預期的不同偏好、順利完成籌資計劃而普遍采用的制度安排。同時,出于盡可能減少集體行動成本的考慮,許多國家的《公司法》規(guī)定,不同類別的股份分開表決,這就形成了“類別股東表決制度”。在這種制度下,一項涉及類別股東權益的議案,一般需本類別股東及其他類別股東分別審議,并獲得各自的多數(shù)同意才能通過。如根據(jù)香港公司條例的規(guī)定,只有獲得持該類別股面值總額3/4以上的絕對多數(shù)同意或該類股東分別經類別會議的特別程序,才能通過有關決議。 我國類別股東表決機制的法律規(guī)定存在極大的缺漏。有限的規(guī)定僅體現(xiàn)在1994年8月的《赴境外上市公司章程必備條款》中。該《必備條款》將境外上市公司中同時存在的A股、H股或B股稱為類別股,并對相關的會議規(guī)則做出了規(guī)定。但這些規(guī)定對于境內上市公司的流通股股東而言,無疑只能是望梅止渴。因為該《必備條款》將法定類別股限于普通股、外資股(包括H股和B股),而且只對境外上市公司生效。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證監(jiān)會于2002年7月發(fā)布了《關于上市公司增發(fā)新股有關條件的通知》。該通知第5條規(guī)定:“增發(fā)新股的股份數(shù)量超過公司股份總數(shù)20%的,其增發(fā)提案還須獲得出席股東大會的流通股股東所持表決權的半數(shù)以上通過。”然而,這一《通知》,只是證監(jiān)會專門就“增發(fā)”而頒布的行政規(guī)章,對其他事項均無法律效力。 所以,盡管我國的類別股事實上應當包括國有股、法人股、個人股,但在目前的法律和政策框架內,對于非流通股流通方案采取類別股東表決制度,尚無法律和政策依據(jù)。 4.“流通股股東認同率制度”存在缺陷 值得注意的是,有學者不贊同股東類別表決方案。“股東分類別表決是在股權統(tǒng)一前提下的一種表決制度,它是指在涉及到該類別股東利益時才由這部分股東予以表決,不涉及的就不表決,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還是一種消極的權力;而流通股股東認同率制度則不同,它是在股權分裂的情況下保護流通股股東利益的一種重要手段和途徑,即凡是涉及公司經營、分配、融資與再融資等重大事項都要經過流通股股東的表決和認同,這包括公司的重大資產重組與股權置換行為、公司分紅與再融資等會對不同類別股東的利益有重大影響的行為以及非流通股轉為流通股這樣能夠引起公司乃至整個股市的運行格局發(fā)生重大改變的重大行為等,這樣的表決和認同更多地體現(xiàn)著一種積極的權力。”(韓志國,2003)另有一些學者也對此表示附議。(華生,2003)。 事實上,從功能上說,類別股東表決制度與流通股股東認同率制度并沒有本質的區(qū)別。它們都是為了解決由于股權類型不統(tǒng)一而帶來的利益異質問題。但流通股股東認同率制度的局限性在于,如果公司的一切重大事項(而不僅是非流通股的流通問題),都必須獲得一定的流通股股東“認同率”,這無疑有悖于股份經濟的基本原理:出資、收益、風險,必須與表決權相配比。小股東如果獲得了與其收益權不相匹配的過高的表決權重,由于他們無法獲得表決權下的全部收益,將帶來過高的代理成本,甚至會引發(fā)敲詐或者其他道德風險(Frank H. Easterbrook, Daniel R. Fischel,1994)。 區(qū)分這兩項制度,對于設計切實可行的方案,既是技術前提,也是法律基礎。 5.“讓利或補償論”不具有法律約束力,易引起誤導 “讓利論”。一些為全流通政策提供建議的學者稱,非流通股流通政策的思路之一為“‘非流通股股東讓利’原則:為使雙方協(xié)商一致,非流通股股東可以少拿一部分,讓利于民”(夏斌,2003)。 就法律的角度分析,法律行為有“單方法律行為”、“雙方法律行為”和“多方法律行為”之分。“單方法律行為”是指只須由一方當事人做出意思表示即可生效的行為,如放棄繼續(xù)權、放棄股權等;而“雙方法律行為”和“多方法律行為”則是指須由雙方或多方意思表示一致才能生效的行為,如買賣、擔保等行為。 以國有股為主體的非流通股走向流通,并不是純粹的棄權(放棄流通權利或放棄因流通而帶來的利益)行為。相反,它不但會引起存量利益的大幅調整,而且必將在新增利益方面,引發(fā)非流通股與流通股之間的矛盾和沖突。因此,它絕不是非流通股股東“可不可以少拿一部分利益”的單方行為,而應是由作為各方當事人的非流通股股東和流通股股東,本著公平、合理、合法的原則,決定如何調整利益格局的多方行為。 如果不做這一解釋,那么從法律的角度分析,即使作為國有股東的國資委,可以“自愿”對流通股股東“讓利”,但大量的法人股股東,則完全可以拒絕“讓利”。 “補償流通股股東論”。與“讓利論”一脈相承的是“補償論”,即非流通股股東必須補償流通股股東,并且補償?shù)某潭仍酱笤接欣诜桨傅膱?zhí)行和市場的認同。然而,從法律的角度分析,“補償”是含混不清的曖昧字眼,常用于由于道義或者情感上的可非難性而為受害方提供的一種物質供給或者其他安排。但這種供給或者安排,更大的意義在于滿足補償方的道德或情感要求,并不屬強制性的法律義務。與此最為接近、但法律含義大相徑庭的語匯是“賠償”,指一方非法致使他人權益受損而做出金錢或其他方式的彌補。 另外,“補償論”必然會面臨的法律瓶頸是法律對所有財產的平等保護。由于股權割裂這一體制性原因,在目前的法律制度框架下,非流通股及其增值部分的財產取得方式,盡管不合情理,但仍屬合法取得,法律無法強制性地要求非流通股股東做出補償。 總之,“讓利論”與“補償論”,在一定程度上誤導了市場,削弱了流通股股東的博弈力量。 6.“一刀切”流通方案受產權規(guī)則約束,難以推行 有方案認為,應由國家有關部門統(tǒng)一決策,制定流通時間表,可以先搞試點,待方案成熟完善后推而廣之,最后達到全流通。 從法律的角度分析,非流通股是否流通,其決定權在于產權主體,而以什么價格流通,則是市場博弈的結果。任何股東,不論所有制形式如何,其行為均不能凌駕于《公司法》、證券法以及合同法規(guī)則之上。一種特定類型的股東,不能以假借行政命令的方式,脅迫其他類型的股東接受其決定。國資委作為國有產權代表,固然可以代行國有股的轉讓意愿(但不能單方面確定流通方案)。但目前非流通股已經不完全是國有股。國有股經過前一段時期較為集中的協(xié)議轉讓,相當部分已經由非公有經濟成分擁有,受讓者權益應當是原有合同的延續(xù),更改合同顯然缺乏法理基礎。因此,由國家制定非流通股流通時間表,或者采取一刀切的做法,只能是無強制執(zhí)行能力的建議而已。 任何非流通股流通方案,不論是否必須在政府的主導下進行,都必須注意法律規(guī)則的銜接與順暢,否則很難獲得通過。 非流通股流通方案必須確立的兩個法律前提 1.從“同股同權”到“異股異權” ——《公司法》規(guī)則的重新解釋 根據(jù)前述“同股同權”的法律解釋,可以合乎邏輯地推出,不同種類的股份,其權利內容應當不同,即“異股異權”。這樣,我國《公司法》第130條關于“同股同權”的規(guī)定,如果要適用于流通股與非流通股,則無論是在邏輯還是在法理方面,都難以順暢。 股權割裂是中國證券市場的“原罪”。在當時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為經受“姓社姓資”的意識形態(tài)質疑和攻擊,從而取得合法地位,我國股市一開始即背負著自我證明確實姓社、具有發(fā)展和壯大公有制功能的歷史重負,而這個制度性遺患造成的股權割裂,成了中國股市困境的總根源。因而,整個制度設計從一開始就不是考慮什么樣的設計是最合理的,而是考慮什么樣的設計是最有可能被接受的。在這個自我證明姓社的實踐過程中,股市成為國家分配資源、甚至是轉移財富的一種渠道。由于對割裂的股權結構視而不見,《公司法》中“同股同權”的制度設計,使得非流通股股東可以非常方便地分享來自個人股東的溢價收入,甚至許多非流通股股東“盤剝”流通股股東的“鐵血法則”,也竟“合法”地產生,“資本神話”因而也層出不窮。 以上分析表明,在股票發(fā)行之初,非流通股股東即已背棄了《公司法》第130條“同股同價”這一“同股同權”的前提,嗣后又利用割裂的股權結構,進行大幅度的財富轉移。如果目前在非流通股流通問題上,又要主張“同股同權”,顯然缺乏法律基礎。 總之,非流通股與流通股,屬于性質不同的股份,屬于“異股異權”,因而不受《公司法》“同股同權”規(guī)則的拘束。 2.從“讓利補償”到“支付流通對價” ——合同法規(guī)則的合理演繹 前述分析表明,“讓利與補償論”,一方面由于不屬嚴格的法律用詞而喪失了法律拘束力,另一方面,這種表述給非流通股股東以一種誤導,以為在流通過程中“讓利與否”、“補償與否”,全在于自己的決斷,而并非自己的義務。 鑒于此,筆者認為,有必要厘清表述,將它表述為“非流通股股東支付流通的對價”。 在法律上,對價(consideration)或稱約因,是指一方為取得合同權利,而向對方當事人所作的給付。缺乏對價,一項合同不可能成立或變更。 非流通股要取得流通的權利,必須支付“流通的對價”。其解析范式如下: 我國《公司法》、證券法以及其他法律法規(guī)中,從未出現(xiàn)國有股、法人股不能流通的字眼,相反,《公司法》第130條規(guī)定,股份必須同股同權同利;證券法第3條規(guī)定,證券發(fā)行必須公平公正公開。就此而言,我國國有股和法人股似乎并非不具備上市流通的權利。 然而,仔細研讀現(xiàn)行的《公司法》,國有股和法人股暫時不許上市流通,卻是明白不過的“潛規(guī)則”。 我國《公司法》第74條規(guī)定,股份有限公司的設立,可以采取發(fā)起設立或者募集設立的方式……募集設立,是指由發(fā)起人認購公司應發(fā)行股份的一部分,其余部分向社會公開募集而設立公司。《公司法》的這條規(guī)定,為不流通的發(fā)起人股——主要體現(xiàn)為國有股和法人股——與流通的社會公眾股共存于公司中,提供了制度平臺。 另外,《公司法》第152條規(guī)定,股份有限公司申請其股票上市必須符合下列條件:……向社會公開發(fā)行的股份達公司股份總數(shù)的百分之二十五以上……“向社會公開發(fā)行的股份”要滿足一定比例的要求,從表面上看,是為了滿足證券市場對公司股權流動性的要求,但更深的層面在于,它隱含著一個假定,即向社會公開發(fā)行之外的股份——發(fā)起人股,在未來的三年內不得上市流通。三年內一旦上市流通,就必須支付變更合同的對價。進而,《公司法》第147條規(guī)定,發(fā)起人持有的本公司股份,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三年內不得轉讓,更加強化了這種理解。 所以,所有的流通股股東都認為,發(fā)起人在發(fā)行股票時,對非流通股有“暫不流通”的承諾,這種承諾已經構成了投資者的心理預期,對市場的供求關系進而對流通股的股價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因而,非流通股“暫不流通”,可以被認為是一個具有約束力的默認的合同條款。非流通股股東要改變合同,獲得流通的權利,就必須與合同的另一方——流通股股東協(xié)商一致。因為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77條規(guī)定,只有當事人協(xié)商一致,才可以變更合同。在各方達成一致之前,非流通股不具有流通權。顯然,非流通股股東必須支付相應的對價,合同各方才可能“協(xié)商一致”,進而變更合同,實現(xiàn)非流通股的流通。 這是無法逃避的法律邏輯,近年來市場的反應,多次回應了這一點。 明確概念并確立法律前提后,本文接下來對流通方案面臨的法律障礙及其應對策略作一個總體的評估。 非流通股流通方案的法律困境及其克服 1.清理國有資產法規(guī)和政策,刪除過于僵化的規(guī)定 其一,1994年國家國有資產管理局、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聯(lián)合發(fā)布的《股份有限公司國有股權管理暫行辦法》第27條規(guī)定,國有股持股單位不得以任何理由、任何方式同意單方面縮小國有股權比例。這兩個“不得以任何”的規(guī)定,是直接規(guī)范國有股權管理與處置辦法的相關規(guī)定中最直接、最為剛性的一條。因為國有股無論是通過配售、縮股、回購、贈股等方式實現(xiàn)流通,都將構成國有股權比例的縮小,因而受制于這一規(guī)定。 以可能的回購方案——上市公司按照凈資產的價格向非流通股股東回購并注銷非流通股——為例。雖然我國《公司法》規(guī)定,公司為減少注冊資本或與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其他公司合并時,可以由股東大會決定回購并注銷股份,而且《暫行辦法》的效力要低于《公司法》,但國有持股單位作為最大的股東,如果要承擔過大的政治風險,將不會在股東大會中贊成回購方案,以至于公司無法通過股東大會而完成國有股回購的法律程序。 其二,2003年12月15日,國資委發(fā)布了《關于規(guī)范國有企業(yè)改制工作的意見》。該《意見》在“定價管理”一項中規(guī)定,上市公司國有股轉讓價格在不低于每股凈資產的基礎上,參考上市公司盈利能力和市場表現(xiàn)合理定價。據(jù)此規(guī)定,國有股上市流通的底價應為每股的凈資產價格。這條規(guī)定值得商榷之處在于,價格的形成本是市場博弈的結果,購買方對資產未來的增值預期,直接決定著價格的高低。而且,從歷史上看,國有股每股凈資產已經包含了從流通股“轉走”的部分價值。如今先行確定“凈資產底價”,然后要求流通股股東以此為基礎,與非流通股股東展開“博弈”,其合法性和市場效果都存在很大的懸疑。 這些僵化的規(guī)定,都有必要進行相應的調整。 2.突破“發(fā)起人持有股份三年不得轉讓”的 《公司法》規(guī)定 我國《公司法》第147條規(guī)定,發(fā)起人持有的本公司股份,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三年內不得轉讓。對于我國相當部分的上市公司而言,如果公司成立未滿三年,大量的國有股權和社會法人股,作為當然的發(fā)起人股份,都將面臨這一法律困境。事實上,國務院在2001年6月12日發(fā)布的《減持國有股籌集社會保障資金管理暫行辦法》中,也似乎是察覺到了《公司法》這條規(guī)定給國有股減持帶來的許多尷尬,于是在該辦法第5條中規(guī)定,股份有限公司設立未滿3年的,擬出售的國有股通過劃撥方式轉由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持有,并由其委托該公司在公開募股時一次或分次出售。”這里以“劃撥”和“委托”兩個詞代替了“轉讓”,但其終極目的仍舊是“出售”。這樣,無論在法律上作何種解釋,國有股任何形式的減持,都是產權主體的變更,都是法律意義上的“轉讓”。所以,其中的法律障礙仍無法回避。 值得注意的是,2001年7月24日,作為試點并開始減持之旅的四只新股,都沒有能夠符合“成立三年的要求”。烽火通信成立于1999年12月25日,其國有股應該在2002年12月25日之后方可轉讓,同理,成立于1998年10月的北生藥業(yè)、1999年9月30日的江汽股份、1999年9月3日的華紡股份也都不具有在當時轉讓國有股的資格。對此事件的解釋,財政部與證監(jiān)會的有關部門曾表示,四家方案的擬訂,完全以國務院2001年6月12日頒布的《暫行辦法》為準,并不違反《公司法》。而且,《公司法》第148條規(guī)定,“國家授權投資的機構可以依法轉讓其持有的股份,也可以購買其他股東持有的股份。轉讓或者購買股份的審批權限、管理辦法,由法律、行政法規(guī)另行規(guī)定。”似乎這可以成為《暫行辦法》規(guī)定“委托出售國有股”的法理依據(jù)。然而,必須注意的是,《公司法》第148條所謂“由法律、行政法規(guī)另行規(guī)定”的對象,只是有關轉讓或者購買股份的“審批權限和管理辦法”,而并不涉及突破“三年內不得轉讓”的限制。否則,從最基本的立法技術和語言邏輯出發(fā),如果《公司法》第147條“三年不得轉讓”的規(guī)定有例外適用的情形,就應在該條中做出除外規(guī)定。而且,從當時的立法本意出發(fā),“發(fā)起人三年不得轉讓所持股份”,既是維持公司經營穩(wěn)定的需要,也是其分享向公眾高溢價發(fā)行股票所帶來收益而必須承擔的責任。其隱含的假定是,發(fā)起人在三年內必須“留守”公司,既不能協(xié)議轉讓,更不能“上市流通”,這是一項有約束力的承諾,構成了投資者明確的心理預期。 未滿三年的發(fā)起人股份不得轉讓,非流通股流通方案的這一首要瓶頸,必須予以突破。刪除這一規(guī)定的法理解釋仍然是“支付流通對價”,從而改變這一“合同約定”。 3.創(chuàng)造法律“選擇權”,尊重產權主體的流通意愿 任何一種流通方案,都無法回避一個根本性的問題,即非流通股股東的意愿問題。1994年《股份有限公司國有股權管理暫行辦法》第2條規(guī)定,國家股和國有法人股統(tǒng)稱為國有股權,其產權代表是政府。在政府主導的減持模式下,不管采取哪種模式,在法律上都可以認為已經獲得了產權人的同意。而社會法人股則不同,政府無權替代社會法人股股東做出決定。因而,征得后者同意,是方案推行所不可回避的法律邏輯。 以可能的配售方案——非流通股以凈資產價向流通股股東定向配售——為例。如果社會法人股股東不同意,能否強制推行?在目前的法律框架內,幾無可能。因為《公司法》第103條只是規(guī)定,股東大會有權對公司增減注冊資本、公司合并、解散等事項做出決議,但對于非流通股以凈資產向流通股定向配售,股東大會卻無此權限。所以,即使國有股控制著股東大會,也無權做出這一決議。 但有沒有變通方案?在法理上,可行的變通方案是提供法律選擇權,因為存在選擇權的制度設計,可以避免私權遭受國家強力壓迫的詬病,這在法理上完全可行。近年來,備受爭議的鄭百文重組方案最后獲得通過,為非流通股的流通方案樹立了一個可資借鑒的樣板。 2000年12月31日,鄭百文召開股東大會,確定了一項特殊的重組框架,其部分內容為:三聯(lián)集團公司豁免鄭百文的債務,但鄭百文的全體股東,包括非流通股和流通股股東需將所持公司股份的約50%過戶給三聯(lián)集團公司;不同意的股東將由公司按公平價格回購,公平價格由下一次股東大會以《獨立財務顧問報告》確定的價格為準。這一方案在法律上無疑具有示范意義。 流通方案也可采取類似的設計,來實現(xiàn)以國有股“帶動”法人股流通的目的。在進行方案設計時,可通過公司股東大會以特別決議的方式,修改公司章程,賦予法人股股東選擇權:其一,法人股以凈資產向流通股股東配售股份(或贈股、縮股等其他方式),從而獲得流通權;其二,如果法人股不接受,則由公司以凈資產的價格回購其股份,再由公司向流通股股東配售,從而達到間接流通的目的。通過法律機制創(chuàng)造“選擇權”,既殊途同歸,又滿足了尊重私權的法律要求。 4.詮釋“同股同權”,確立類別股東表決機制 盡管在我國目前的法律和政策框架內,將類別股東表決制度適用于非流通股流通方案尚無明確的法律和政策依據(jù)。但從《公司法》基本原理出發(fā),在“異股異權”情況下,對流通方案采取類別股東表決機制,卻仍然存在厚實的法理基礎。 當然,為避免爭議,從最低的立法成本出發(fā),可以考慮的方案有兩條: 其一,由有關監(jiān)管部門(證監(jiān)會或證監(jiān)會與國資委聯(lián)合)通過行政規(guī)章的形式,確立類別股東表決制度,并明確對流通方案適用。 其二,由各上市公司通過非流通股股東與流通股股東之間的博弈,通過股東大會修改公司章程,寫入類別股東表決機制,并明確適用于流通方案的表決。 這兩項方案的一個共同前提是尊重事實,尊重“異股異權”的邏輯,除承認A股、H股、B股的劃分外,還應將國有股、法人股、個人股確定為類別股。對流通方案進行表決時,必須舉行類別股東會議,并分別取得非流通股股東和流通股股東的多數(shù)通過。 非流通股與流通股長期割裂這一中國特有的資本市場痼疾,使得對“類別股東表決機制”的市場需求,在股市長期走低、流通股股東信心嚴重受挫的情況下,顯得尤為迫切。而在《公司法》修改短期內無法完成的情況下,這兩種方案,可以比較迅速地彌補當前立法的缺漏。當然,在政府主導下的非流通股流通,比較可行的是第一種方案。 5.構建流通權證制度,促進“流通對價權證化” 前文的分析表明,非流通股要走向流通,必須向流通股股東支付“流通對價”,而不是“讓利”或“補償”。而價格的確定,隨著公司上市時間長短、業(yè)績及市場前景的不同呈現(xiàn)出明顯的差異。因而,它本質上是市場博弈、個案推進的過程,事實上無法由政府提供整齊劃一的方案。這樣,非流通股以什么形式支付“流通的對價”,就成為一個焦點問題。 在目前的制度框架下,可行的一種方案為,按持股比例,并綜合考慮其他因素,向流通股股東無償發(fā)放非流通股流通權證。這樣,非流通股股東沒有任何損失,因為它本來就沒有流通的權利,相反,由于流通權證的存在,它有了額外的選擇,即通過獲得流通權證得到二級市場流通的權利。至于非流通股股東是否愿意選擇股權流通,則由它自己在綜合衡量控制權的得失、取得流通權的成本、流通后收益等因素的基礎上做出,這是市場行為,政府無須進行干預。 流通權證可以被簡化地定義為:1份流通權證+1股非流通股(國有股或法人股)= 1股流通股。在具體操作上,各公司可以設定某一天為股權登記日,向所有流通股股東配發(fā)流通權證。每一股流通股獲配的流通權證數(shù)量,為該上市公司非流通股數(shù)量除以流通股數(shù)量之商。舉例而言,用友軟件總股本為1億股,流通股為2500萬股,即2500萬股流通股的持有人擁有用友軟件全部1億股股份的流通權,除去自身2500萬股的流通需要,還有可供轉讓的7500萬股的流通權,因此,每一股流通股可以獲配3份流通權證。這樣,將會有7500萬份流通權證產生,也有7500萬股非流通股等待進入流通市場,二者正好匹配。 非流通股股東可以在市場上購買流通權證,流通股股東也可以向非流通股股東購買非流通股,只要流通權證和非流通股相結合即轉化為新的流通股,而流通權證和非流通股同時消滅。滬深交易所組織流通權證的交易以及流通權證和非流通股結合轉股等事宜。流通權證可以是無形的,由中央登記結算公司統(tǒng)一托管,中央登記結算公司為每一個股東自動產生一個流通權證戶頭,以方案實施之日為準,向流通股股東配發(fā)前述比例的該股東投資的上市公司的流通權證。流通權證的交易采用和目前股票交易同樣的電子自動撮合交易系統(tǒng)。為了促進非流通股盡快和流通權證相結合轉化為單一的流通股,設定一個5年或稍長時間的一個轉股期限,到期上市公司有權使用配股資金按照凈資產折價強制回購,從而消滅非流通股。非流通股消滅時,流通權證也同時消滅,不再有任何價值。 6.理清權源,明確全國人大 對國有股流通方案的決定權 確定國有股流通方案,通常的理解是由作為國有股權代表的國資委與流通股股東共同進行。因為國資委的職責之一是,根據(jù)國務院授權,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等法律和行政法規(guī)履行出資人職責,起草國有資產管理的法律、行政法規(guī),制定有關規(guī)章制度。但仔細分析我國目前的法律框架,卻不能得出這樣的結論。 國資委對國有股的權力源于國務院的授權。而國務院是否有權制定行政法規(guī),決定減持國有股以補充社保基金?根據(jù)中國《立法法》的規(guī)定,國務院可以根據(jù)憲法和法律,制定行政法規(guī),就下列事項做出規(guī)定:“(一)為執(zhí)行法律的規(guī)定需要制定行政法規(guī)的事項;(二)《憲法》第八十九條規(guī)定的國務院行政管理職權的事項。”另外,對應當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制定法律的事項,國務院也可以根據(jù)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的授權決定先暫行制定行政法規(guī),待經過實踐檢驗,制定法律的條件成熟時,再由國務院及時提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制定法律。 所以,國務院如果有權制定行政法規(guī),決定國有股流通方案,則必屬以下三種情形之一:其一,為執(zhí)行已經存在的法律規(guī)定的需要而制定行政法規(guī),以與之配套;其二,國務院得到了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的授權;其三,國有股流通,屬于國務院行政管理職權事項之一。 其中,由于國有股流通尚未有法律規(guī)定,而且直到目前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也未授權國務院決定國有股流通方案,所以第一和第二種情形都不存在。唯一的可能是第三種情形,即國有股流通,本屬國務院行政管理職權事項之一。《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89條列出了國務院有權行使的十八項職權,其中最有可能的是第六項“領導和管理經濟工作和城鄉(xiāng)建設”。 但從法理上分析,國有股的價值源于公民勞動的歷史凝聚,屬于全民共有的財產;而減持國有股以籌集社保基金,直接受益的是作為社保基金受益人的全體公民,但同時又影響到目前數(shù)千萬股民的私人財產權利和切身經濟利益。因而,對全民財產的處分及其對私人財產權的影響等問題,從法理上看已經超越了一般的政府行政管理權的層次,而理應訴諸作為國家最高權力機關的全國人大。因此,在沒有明確的法律根據(jù)或得到人大的明確授權之前,就算權宜上可以對《憲法》規(guī)定的行政管理職權進行寬泛解釋,國務院就國有股減持問題制定行政法規(guī)的法律依據(jù)恐怕也有欠圓滿。正因為如此,國務院2001年6月出臺的《減持國有股籌集社會保障資金管理暫行辦法》,只是泛泛地稱“為完善社會保障體制,開拓社會保障資金新的籌資渠道,支持國有企業(yè)的改革和發(fā)展,制定本辦法”,其法理基礎并不牢固。 由于國有股的流通方案,關系到全民(包括但不限于國有股與流通股之間)財產的重新分配,國務院在得到最高權力機關的授權之前,無權單獨決定,自然也就無法對國資委做出授權。明確全國人大對國有股流通方案的決定權,而不是由陷于出資人和監(jiān)管者角色沖突中的國資委行使這一權力,更有利于問題的全面和穩(wěn)妥解決。 |
| 首頁 ● 新聞 ● 體育 ● 娛樂 ● 游戲 ● 郵箱 ● 搜索 ● 短信 ● 聊天 ● 點卡 ● 天氣 ● 答疑 ● 交友 ● 導航 |
| 新浪首頁 > 財經縱橫 > 焦點透視 > 個股全流通試點 > 正文 |
|
| ||||||
|
新浪網財經縱橫網友意見留言板 電話:010-82628888-5173 歡迎批評指正 新浪簡介 | About Sina | 廣告服務 | 聯(lián)系我們 | 招聘信息 | 網站律師 | SINA English | 會員注冊 | 產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4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