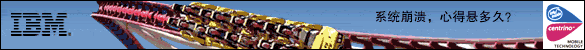| 證券投資基金法背后的故事:三審四辯基金法 | |||||||||
|---|---|---|---|---|---|---|---|---|---|
| http://whmsebhyy.com 2003年11月06日 07:48 北京娛樂信報(bào) | |||||||||
|
失落總是與成功相伴而行。 懷胎數(shù)載的《證券投資基金法》終于塵埃落定。盡管歷經(jīng)增刪數(shù)十次、批閱四春秋的艱難,但在王連洲的心中還是留下了一連串的遺憾。“一項(xiàng)法律的最終出臺是各部門相互妥協(xié)、利益權(quán)衡的結(jié)果。我們的原則就是讓法律盡早出臺。”從起草、審議到表決通過,爭議貫徹始終,尤其是四個(gè)關(guān)鍵問題至今難成共識。而每一次博弈的背后,都是一個(gè)個(gè)說不完
戲劇收場 基金立法種瓜得豆 證監(jiān)會不想多管,原計(jì)委不愿放權(quán)。“如果法律中說不清私募基金由誰監(jiān)管審批,干脆就別提。”本來對立的意見就這樣戲劇性地一致起來。于是有關(guān)私募基金的一章在立法草案正式提交人大審議前被刪掉了。制定一部全面的《投資基金法》在立案之初是絕大多數(shù)參與者的初衷,最終卻只出臺《證券投資基金法》。《證券投資基金法》起草工作組原組長王連洲用“種瓜得豆”來形容這個(gè)多方博弈的結(jié)局,多少透著些許的無奈。 就是在2002年2月起草組向全國人大財(cái)經(jīng)委提交《投資基金法草案稿》前的最后那次定稿會上,原計(jì)委的派員提出:“‘向特定對象募集的基金(私募基金)’,規(guī)定的內(nèi)容不具體,不充分,對產(chǎn)業(yè)投資基金或者風(fēng)險(xiǎn)創(chuàng)業(yè)投資基金發(fā)起成立的資質(zhì)條件、投資運(yùn)作以及審批監(jiān)管的特殊要求和主體的明確等沒有充分體現(xiàn)出來,希望加以完善和充實(shí),否則干脆就別提產(chǎn)業(yè)、創(chuàng)業(yè)投資基金的問題,只規(guī)定證券投資基金就是了。”與會專家們心里都明白,計(jì)委最關(guān)心的是,由誰審批監(jiān)管要明確,因?yàn)檫@個(gè)權(quán)力本該屬于他們的。 同時(shí)“證監(jiān)會認(rèn)為私募基金究竟歸誰管理還不甚明確,不希望將這一條內(nèi)容放在這個(gè)法中,主張只規(guī)范證券投資基金就行了。”王連洲說,其實(shí)證監(jiān)會是不想背上與證券無關(guān)的實(shí)業(yè)投資基金的包袱。 如此看來,不提及私募基金的內(nèi)容還可以為以后產(chǎn)業(yè)投資基金和風(fēng)險(xiǎn)創(chuàng)業(yè)投資基金單獨(dú)立法留下空間。在不能如愿的情況下,兩家的心理底線是一致的。“與會的領(lǐng)導(dǎo)小組成員周道炯在與厲以寧耳語后,由厲以寧教授決斷宣布,將體現(xiàn)統(tǒng)一綜合立法的《投資基金法》改為單純的《證券投資基金法》。”對這一重大的改動,包括王連洲在內(nèi)的與會者都感到有些突然,但沒有一人持有異議,因?yàn)檫@樣一來所有的矛盾都回避開了。 有意思的是,當(dāng)初香港資深大律師梁定邦提出按照“公開”募集資金和向“特定”對象協(xié)議募集資金分別進(jìn)行規(guī)定,就是為了化解綜合立法與單純立法爭論的僵局。然而,這種試圖繞開矛盾的嘗試最終沒能成功。 方向之爭 綜合立法終于讓步 王連洲回憶起在起草階段相當(dāng)長的時(shí)間里,“制定一部既能夠涵蓋規(guī)范證券投資基金,又能涵蓋規(guī)范產(chǎn)業(yè)投資基金和風(fēng)險(xiǎn)投資基金統(tǒng)一的《投資基金法》占據(jù)著主流思路,并得到了時(shí)任財(cái)經(jīng)委多數(shù)領(lǐng)導(dǎo)的贊同。”時(shí)任立法起草工作小組組長的王連洲也是綜合立法的擁躉,“因?yàn)樵缭?997年當(dāng)時(shí)的國務(wù)院證券委就頒布實(shí)施了《證券投資基金管理暫行辦法》,對證券投資基金起碼有了規(guī)范運(yùn)作的行政法規(guī)和規(guī)章。如果不統(tǒng)一立法,而讓各個(gè)主管部門分別起草制定單行法或者行政法規(guī),難以避免各部門越權(quán)立法、重復(fù)立法、加大立法成本甚至產(chǎn)生各項(xiàng)法律之間相互沖突的現(xiàn)象。”并且,當(dāng)時(shí)發(fā)展產(chǎn)業(yè)投資基金和風(fēng)險(xiǎn)投資基金的呼聲很高,面對法律上的空白,有關(guān)主管部門對提高產(chǎn)業(yè)投資基金和風(fēng)險(xiǎn)投資基金的法律保護(hù)有迫切的要求。 然而,從始至終有一種與綜合立法截然相反的認(rèn)識和意見,主張只制定《證券投資基金法》。起草領(lǐng)導(dǎo)小組成員、時(shí)任人大法工委副主任委員的董輔礽教授就是這一觀點(diǎn)的突出代表,他一開始就非常明確地表明自己的觀點(diǎn)——“證券投資基金與產(chǎn)業(yè)、風(fēng)險(xiǎn)創(chuàng)業(yè)投資基金除了維護(hù)投資人的利益是共同的,其他沒有什么共同點(diǎn)。” 董輔礽語出驚人,這句話令所有的委員至今記憶猶新。他認(rèn)為不同類的基金在設(shè)立的目的、功能定位、募集方式、投資對象、運(yùn)作規(guī)則以及政府干預(yù)的程度等等,都存在著很大的不同,很難在一部法律中做出統(tǒng)一的規(guī)范。在董輔礽看來,產(chǎn)業(yè)、風(fēng)險(xiǎn)創(chuàng)業(yè)等實(shí)業(yè)投資基金還沒有充分發(fā)展,尚不宜先立法。 董輔礽是最終的勝利者,但當(dāng)時(shí)他卻是孤獨(dú)的。在已經(jīng)占據(jù)主導(dǎo)地位的主流思路和意識面前,哪怕是富有真知灼見的相反意見和建議,也往往是“說了也白說”,難以勝出。更何況扮演捉刀人角色的起草小組大多數(shù)成員也都是綜合立法的虔心擁護(hù)者。 綜合立法的工作并沒有因?yàn)槎o礽的反對而停下腳步。工作小組于2000年1月24日,正式將包括“創(chuàng)業(yè)投資基金的特別規(guī)定”專門一章的“投資基金法草案”第一稿送交起草領(lǐng)導(dǎo)小組。甚至因?yàn)榇烁鍥]有具體突出“產(chǎn)業(yè)投資基金”的內(nèi)容,還招致有關(guān)部門與會人員的反對起草。于是工作小組又于2000年6月21日,向領(lǐng)導(dǎo)小組正式提交第二稿,充實(shí)了相關(guān)內(nèi)容:將證券投資基金、產(chǎn)業(yè)投資基金和創(chuàng)業(yè)投資基金分列為三章,分別進(jìn)行規(guī)定。 但是,在寧波召開的投資基金法起草領(lǐng)導(dǎo)小組工作會議上,這份尊重了多數(shù)派意見的草案卻招致了更多的批評。正如董輔礽預(yù)見到的一樣,按照基金投資方向的不同,分別對證券投資基金、產(chǎn)業(yè)投資基金和風(fēng)險(xiǎn)投資基金分章節(jié)作規(guī)定,的確遇到了內(nèi)容規(guī)定交叉和重復(fù)以及顧此失彼的其他立法技術(shù)問題。 與會的梁定邦正是在這種復(fù)雜的情況下提出了雙方都能接受的第三條路線——既然從出口(按照基金不同投資方向)難以走通,是否改變一下立法技術(shù)從入口(按基金募集方式)一網(wǎng)打盡,按照“公開”募集資金和向“特定”對象協(xié)議募集資金分別進(jìn)行規(guī)定。反正資金從募集方式上來說,不是公募即是私募。 于是2000年9月25日形成的基金法草稿第三稿中,就將“向特定對象募集資金的基金”專列一章。 故事又回到了最初,“董輔礽教授想種豆沒得到豆,沒想到費(fèi)了一年的工夫種了瓜,卻最終得到了豆。”王連洲難以掩飾心中的無奈。而同樣參與起草的北京大學(xué)的曹鳳岐教授現(xiàn)在看當(dāng)時(shí)的選擇“實(shí)屬明智之舉”,“若按原來的綜合立法思路,不僅操作上會困難重重,相關(guān)爭議也會較多,《證券投資基金法》就不會那么順利的出臺。” 學(xué)術(shù)之爭 基金定義難覓其蹤 翻開剛剛通過的《證券投資基金法》,并沒有對證券投資基金的定義,僅僅是對證券投資基金的主要法律特征予以描述。對一個(gè)需要規(guī)范的事物,卻沒有在總則中對其概念進(jìn)行界定,沒有確定法律的調(diào)整范圍,沒有定義的《證券投資基金法》可是開了個(gè)先例。 “不管采取哪個(gè)概念,都會有相反的意見。既然誰也說服不了誰,為避免不必要的爭論,推動《證券投資基金法》的及早順利出臺,干脆取消了基金的定義。”如果說綜合立法與單純立法之爭是權(quán)力的博弈,王連洲認(rèn)為對基金定義的爭論則完全是學(xué)術(shù)思想的碰撞。 今年6月,《證券投資基金法(草案)》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進(jìn)行第二次審議時(shí),一項(xiàng)最令人疑惑的修改就是,作為一部規(guī)范證券投資基金活動的根本性大法,竟然取消了對“什么是證券投資基金”的明確說法。 曾為起草工作小組成員的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法學(xué)所的劉俊海博士對其中原因毫不避諱:“在二審稿中取消了關(guān)于證券投資基金的定義,絕非偶然。這實(shí)際上是回避了長期以來圍繞投資基金立法定義的爭論。因?yàn)閺?999年啟動投資基金立法程序開始,社會各界對于什么是投資基金,怎樣給它下定義,就一直眾說紛紜。” 草案中基金定義幾易其稿的歷史證實(shí)了劉俊海的說法。 2000年1月24日的基金法草案稿規(guī)定:投資基金是指多個(gè)投資人共同出資,根據(jù)特定投資目的依法設(shè)立,由專門的管理人管理,托管人托管,按照投資組合原理運(yùn)作,投資人共享收益、共擔(dān)風(fēng)險(xiǎn)的一種“投資方式”。 2000年8月由全國人大財(cái)經(jīng)委員會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交的基金法草案一審稿,將證券投資基金定義為“是指通過發(fā)售基金份額募集資金形成獨(dú)立的基金資財(cái)產(chǎn),由基金管理人管理、托管人托管,以資產(chǎn)組合方式進(jìn)行證券投資,基金份額持有人按其所持份額享受收益和承擔(dān)風(fēng)險(xiǎn)的投資組織。” 一個(gè)多月后這個(gè)定義又改為,由專業(yè)機(jī)構(gòu)根據(jù)特定投資目的,向公眾或者特定對象募集資金,實(shí)行分工和專業(yè)化管理的“組合資產(chǎn)”。 曾在美國做訪問學(xué)者的劉俊海博士給基金的定義也帶有“美式”學(xué)術(shù)背景。他的定義可以歸結(jié)為“資本集合體”,與美國人把“投資基金”稱為共同基金如出一轍。但是“投資基金”在英國稱單位信托,在日本稱證券投資信托,在我國臺灣也稱證券投資信托,劉俊海的定義自然遭到了其他學(xué)術(shù)背景專家的反對。 “當(dāng)時(shí)有‘投資組織’、‘投資方式’、‘投資計(jì)劃’、‘基金公司或者信托’還有‘金融工具或產(chǎn)品’、‘投融資制度’,甚至更多種定義。”參與起草的王連洲對記者說。 “坦率地講,制定一個(gè)讓各方都能接受的精確定義,是一件困難的事情。因此,立法者被迫采取了相對靈活、變通的方式——回避,僅僅是對證券投資基金的主要法律特征加以描述。從立法技術(shù)上講,這樣做,有利于避免不必要的爭論,推動《證券投資基金法》盡早出臺。”劉俊海對立法機(jī)構(gòu)的最終決定表示理解。 在我國的立法實(shí)踐中,類似于《證券投資基金法(草案)》二審稿這種回避法律主體定義的情況,亦有先例可循。比如在《消費(fèi)者權(quán)益保護(hù)法》的制定過程中,有關(guān)方面對如何定義消費(fèi)者,也一直爭論不休,最終采取的方式便是在法律中不再明確消費(fèi)者的定義,而只是對消費(fèi)者的特征加以規(guī)定,“消費(fèi)者為生活消費(fèi)需要購買、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務(wù),其權(quán)益受本法保護(hù)。” “這樣做的結(jié)果是什么呢?我們都知道有一個(gè)‘打假’英雄叫王海。‘王海現(xiàn)象’產(chǎn)生以后,大家就在爭論,王海是不是消費(fèi)者?王海的行為是否屬于《消法》保護(hù)的范圍?爭論來爭論去,很難有一個(gè)共識。什么原因?法律本身對消費(fèi)者缺乏一個(gè)明確的定義。”盡管為了法律的盡早出臺達(dá)成了妥協(xié),劉俊海仍然擔(dān)心取消證券投資基金定義可能會產(chǎn)生兩方面的問題:第一,由于法律規(guī)定不明確,可能會讓許多類似于證券投資基金的新的投資產(chǎn)品輕易地規(guī)避法律管轄;第二,作為規(guī)定證券投資基金的基礎(chǔ)性法律,對證券投資基金未能有所定義,可能導(dǎo)致證券投資基金的法律主體地位模糊不清,從而不利于證券投資基金業(yè)的發(fā)展。 利益之爭 基金意志反復(fù)博弈 在基金法起草審議過程中的幾次重大爭論中,真正分出個(gè)勝負(fù)的不多,對基金持有人大會表決事項(xiàng)參會人員比例的修改可以算作一次。 “草案在提交人大二審時(shí),將基金持有人大會應(yīng)當(dāng)至少有代表基金份額50%以上的持有人參加的比例降為30%。持有人大會是基金份額持有人實(shí)現(xiàn)權(quán)益的重要途徑,降低門檻增加了基金持有人的話語權(quán),方便他們體現(xiàn)意志。”現(xiàn)在提起來王連洲還是一臉的興奮。這項(xiàng)修改在當(dāng)時(shí)獲得了高度的贊揚(yáng),被媒體稱為“立法的亮點(diǎn)”。 但這個(gè)亮點(diǎn)只亮了四個(gè)月,在其后提交人大的三審稿中,這條規(guī)定中30%的比例再度被恢復(fù)為50%。“人大在二審后就這一條修改進(jìn)行了調(diào)研,有不少專家認(rèn)為30%的比例過低,大會作出的決定難以體現(xiàn)多數(shù)持有人的意愿。提高比例是加大基金份額持有人權(quán)益保護(hù)力度。”對于為何在表決事項(xiàng)參會人比例上變來變?nèi)ィ龑徃骞己髱缀跛械拿襟w都是這樣解釋的。 然而王連洲對記者說:“這一點(diǎn)其實(shí)有些爭議。降低表決事項(xiàng)參會人比例實(shí)際在另一方面加大了基金管理人的壓力,特別是小基金公司對此比較擔(dān)心。本來發(fā)行規(guī)模就小,比例再降低點(diǎn),用不了多少持有人參加就可以進(jìn)行表決,萬一表決結(jié)果把封閉式基金轉(zhuǎn)成開放式基金了,他們怎么應(yīng)付?人大在調(diào)研過程中,很大程度上是聽取了這些小基金公司的意見。”王連洲認(rèn)為在這一回合的較量中,其實(shí)是基金持有人落敗了。 小基金公司出于保護(hù)自身的目的,建議恢復(fù)表決事項(xiàng)參會人比例50%的規(guī)定是很正常的,讓人疑惑的是,人大的天平為何最終偏向了人數(shù)上遠(yuǎn)遠(yuǎn)小于基金持有人的小基金公司一邊,王連洲一言以蔽之:“會哭的孩子有奶吃,基金公司雖小,但總比普通投資者更有機(jī)會向立法機(jī)構(gòu)進(jìn)言。”并且,大基金公司雖無此上述擔(dān)心,在根本利益上卻是同前者一致的,至少也不會希望比例為30%的規(guī)定寫在最終的法律中。 風(fēng)險(xiǎn)之爭 基金融資無果而終 基金公司一心希望的允許開放式基金短期融資的規(guī)定,邁過了二審那一關(guān),卻最終絆在了三審的坎上。《證券投資基金法》出臺過程中多次重大爭論都是無果而終,這項(xiàng)修改又是一個(gè)很好的例證。 草案一審稿中就有“根據(jù)開放式基金運(yùn)營的需要,基金管理人可以按照央行規(guī)定的條件為基金向商業(yè)銀行申請短期融資”的規(guī)定,但是對于這一規(guī)定一直存在爭議。 全國人大代表秦池江就是持反對意見的代表人物。他認(rèn)為基金公司不具有貸款主體資格,銀行融資風(fēng)險(xiǎn)形成之后,責(zé)任難以落實(shí),銀行難以進(jìn)行債權(quán)追索,最終會將風(fēng)險(xiǎn)轉(zhuǎn)嫁于銀行。著名經(jīng)濟(jì)學(xué)家劉紀(jì)鵬亦與前者有同樣的擔(dān)心,贖回是市場傳遞的真實(shí)信號,如果用融資掩蓋了這一市場信號,會使對風(fēng)險(xiǎn)的暴露滯后。因此他們在二審時(shí)對此都投了反對票。 “管理人代表基金向商業(yè)銀行申請短期融資,風(fēng)險(xiǎn)要比銀行的一般企業(yè)貸款小,且可靠性更高。”持贊成意見的人大財(cái)經(jīng)委副主任委員周正慶對前兩者提出的理由不以為然,“當(dāng)基金向商業(yè)銀行貸款時(shí),必須有足夠的股票和債券作抵押,這種抵押流動性比較好,所以它申請短期融資對商業(yè)銀行來說沒有太大風(fēng)險(xiǎn)。何況,最終的貸與不貸,關(guān)鍵還是在商業(yè)銀行。”在周正慶看來,開放式基金往往在經(jīng)營比較好、回報(bào)率比較高的情況下贖回比較多。在這種情況下進(jìn)行短期融資,不僅非常必要,而且也符合世界通行的做法,否則不利于開放式基金防范風(fēng)險(xiǎn)。 “我也是不主張剝奪開放式基金的融資權(quán)利的。”王連洲的觀點(diǎn)與周正慶基本一致,但是他建議要對融資的比例、期限、用途作嚴(yán)格規(guī)定。 盡管二審時(shí)保留了允許開放式基金短期融資的規(guī)定,但如此重量級人物的觀點(diǎn)鮮明對立,已經(jīng)預(yù)示了這一條款獲得通過的難度相當(dāng)大。矛盾的焦點(diǎn)在于基金公司的風(fēng)險(xiǎn)是否會轉(zhuǎn)嫁給銀行,在雙方爭執(zhí)不下的時(shí)候,“最終是高層領(lǐng)導(dǎo)拍板,決定刪除這一規(guī)定。主要是因?yàn)槲覈壳皩?shí)行的是分業(yè)經(jīng)營、分業(yè)監(jiān)管,禁止銀行資金入市,如果允許基金管理人為基金申請融資,這一禁令就會被打破。”王連洲的解釋證實(shí)了秦池江的顧慮,在某種程度上也代表了監(jiān)管層的擔(dān)憂。 “實(shí)踐中雖然發(fā)生過比較集中的申請贖回的現(xiàn)象,但由于基金管理公司都已按有關(guān)規(guī)定,在基金資產(chǎn)中保持了一定比例的現(xiàn)金和政府債券,并在合同中事先約定了相關(guān)條款,較好地解決了支付大額贖回的資金安排,至今還沒有出現(xiàn)過不能支付的問題。所以是否通過向銀行融資來解決贖回款項(xiàng)的支付,并不是基金公司需要迫切解決的問題。與其為這個(gè)爭論不休,還不如放一放再說。”華夏基金管理公司的首席分析師張后奇無意中點(diǎn)破了再次以回避矛盾的方式解決的事實(shí),“法律沒有禁止的就可行,盡管刪掉這一條,還是為開放式基金短期融資保留了法律空間。”王連洲也認(rèn)為,可以在實(shí)踐中進(jìn)行探索,今后還有修改的可能。 “理想中的投資基金立法還是一部綜合的法律,在募集形式上包括公募和私募,在投資方向上包括證券投資基金、產(chǎn)業(yè)投資基金和風(fēng)險(xiǎn)投資基金。”一直對綜合立法情有獨(dú)鐘的王連洲在《證券投資基金法》出臺后,對記者坦言理想與現(xiàn)實(shí)的差距。 不過故事的最終結(jié)局還算是圓滿,《證券投資基金法》剛剛出臺,證監(jiān)會又開始就《證券公司客戶資產(chǎn)管理業(yè)務(wù)管理暫行辦法》征求意見,巧合的是王連洲又在參與之列,“這個(gè)《暫行辦法》規(guī)范的正是私募基金的一部分。各類基金由不同的法律進(jìn)行監(jiān)管也不失為一種解決辦法。畢竟,再單獨(dú)為產(chǎn)業(yè)、風(fēng)險(xiǎn)投資基金立法在短期內(nèi)是不太可能了。” |
|
| 新浪首頁 > 財(cái)經(jīng)縱橫 > 焦點(diǎn)透視 > 《證券投資基金法》施行 > 正文 |
|
| ||||
| 熱 點(diǎn) 專 題 | ||||
| ||||
|
新浪網(wǎng)財(cái)經(jīng)縱橫網(wǎng)友意見留言板 電話:010-82628888-5173 歡迎批評指正 新浪簡介 | About Sina | 廣告服務(wù) | 聯(lián)系我們 | 招聘信息 | 網(wǎng)站律師 | SINA English | 會員注冊 | 產(chǎn)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4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