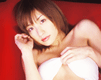|
文/傅勇
曾幾何時,中國的富豪們給人留下了揮霍無度的暴發戶形象。前不久,美國《時代》雜志“生動地”描繪了中國富豪的典型生活方式。男人們身著“國產或者意大利品牌的西服(袖子上還留著商標)”,“在每年會費1萬美元的俱樂部中打高爾夫球,去拉斯維加斯豪賭。”“每餐要在600美元以上,菜單中包括鯊魚翅、鮑魚等各種高檔海鮮,”;而女人們則是
懷抱長毛寵物,穿的是“路易·威登或者香奈爾的時裝”,手提“芬迪的手袋”,涂上鮮紅的指甲油,“只乘坐奔馳轎車或者黑色勞斯萊斯轎車,同時配有吉利號碼的車牌……”
幸好,近日發布的2005年內地慈善家排行榜為我們提供了一些鮮活的反例,使得上述描述顯得以偏概全,讓人難以認同。在內地慈善家排行榜位列榜首的云南世紀金源集團公司董事長黃如論無疑是近年來的“慈善先生”:過去兩年內他共捐出了2.86億元,相當于他全部財富的二成。
我們得承認,正確地看待自己財富并將他們處置得當并非易事,為物所累的人并不在少數。對此,美國鋼鐵大王、私人大規模慈善活動的倡導者卡耐基深有體會。在專門探索如何正當處理財富的書(《財富的福音》)中,他這樣寫道:“應該好好記住,賺錢需要多大本領,花錢也需要多大本領。唯有如此才能有利于社會。”最后,卡耐基捐出了他一生所有的財產,共計3.5億美元,相當于現在的30億美元。由此倡導了美國大規模的慈善事業。
對于我們這個正致力于建設和諧社會的發展中大國來說,這一點尤為重要。市場經濟是我們已經找到的最能激發人們創富欲望的制度,然而,一個和諧社會絕不僅僅意味著商品的堆積。市場經濟的邏輯本質上是一種優勝劣汰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財富的集中不僅是獲取規模效益的需要,也是市場競爭的必然結果。這一機制正是保證經濟效率的前提。因此,貧富不均是不可避免的,起點上的不公平又會導致更嚴重的分化。而馬克思對資本主義最為憎惡之處也正在于此:在資本積累過程中,“財富在資本家一端累積,而貧窮在工人階級一端累積”。
《圣經》中“馬太福音”第25章有這么幾句話:“凡有的,還要加給他叫他多余;沒有的,連他們所有的也要奪過來。”1973年,美國科學史研究者莫頓用這句話來概括社會分化的現象,并命名為“馬太效應”。市場競爭的這種“馬太效應”無疑是和諧社會的最大威脅之一。
對此,政府的有形之手能夠解決一部分問題。福利國家在財富再分配上做的不可謂不多。然而,在維護公平的同時也損害了效率。瑞典作為福利國家的“櫥窗”,還獲得了一項額外殊榮——以自己國家命名的“瑞典病”:經濟增長緩慢,工作積極性下降,政府機構龐大等等。原因很簡單,高額稅收強行拿走了過多的利潤,降低了企業家甚至工人的積極性,從而影響了把蛋糕做得更大。
實際上,對于一個和諧社會來說,最好的穩定器來自人們發自內心的慈善活動。自愿的慈善活動給了慈善家們充分的自由度來決定何時貢獻自己的財富。在個人事業處于發展時期,財富的積累對企業家自己也非常重要,應該允許他們專注于自己的事業。實際上,隨著年齡的增長,大多數人會傾向于看淡財富,而更加關心社會的疾苦。因此,慈善這種財富的轉移方式無疑要靈巧和柔和的多。
具體來說,慈善活動首先幫助社會實現了一種分工:在某個時刻,有些人在努力做大蛋糕,而慈善家則關心如何公平地分配它。這樣,前者并不一定要隨時準備把自己的財富貢獻給社會,相反,可以把財富投入到再生產中;而慈善家是在把已經積累起來的財富在社會范圍內再分配。也就是說,這種分工可以保證生產性更強的資源從事生產。正如現代經濟學的鼻祖亞當·斯密所發現的,分工是提高經濟效率的最重要的源泉,財富上的分工也是如此。這樣,慈善活動在一定程度上擺脫了政府征稅“一刀切”式的拙笨,能較好地協調公平和效率的關系,增強社會自我調節的韌性。
其次,慈善的作用在于在總財富一定的情況下,能夠增進社會整體福利。福利經濟學指出,同一般商品一樣,人們從一單位財富中所獲得的滿足感隨著財富的增加而不斷減少,也就是說邊際效用遞減規律同樣適用于財富。具體地看,同樣是100元,對一個億萬富翁和一個下崗職工來說,意義可能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慈善家把一部分財富轉移給窮人,對整個社會來說,所增加的效用要大于減少的效用,從而會增進全體人民的福利。而這在經濟學上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卡爾多式的社會改進。
當然,慈善活動絕不是富翁們的專利。其實,美國只有10%的捐款來自公司企業,5%來自大型基金會,而85%的捐款來自美國民眾,這些捐款占了老百姓平均收入的2%。所以,眾人拾柴火焰高,正是涓涓細流匯成了金錢巨浪。而要在一般民眾中樹立起合理的財富觀,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慈善這一社會穩定器作用的有效發揮需要為其提供良好的環境。人們愿意慷慨解囊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們能夠信任接受捐款的慈善機構把他們的錢真正用于他們所關注的事業上。另外,為了鼓勵社會參與慈善公益事業還可以制定一些稅務優惠政策。比如你捐款100美元,就可以得到30美元的稅務優惠,實際上你只捐了70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