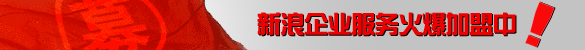|
■調查報告■湯安中
近年來國內學者對貧富差距作了大量研究,多采用基尼系數方法,但所得結論極不相同,使人無所適從。根本原因是中國統計數據攙水、攙假所致。另一些學者則采用大數法,以一個省為基本樣本單位,對比分析東西部貧富差距,然而省內各市、縣都存在著巨大差距,如甘肅的蘭州市與隴南的自治縣,收入分配水平相差8—10倍,在大平均數下,經濟總量
小的貧困縣的真實情況完全被掩蓋了。再者,上述兩種慣用的研究方法,可操作性較差。
因此,筆者決意跳出基尼系數及大數研究方法,另辟研究蹊徑。以東西部縣域經濟為案例,用實證的方法研究經濟差距變化軌跡,探索縮小差距的路徑。
縣域是貧困人群的農民最集中的地方。薩繆爾遜研究美國的貧富差距時,采用多角度方法,既有對政府部門提供的全國家庭收入分配的研究,也研究了“財產的分配”,研究了不同職業的收入差距,還研究了經濟等級化與機會以及收入和能力差別等方面的問題。筆者以為,中國的貧富問題也有許多方面可以研究,中國不同于美國,中國的農村人口占到70%以上,最大的貧困人群是農民。因此,只要研究清楚了農民,也就基本摸清了中國貧困的演變軌跡。
為了增加貧富差距變化的可比性,東西部各選了兩個改革開放前均以農業為主導產業的縣,農村人口均占85%以上。
東部所選的兩個富縣,均在浙江省,因為該省經濟在改革開放以來的20余年中,國家財力及外國資本影響甚小,換言之,外生變量影響小,全靠內生增量活動快速發展起來的,這使我們在對比西部貧困縣時,具有了較現實的較相近的可比性。
所選的東部富縣,特地選了兩個百強縣:一是前18名,一是前55名。西部的兩個貧縣則均屬于省級貧困縣。如果貧富差距是4∶1,那么,東西部貧富差距就可確定為小于4∶1,從而不需將全國所有富縣與所有貧縣的數據加以統計、梳理再去作對比分析了。
選擇以縣域經濟作基本樣本,可以繞開與上海、北京、蘇州、南京、西安、重慶、昆明等大都市的不可比性。因為,大都市在改革開放前就遠遠比西部廣大農村要發達得多,改革開放后,因人文與地理條件的優越,又接受了數千億美元的外資與數萬億元國家財力支持,它們的經濟總量對于西部貧困省是一個望塵莫及的經濟巨無霸。北京市的地方財政收入2004年為744億元,相當于陜、甘、青、寧、新、藏、黔七省區之和還多。上海財政收入為1106億元,則更多了。根本無法去作有意義的比較。避開大都市,在研究縣與縣的貧富差距時,就可較好地摸清許多真實情況,發現貧富差距的軌跡。
考慮到1990年以前的數據殘缺不全,準確度差,本課題著力研究1990年至2004年以來15年的變動軌跡。
一、貧富差距變化的軌跡,在1990年代中期以前是越拉越大,之后,人均GDP與農民人均純收入的差距都由拉大轉為縮小
1990年代前期,東部的潛在生產力處于超常發展時期,尤其是1992年小平南巡講話后,思想獲得了再次解放,土地生產力要素的作用得到了數倍、數十倍甚至數百倍的放大,經濟特區、開發區、高新區、工業園區、臺灣工業園等等,在東部地區遍地開花、結果。因此,東部的經濟發展出現了“井噴”,而西部卻仍處于“冰封期”。因此,東西部人均GDP的差距曲線成45°上升。從1991年的1∶2.2開始之后的幾年,表現為1∶3.2,1∶5.1,1∶5.6,1∶6.1,1∶6.8,1∶7.6。尤其是1992年至1996年,幾乎每年擴大1倍!自1999年后,東部改革開放的春風終于度過了“玉門關”,人均GDP的較大差距開始緩慢縮小。到了2004年,西部人均GDP為3777元,東部為19262元,差比降為1∶5.1,相當于1994年的水平。
出乎人們意料的是,農民人均純收入的貧富差距,比人均GDP差距縮小得更快更早。從1990年的1∶25起拉大,之后幾年分別為1∶2.6,1∶2.8,1∶2.9,1∶3.8,1∶4.4,到1996年達到1∶48,比人均GDP的最大差距的1∶76還要小得多,而且是提前兩年即達到了人們所講的庫茲涅茨曲線的谷底,在1997年開始出現了人們所講的“先升后降”。之后的8年,一直保持一種不斷縮小的趨勢,2001年出現小幅反彈,主要是受農業旱災影響。到了2004年,西部二縣農民人均純收入為1940元(西部12省平均為2192元),東部二富縣為5820元,差比為1∶30,相當于1993年的差距。
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04年,二貧縣為5538元,二富縣為15476元,富縣為貧縣的2.78倍,這說明,同樣是工薪階層其收入東西部也存在近3倍的差距。
二、東西部貧富縣差距所以在1990年代中后期由拉大變為縮小,最主要原因是民工經濟、鄉鎮企業及農業政策,而人口自然增長率的反向變化也是其原因之一
(一)農民工經濟的蓬勃發展是推動東西部貧富縣農民純收入差距由大到小變動的決定性因素。
就農民人均純收入的差距變化趨勢看,1985年為1∶2,1996年最大時為1∶4.8。從1985年至1996年的11年時間,收入差距之所以如此迅速拉大,根本原因是:東部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及民工潮的涌起,使東部農民從鄉鎮企業(包括個體)及打工收入中的工資收入部分的比例迅猛增加,從而使農民純收入呈超常增長之勢。東部富縣數據表明,1991年至1996年,每年較上年的增長率為:12.5%、20.5%、21.1%、36.6%、41%、17%。而西部地區農村,由于觀念的落后、信息的閉塞,很少有農民下廣東、去沿海打工,此階段農民純收入中家庭收入90%全靠農牧業。至1990年代中期后,由于民工潮的不斷擴展,在比較利益誘導下,西部農民終于離土離鄉外出打工,從而改變了西部貧困縣農民單靠農牧業的經濟收入結構。1998年以后,全國農村外出打工人數每年幾乎都保持在10%以上的增速,2003年、2004年外出打工勞動力分別占到農村家庭戶數的68%、75%,勞動力外出打工收入一般可占到家庭全部收入的30%,有的占到40%。因此出現了農民人均純收入的快速增長。這種差距的縮小可以說完全得益于東部草根經濟與大規模的城市建筑的高速發展,勞動需求在當時并不需要有高技術、高技能,因此使西部貧縣大批低技能及無技能的農民都能找到賺錢的地方。可見富裕地區的經濟的發展效應從收斂到擴散,在中國的就業方面得到了充分體現。這也證明了小平關于“讓一部人先富起來”的構想是正確的。
民工經濟對縮小人均GDP差距也有作用,但不如對農民人均純收入影響大,因為,GDP產值還包括工業、商業、服務業。西部貧困縣要發展第二、第三產業是一個縣的整體經濟實力決定的,因此人均GDP的差距直到1999年才開始由拉大變為縮小,直至2004年仍達1∶5之大。在這里有一點需要指明的是,自1999年國家在貧困縣開發了鋁、鋅礦藏,投入了10多億元,使GDP大量增加,因此才使人均GDP差距快速縮小。若沒有國家的巨額投入,據筆者的計算,由于民營經濟的開始發展,人均GDP也會縮小,但幅度遠要小得多,那么2004年的差距會是1∶6或更大些,而不是1∶5。
(二)人口的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人均純收入比差。
東部富縣從1985年開始,大家都忙于生產發展,自覺計劃生育,因此人口自然增長率降至10‰以下,1994年、1995年、1996年、1997年為分別為7.77‰、5.01‰、4.58‰、5.07‰,平均為5.61‰。而西部的貧縣,從1990年至1997年一直保持11.6‰以上的增速,最多一年達到19.15‰。同樣的財富被快速增長的人口分攤,自然就少了。到1998年后,貧縣的人口自然增長率出現了較大降幅,1998年至2003年,分別為7.9‰、7.6‰、11.2‰、7.1‰、7.3‰、8.9‰,平均為8.3‰,而相反的是,富縣在2000年后,由于有錢了,“有時間生孩子了”,遂出現了反彈,2000年至2003年四年的平均增長率為9.45‰。一降一升,對人均GDP及農民人均純收入之差距發生逆向的正馬鞍型變化。人口多了,不僅影響收入的分攤,還影響勞動收入的獲取。
(三)農業政策的影響。
在2001年前,農民的負擔較重。自“三提五統”及農業各種稅取消,近年又有了糧食直補,相對增加了農民的純收入。此外又開始實行了退耕還林還草,每畝補助160元,退耕的地種了多年生的苜蓿,又以苜蓿養了羊,從養羊中又獲得了一筆增收。
教育的因素在2004年前影響力雖有,但尚不明顯。
正是上述基本原因,使東西部貧富差距從1990年代中后期達到了庫茲涅茨曲線的谷底,然后在東部經濟的擴散效應及國家的積極扶農政策的支持下,開始出現了良性的縮小趨勢。但若以為,只要政策正確、加強扶貧力量就可在短期內從根本上改觀西部的貧困,那就大錯了。筆者實地考察發現,深層的經濟實力的差距還相當之大,主要是社會生產力性質(體現在產業結構上)、經濟的耗散結構程度、地方財政的創收能力以及飲用水這四個方面的差距,決非短期內可獲得根本改變。過高的期望值只能導致國人的急躁與埋怨情緒,對穩步推進改革與可持續發展極為不利,需要國人警惕。
(作者單位∶山東師范大學經濟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