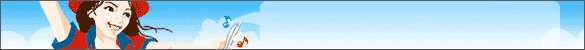|
2005年7月6日,法國著名作家、1985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克勞德·西蒙辭世。作為法國“新小說”派重要成員之一,西蒙最突出的風格是在文體上的變革,然而就在這種極端前衛(wèi)的文體中,隱含了對人類生存現(xiàn)實的深刻關注。通過對愛、時間、死亡、希望、戰(zhàn)爭等等諸如此類題材的處理,西蒙的寫作最終打開了一條“覺醒的通道”
□周江林
克勞德·西蒙這樣談到過文學及人生:“總是處理相同的事物——愛,時間,希望,覺醒的通道,男人的悲傷,死亡。”
對于克勞德·西蒙來說,死亡就是一條覺醒的通道。2005年7月6日,這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法國新小說派戰(zhàn)將與世長辭。一個美和德行普遍萎縮的時代,一個大師的離去。在西蒙離去的身后,人類“覺醒的通道”又將以怎樣的姿態(tài)向前延伸?
童年的傷口
克勞德·西蒙出生后幾個月,身為騎兵軍官的父親就死于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中。西蒙被母親帶回法國。
年輕時,西蒙參加過西班牙反佛朗哥的內戰(zhàn),隨后又入伍參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戰(zhàn)爭對于他來說,是最重要的經歷之一。
從西蒙的早年經歷不難發(fā)現(xiàn),他很早就沒有了青春,他身上深深印下了人類暴力文明的傷口。戰(zhàn)后他到蘇聯(lián)、歐洲、印度、中東各地旅行,歸來后在鄉(xiāng)間從事葡萄種植業(yè),同時進行文學創(chuàng)作。
西蒙探索一種像巴羅克體藝術的螺旋形敘述結構,以代替?zhèn)鹘y(tǒng)的直線形敘述,并以此表現(xiàn)內心活動中不斷變動的感覺、回憶和想象。
在幾乎完全排除了傳統(tǒng)小說敘事中追索時間的方法后,西蒙試圖呈現(xiàn)的是小說的空間組合,展示多層次的畫面描述——以獨特的夢游者之觸須感受世界,其“漫游”境界因而富有詩意和迷人,但同樣具有閱讀難度,《弗蘭德公路》就被公認為難以卒讀之作。造成這一狀況的原因,可能與他早年經歷的傷痕有關,他必須通過寫作再現(xiàn)這些傷痕,并以此達到自我治療的目的。
西蒙令人驚嘆的是他的持久力,他認為自己是在進行文學領域內保守勢力與進步力量的斗爭,一個作家的任務是不向潮流趨勢低頭。西蒙一直走在自己的路上,一走就是50多年。
夢游者的現(xiàn)代政治學
這個世界沒有新意。
任何時代,“出位”和“退隱”都是不同方向的兩種方法——一些人憑借體力和勇氣攀登上耀眼舞臺,另一些人卻選擇隱忍。在所謂的新小說派陣營里,前者有羅伯·格里耶和杜拉斯等,后者就是這個克勞德·西蒙。不同的方向飛往天堂和地獄,卻贏得了相同的需求——在這個貧乏世界生存的自由感覺。
不管承認與否,赴死情結其實滋生了西蒙的一種政治學——他的文學有藏在暗處的政治傾向——這里,人們總被一種觀念所誤導,認為像西蒙們,只是迷醉純文學境界者,用文字建構他的世界疆域。
其實,幾乎所有世界藝術史上功成名就的人物,都是當代政治學的參與者——小說創(chuàng)作就是一種政治活動。
同樣的概念延伸,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就是7月9日晚在北京工體形成大多數(shù)旋風的周杰倫,也是體現(xiàn)時代強烈的政治表現(xiàn)性——只是少數(shù)者西蒙與大多數(shù)周董及傳統(tǒng)在參政方式有所區(qū)別,從此意義上看,西蒙對我們時代青年是能產生意義的,只是并沒有多少人能意識到。
西蒙的政治觀體現(xiàn)在對戰(zhàn)爭復雜的心態(tài)上,西蒙意識到戰(zhàn)爭的因子早已滲透到各種社會形態(tài)中,暗藏各個角落,并可怕地從每一個人隱秘的心靈處被漸漸喚醒,個人身上的自我可能是培育惡性的溫床。
因此,當代人的重任是如何做。
對付現(xiàn)實的人生
在《草》卷首,西蒙引用了帕斯捷爾納克的話:“誰也創(chuàng)造不了歷史。人是看不到歷史的,就如同看不見草生長一樣。”這無疑表明了西蒙對現(xiàn)實的不信任。在日后的創(chuàng)作歲月中,他更多地選擇碎片般的夢游。
成為夢游“他世界”的旅行者是容易實現(xiàn)的,接下去,對付現(xiàn)實的人生必須以大勇氣為無形的代價。
其實,說克勞德·西蒙的作品僅僅采用了一種拒絕理解的寫作風格,顯然是片面的。他沒有這么強悍,他不想成為一位明星,一位文體明星——雖然法國歷來有制造藝術和哲學明星的偉大傳統(tǒng),但是,西蒙不是,他是獨居和低調的。
他喜歡葡萄園和葡萄酒,除了讀書、參加戰(zhàn)爭以外,他大多數(shù)的歲月就生活在葡萄園里。他還喜歡黃昏,喜歡露水,喜歡青草的味道和奶牛,也偏愛鄉(xiāng)野間的性事。《弗蘭德公路》、《歷史》和《農事詩》幾乎就是這些的產物。
我認為,1985年諾貝爾對他的評語“以詩和畫的創(chuàng)造性,深入表現(xiàn)了人類長期置身其中的處境”,似乎有點含糊其辭。究其原因,西蒙本身就有點含糊。他那太個人的生活場景,就像七小時以上的長篇獨白,說來說去就是那種感覺。然后,從大的范疇說,的確類似人類的處境——所謂人類,既是指我身邊那幾個人。
在答謝諾貝爾獎詞中,西蒙引用了馬克思《資本論》中的觀點:一種使用價值或一件物品,只是當人類的勞動體現(xiàn)在其中時才具有價值。他對機械化、工業(yè)化的潮流持批判意見。他像他的前輩、戰(zhàn)友一樣,視潮流為人類的一種腐化力量,但顯然他個人并不試圖與這世界斷絕聯(lián)系,只是呈現(xiàn)一種緘默的欲望。
但是,讓人覺得累心的,并非是他前無古人的文體,而是他那幾乎病態(tài)的理智的定力,以及他“在戰(zhàn)爭中深深的感人的沉思”。實際上,他的沉思一直不愿醒來,而他的沉思也從未回避現(xiàn)實 。
克勞德·西蒙生平
克勞德·西蒙,法國小說家。1913年生于馬達加斯加的首府塔那那利佛。他出生幾個月后,身為騎兵軍官的父親就死于戰(zhàn)場。西蒙被母親帶回法國的佩皮尼揚接受小學教育,后來又到巴黎一所著名中學就讀,畢業(yè)后赴英國牛津和劍橋大學讀書,他還曾隨法國立體派畫家安德烈·洛特學過繪畫。
1936年,他曾到西班牙共和軍與佛朗哥部隊激烈爭奪的巴塞羅納協(xié)助起義者,這場殘酷的戰(zhàn)爭在他的心中留下極其深刻的印象。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爆發(fā),西蒙應征入伍,成為第31個龍騎兵。1940年春,他參加了著名的牟茲河戰(zhàn)役,受傷被俘,不久又逃出德軍集中營,回國參加地下抵抗運動。戰(zhàn)后他到蘇聯(lián)、歐洲、印度、中東各地旅行,歸來后在鄉(xiāng)間從事葡萄種植業(yè),同時進行文學創(chuàng)作。(志琳)
由西蒙之死 聯(lián)想到法國的失落
七月的法國注定是陰郁的。6日,巴黎從原本勝券在握的2012年夏季奧運會舉辦權競爭中突遭淘汰。一時間,法國民眾莫名不安,仿佛在陽光下被對手暗算了一下。體育歷來是主流大眾的節(jié)日,更何況奧運盛典,幾乎可以和國家利益相提并論,這種失落也就可想而知了。
然而,世人不知,就在7月6日這天,法國最近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著名作家克勞德·西蒙逝世,享年91歲。消息傳出已是三天之后,西蒙業(yè)已安葬。
法國文化部部長雷諾德·瓦布萊斯遲遲才透露這一消息,這里也許有著國家出于對大事件的平衡利益考慮。將體育和文學放在一起比較,兩者同為國家、社會和一個時代作出了貢獻,但是吸引眼球的效果,以及附帶出來的所謂“身價”,竟顯得如此不同:孰重孰輕,不用經過大腦,誰都會有結論。
將歷史回溯幾百年,那時的文學(連帶其他藝術或思想)是主流中的主流,法國給人類貢獻了多少熱血沸騰的偉大作品和思想,這種驕傲感,人類一直在享用。只是,世界全球化和越來越提速的實用主義趨向,已經將美和德行消磨成一種小圈子里打轉的優(yōu)越感,即便人文傳統(tǒng)豐厚的法國也難免俗。
一位戴上諾貝爾桂冠的文學大師之死,等于某些精英堅守的陣地,再一次后撤一步。少數(shù)歷來會被大多數(shù)步步擊敗,這是常識,但是,人類可貴之處也在于,總會有人對這個世界大多數(shù)人的趣味,說不!克勞德·西蒙就是其中一個。
在他眼里,純粹的情感本身是文學的基礎,而現(xiàn)代人缺乏真正的情感,純粹的情感。也少有辨證的是非觀念和尋求靈魂家園的沖動。人類總會在物極之際渴望另外的東西,此時,文學(藝術)雖然薄如游絲,但總會牽上人類伸出之手。(江水)
【留聲】創(chuàng)作是一種勞作
數(shù)世紀以來,在文藝復興之前、之中以及之后,最偉大的作家或音樂家都是運用的一種藝人的語言,他們有時被視為奴仆,奉命進行創(chuàng)作,他們把自己的創(chuàng)作視為勞心費力,盡責盡力之作 (我想到的是讓——塞巴斯丁·巴赫、尼古拉·普桑等人)。
而今,對于某些評論家來說,勞動、工作這些概念已變得如此信譽掃地,以至一談到某個作家的創(chuàng)作艱辛,他們就覺得這是天大的笑話,對此如何解釋呢?也許,對這個問題多談幾句并不是壞事,因為這個問題涉及的范圍要比單純的意氣用事廣泛得多。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章中曾寫道:“一個使用價值或財物只有當它體現(xiàn)了人類勞動時才具有某種價值。”這就是一切價值的艱難起點。雖然我既不是哲學家也非社會學家,可是有種現(xiàn)象令我困惑不安:在19世紀,隨著機械化和工業(yè)化的飛速發(fā)展,人們同時看到了一種不良意識的冒頭和勞動概念的貶值(這種轉化勞動報酬極其微薄),作家被剝奪了努力創(chuàng)作的權力。
——摘自1985年西蒙
獲諾貝爾文學獎時的演說辭
法國“新小說”簡介
法國“新小說”是一種創(chuàng)新的文學實驗,上世紀30年代出現(xiàn),到上世紀50年代才形成頗有名氣的文學流派。
“新小說”派有四大干將:羅伯·格里耶、娜塔麗·薩羅特、克勞德·西蒙、米歇爾·布托爾;而名氣較大的貝克特、杜拉斯則被認為是外圍作家。這些作家創(chuàng)作出一大批跟以巴爾扎克為代表的傳統(tǒng)寫實小說風格迥異的小說,在具體的寫作方法上力求創(chuàng)新為主要特征,后來被泛稱為“新小說”。
“新小說”主要作品發(fā)表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上世紀70年代末走向消亡。但到了1985年,克勞德·西蒙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標志著“新小說”得到西方學院派認可,成為法國文學史中的經典。上世紀80年代,我國對“新小說”的介紹達到高潮。
(志琳)
西蒙書架
《風》
在這部作品中,西蒙寫了發(fā)生在外省小城中的欲望和騷亂這樣一個淺顯、直露的故事,并以此對人類的境況進行深入的探察。《風》把生活描繪成了“一個沒有開端或結尾的混雜物”,同時又有點贊頌“它的絕妙和驕傲的獨立”。
《弗蘭德公路》
是一部戰(zhàn)爭題材作品,表現(xiàn)手法新穎而獨特。小說沒有按傳統(tǒng)的時序敘事,而是由戰(zhàn)后騎兵喬治與德·雷謝克的年輕、放蕩妻子高麗娜過夜時所產生的斷續(xù)回憶,以及雜亂無序和模糊不清的想像來展開故事,表現(xiàn)主題。
《豪華旅館》
這部小說形象地重構了西蒙在西班牙內戰(zhàn)期間的經歷,它敘述的是一個革命領導人被那些誤認為是自己一方的人暗殺。作品對人類能夠極大地改善自己這種能力,從客觀和主觀上都持一種極端的悲觀主義觀點。
《常識課》
通過3個在戰(zhàn)爭中陷入困境的士兵,寫到了戰(zhàn)前戰(zhàn)后的種種生活情景。書中插圖不僅給了敘述者回憶種種生活場景的機會,也給了讀者無窮遐想。
《有軌電車》
本書是西蒙晚年的作品,因此有著更多的回憶成分。作者以家鄉(xiāng)地中海海濱某小城的有軌電車這一條線為紐帶,寫出了電車線兩端以及沿途15公里風景線上的種種物質面貌。并且從這兩點一線所組成的空間中展開,鮮明而生動地描寫了從過去到現(xiàn)在活動于這些地點上的人和事。
《歷史》
該書1967年獲得麥迪西文學獎。在這本小說中,西蒙有時似乎是把字詞當作抽象畫家的色彩來使用。《歷史》盡管有情節(jié)和人物,但是它的主要內容是一些經常出現(xiàn)的由語言交織成的視覺圖像,以此來探索伴隨而來的意義。
《植物園》
這是一部自傳性作品,本書巧妙地“把一個人于本世紀各時期在世界各個角落的零碎生活片斷混雜在一起”,在細部看似繁瑣雜亂、無規(guī)律,在整體看來卻既簡單明快,又賞心悅目。《植物園》延續(xù)了西蒙以往小說的追求和主要風貌。在書中,真實和虛構、心理和外界、暴力和愛、戰(zhàn)爭和人性,這些概念和概念的具體所指,無不滲透西蒙對和諧的向往。
《農事詩》
該書折射出《豪華旅館》曾有過的、對于混亂的西班牙內戰(zhàn)的觀念和情感的迷戀,并以更為復雜的語言來處理人類自我毀滅的沖動。當時許多法國評論家都覺得這部小說對西蒙的創(chuàng)作整體來說,有一點延伸和累贅的味道,而法文版和英文版之間印數(shù)的差距也表明了它們對英語國家文學界極其微弱的影響。(深山 志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