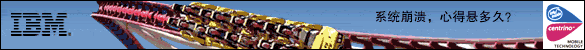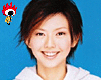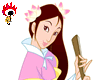| 評首屆“長江讀書獎” | |||||||||
|---|---|---|---|---|---|---|---|---|---|
| http://whmsebhyy.com 2004年06月11日 12:32 中評網 | |||||||||
|
葛劍雄 我的遺憾 我的希望 首屆“長江讀書獎”的結果發表后,我和一些朋友一樣,感到吃驚和遺憾,如此引人矚目的評獎居然因為一個本來完全可以避免的低級錯誤而黯然失色。作為百名推舉委員之
我一直沒有公開發表我的看法,因為要說的話別人基本都已說了。前幾天《文匯報》的記者作電話采訪,我才說了幾點看法。昨天她又打來電話,告訴我這篇報道星期六將見報,但引述我的話只有一句。今天,北京一位朋友又勸我將這些想法寫出來,這才有了下面這些文字。鑒于近來網上一些非理性的言論,為了避免不必要的誤解,我在接受電話采訪后就已將所說的內容電告《讀書》編輯部的吳彬女士。 我最大的遺憾,是這次評獎違背了一條基本規則——主辦者不得包括在評選范圍。按照國內外評獎的通例,《讀書》編輯部作為評獎的主辦單位,所有的工作人員都不得列入評選對象,即使被提了名,主編汪暉自然更應在回避之列。有些讀者或許不知道這一通例,但我相信百名推舉委員應該具有這樣的常識,更何況是嚴格挑選出來的評委!要是事先明確了這一規定,根本就不會出現這樣的“民主”后果。退一步說,即使評委一致推選了汪暉的書,主辦者就不能堅持規則,斷然拒絕?總不見到只有“民主”,沒有“法制”吧! 至于《讀書》現在的解釋,那是完全站不住腳的。問題不在于汪暉是否在國內,關鍵是他是否還是《讀書》的主編。汪暉出國時并沒有辭職,也沒有正式告訴讀者和推舉委員,在最近一期的《讀書》上他照樣是主編之一,怎么能成為破例的理由?即使他在評獎開始后正式離職,為維持這一獎項和汪暉本人的榮譽著想,也以繼續回避一段時間為宜。 這一解釋還有一個很大的漏洞。據說汪暉本來擔任評獎的學術委員會主任,因為出國才不當。一個中國公民要出國半年數月,大概不能說走就走,事先沒有安排,何況汪暉還擔當著《讀書》主編的重任?如果他原來就有出國的安排,何必再當學術委員會主任?如果他原來并不知道要出國,那么現在以他出國為由說明他與評獎結果不相干因而可以受之無愧,顯然完全是臨時找到的借口。 其次是選集能不能評獎。由于這次評獎的規則中規定了著作包括文集,所以評汪暉的自選集并不犯規。但我從維持這一獎項的學術聲譽出發,認為除了已故學者或老一輩學者終身成就性的文集外,一般不要評文集,特別是對較年輕的學者。這不是對汪暉的苛求,對其他人也是如此。如果有高質量的文章或專著,盡可以拿出來當文章或著作評,而文集中未必篇篇如此,再說每篇文章寫作或發表的時間也未必都符合評選的年限。 再次是在汪暉之外,居然還有不止一位評委是被提名或獲獎的對象。在這一點上,《讀書》的解釋同樣是不能令人信服的。評委會是最后開的,評委的名單也應該是最后才定的,那么當時已經知道他們的作品被提名或被推薦,有的還有很高的提名率,主辦者為什么還要讓他們當評委?本人為什么還要接受當評委?評委的名單是秘密的,當時如果換上其他人,對他們不會有任何傷害或影響。對那幾位評委來說,如果有被評上的愿望,一開始就該回避,為什么要等到自己的作品列為評選范圍后才退出呢?我不知道,其他評委的作品還有沒有被提名或進入投票范圍。如果只是因為最后沒有被評上而不公布,那如何保證評委的公正性?我認為,擔任評委的一個前提,就是自己絕不參加這一次評選,即使已經被提名也應要求不列入討論。如果不愿意放棄這一權利(當然完全允許),就不應該當評委。 至于對按正常程序評選出來的結果,大家完全可以有自己的看法。本來“長江讀書獎”只是民間的獎項,并不代表整個學術界或知識界,更不代表政府主管部門。只要資助方與主辦方決定了的事,旁人是沒有權力干預的,至多只能議論。主辦者有權選定評委,評委有權評出他們認為合格的結果。但這項獎最終能擁有什么地位,是否能達到主辦者預定的目標,能否具有與獎金額相稱的學術性、權威性,或能相當于國內、國際的哪一種獎,則完全取決于其評獎的程序與結果是否達到應有的水準。從這一點上說,決定的因素不是資助方與主辦方,也不是獎金的數額,而是學術界、知識界和廣大讀者。正因為如此,我才為《讀書》和這次評獎的結果感到遺憾,因為這樣高的獎金和《讀書》已有的地位,本來完全可以獲得更好的效果。 我曾是《讀書》多年的作者,也是《讀書》的老讀者,自認為與《讀書》新老主編都是朋友。我愿意參加“長江讀書獎”的推薦,當然是樂觀其成,希望這一民間獎項具有真正的權威。時至今日,我還是希望主辦者能忘羊補牢,采取切實的補救措施。 我希望,在正式頒獎之前,汪暉兄表明態度放棄獲獎,主辦者宣布汪暉退出評獎。為汪暉兄和《讀書》計,這樣做有百利而無一弊,務請三思。如果認為有違民主,不妨請評委們再討論一次。萬一評委們還是堅持評選結果,汪暉兄主動放棄總可以吧! 我希望,主辦者認真總結一下這次評選的經驗教訓,廣泛聽取各方面意見,修訂出一套更科學、更嚴密的的規則和程序,操作更加透明。譬如說,評委資格應該加上本人的作品不參加本次評選為條件,否則就不得擔任評委。又如,第一輪推薦的結果也應公布,至少應該讓參與推薦的人知道。 我也希望,學術界、知識界關心《讀書》和“長江讀書獎“的朋友們都回到平心靜氣的、正常的討論中來,不要被某些人的謠言和攻擊所左右。 讀“長江讀書獎”工作室《鄭重聲明》 我要說的話,在上一篇文章《我的遺憾,我的希望》中已經說了,但讀了“長江讀書獎”工作室的鄭重聲明后,我不得不再說幾句。 一、聲明的第九點稱:“同時,我們也鄭重呼吁:尊重事實,尊重批評的嚴肅性。對惡意的造謠、中傷、誣陷,我們將保留追究的權利。”對前面的呼吁,我自然完全贊成,在拙文最后我也表明過這樣的態度。但對下面幾句話,我頗不以為然。本來,對惡意的造謠、中傷、誣陷,誰都有追究的權利,不聲明也罷。既然工作室這樣說了,那就意味著有所指,即現在已經出現了對工作室的造謠、中傷、誣陷。但據我有限的閱讀范圍(包括報刊與網絡),前階段對此事的評論有三個方面:一是由“亦遠”與甘陽的文章引出的《讀書》內部的人事紛爭,一是對這些年來《讀書》質量或變化的評價,第三是對這次評獎的議論。我一直主張,將這三方面區分開來,第一部分本不該公開議論,挑起的是甘陽,最多再加上甘陽的對手亦遠,要追究盡管可以找他們。第二部分本來是很正常的,任何雜志都免不了被人家議論,何況一直享大名的《讀書》?但此事與這次評獎是兩回事,沒有必要放在一起討論。退一步說,即使這兩部分已經出現了必須追究的問題,也是《讀書》編輯部或三聯書店的事,與“長江讀書獎”工作室有什么關系? 與工作室有關的只有第三部分。到目前為止,除了有些人言詞過激,將這次評獎斥之為“學術腐敗”或“丑聞”外,似乎也沒有什么造謠或誣陷。而且絕大多數學者的態度是嚴肅的,例如對某君一篇文章,已經有兩位學者聲明糾正。所以我希望工作室有一點雅量,我也希望大家在評論“長江讀書獎”時不要涉及《讀書》本身,有話不妨放在其他文章或其他場合去說。至于第一部分就更不應該與這次評獎扯在一起。如果工作室一定要管自己范圍以外的事,不妨找甘陽等人調查一下,他們要將三聯與《讀書》的舊事扯出來居心何在? 二、《聲明》第十點稱:“以上是迄今為止‘長江讀書獎’工作室發表的唯一正式聲明,我們對此聲明負完全的責任。”可惜這聲明發表得晚了一點,因為在此以前,我已經看到《南方周末》與《文匯報》的有關報道,我的前一篇文章就是根據《南方周末》報道引述《讀書》編輯部的話寫的,而這些話與這次聲明的內容是不同的。 《南方周末》上說: 這次獎項,引發微辭的是費孝通的《費孝通文集》、汪暉的《汪暉自選集》和錢理群的《想起七十六年前的紀念》。因為費孝通是特邀名譽主席,汪暉是學術委員會召集人,錢理群是評審委員會成員。 《讀書》對此做的解釋是,《費孝通文集》符合入選標準,但其文集是終生學術的匯總,拿出來競爭對其它作品未免顯得不公,因此臨時設立特別榮譽獎,此獎將不作為“長江《讀書》獎”的常項。 汪暉作為《讀書》雜志社的成員,和其他所有雜志成員一樣,是不具備推薦、評選資格的。但評選活動開始時,他已經在國外進行學術交流直到現在。《汪暉自選集》得獎后,(讀書》雜志原有將之撤下的打算,但這是經過程序產生的結果,《讀書》雜志沒有這個權力,民主的結果只能尊重。 錢理群和汪丁丁4月22日還在進行評審工作,由于他們兩人的文章都入選了文章獎,23日兩人退出文章獎評審委員會,結果是錢理群的文章當選,汪丁丁落選。《讀書》雜志透露,錢理群這篇文章在讀者和專家評選中都是排名第一。 6月24日《文匯報》的報道稱: 記者近日與《讀書》雜志社取得聯系,得到如下答復:首屆“長江《讀書》獎”是在推薦委員會推薦的基礎上,從得票最多的前10余本書中,由15位評委經過3天封閉式評審評出來的。在整個評審的過程中,所有評委嚴格按照規則進行。回避的原則是有的,那就是:“參評作品的作者,當年不得擔任學術委員”。因此當費孝通、汪暉、錢理群他們的著作或文章被推薦進參評行列,即被排除在相應獎項的評審工作之外,汪暉因此也沒有擔任本次活動的召集人。 而《聲明》稱: 這半年中,曾與推薦委員有多次會議討論和書信往來,但除章程草案中原有的“凡參評作品的作者,當年不得擔任學術委員”這一回避規則外,沒有委員提出任何新的回避規則。 著作獎和文章獎的評審是由兩個學術委員會分別獨立進行的。根據章程,凡有作品入圍者,均未擔任相應獎項的學術委員。 從評獎的運作考慮,設立“長江讀書獎學術召集人”,并根據有關召集人的具體情況,輪流負責各屆評選的召集工作。本屆評審的召集工作由黃平和汪丁丁擔任。 汪暉不是本屆評獎工作的召集人,也完全沒有參加包括章程設計、書目推薦和評審在內的任何工作。 只要一比較,誰都可以發現,三者之間,特別是《南方周末》的報道與《聲明》之間存在著很大的差異。例如,《南方周末》說“汪暉是學術委員會召集人”,《聲明》卻說“汪暉不是本屆評獎工作的召集人”(不過我還不明白,“評獎工作的召集人”與“學術委員會召集人”是不是一回事)。我們當然應該尊重工作室的《鄭重聲明》,但前面的消息是誰提供的呢?是工作室的某個人,還是《讀書》編輯部的什么人?或者是兩家報紙的錯誤報道?或者是哪方面的造謠、中傷、誣陷?無論如何,工作室或《讀書》編輯部應該有個說法。如果以前說錯了,也可以改正,其他人不應揪住不放,但也不能自己改了口又將責任推給人家。 我希望工作室將此事的前因后果說清楚,“以正視聽”。我還希望工作室公布負責人的姓名或工作人員的名單,使大家知道他們與《讀書》或三聯書店的關系,免得再發生誤會。 三、即使根據《聲明》,我們也不難發現,工作室自己制定的《章程》并沒有得到執行,《章程》明明規定“凡參評作品的作者,當年不得擔任學術委員”;但《聲明》卻曲解為“根據章程,凡有作品入圍者,均未擔任相應獎項的學術委員”。兩者的區別在于,前者規定只要有作品入圍,作者就不能擔任當年的評委,而后者卻加上了“相應獎項”,也就是說,著作獎的提名人可以當文章獎的評委,反之也一樣。但這幾個關鍵的字是誰加上去的呢?既然嚴格遵守《章程》,誰有資格作這樣的改變?這究竟是《章程》本身的漏洞,還是事后的曲解?這樣一改,這次評審的做法似乎沒有違規,因為據公布的名單,錢理群與汪丁丁是著作獎評委,而錢、汪都只有文章入圍。但根據《南方周末》的報道,“錢理群和汪丁丁4月22日還在進行評審工作,由于他們兩人的文章都入選了文章獎,23日兩人退出文章獎評審委員會”,既然這樣做不違規,而且他們倆人又不在文章獎的評委中,為什么到評審的最后一天(23日)要退出呢? 《章程》的規定本來完全正確,因為到評委會召開時,由推薦委員提名的著作和文章名單中,肯定已經有了錢理群與汪丁丁的作品,而且錢的提名還是第一,那么他們“當年不得擔任學術委員”。如果這條章程得到嚴格執行,今天就不會產生這方面的批評。我最善意的假設,是當時工作室和評委諸公,包括他們兩位本人都沒有在意,臨時發現不妥才退出,現在卻由工作室曲解章程,以彌補這個漏洞。 我希望工作室正式澄清:究竟是《章程》正確,還是你們現在的解釋對?如果現在的解釋對,“相應獎項”這幾個字是誰授權加上的?我還希望你們說明,在被提名的著作或文章中,還有沒有其他作者當了評委? 四、我對汪暉兄“6月11日以來三次致函工作室并轉學術委員會表示辭謝”感到高興,事實證明我低估了汪暉兄的判斷能力,所以才在上一篇文章中向他提出放棄的建議。不過有一點我還不明白,因為在此期間汪暉兄給旌旗網發過一篇三年前的舊作,作為對諸多評論的答復。這不能不使人產生這樣的聯想,如果不說以魯迅自比,至少汪暉兄是以魯迅為榜樣,面對“黑暗勢力”的圍攻。我還是希望做汪暉兄的朋友,希望自己未被列入“黑暗勢力”。所以我很想知道,汪暉兄之辭謝是出于什么原因,是因為作為《讀書》執行主編不應獲獎,還是因為不愿受“黑暗勢力”的圍攻?我希望在汪暉兄自愿的前提下,工作室能否公布一封他的信件?“以正視聽”。 聲明稱“但工作室至今仍建議他慎重考慮”,我不知道工作室是出于什么考慮。本來,當事人或主辦單位的工作人員不能參與評獎是國內外的通例,并無必要訂入章程,更不必專門研討。而且《南方周末》報道《讀書》編輯部也承認“汪暉作為《讀書》雜志社的成員,和其他所有雜志成員一樣,是不具備推薦、評選資格的。”我在前一篇文章中已經指出(并且得到諸多朋友的贊成),以汪暉出國為理由來破這個例是很不妥當的。事至如此,我不知道為什么工作室還要堅持違規,不能成全汪暉兄的正確選擇,使他能夠早日從這場是非中解脫。 五、《聲明》第八點稱:“汪暉在設獎的醞釀初期,就對之多有疑慮。但由于他是三聯書店聘請的兼職主編,不便對三聯書店的重大事物表示可否,所以一直對評獎一事保持距離。”對這段話我百思不得其解。據《聲明》和《工作日志》,汪暉是1999年10月出國的,而評獎的正式啟動是11月1日。在此前汪暉參加了設獎的醞釀沒有?他疑慮什么?是怕這次評獎出問題嗎?是對這種評獎方法、章程或人員組成有意見?作為局外人,我自然無法了解汪暉作為“兼職”的《讀書》執行主編與三聯書店是什么關系,也不知道這次評獎是三聯書店的“重大事物”還是《讀書》的“重大事物”,如果連他也不便表示可否,那么《讀書》編輯部中還有誰方便表示可否?因為據我所知,另一位執行主編黃平兄也是兼職,也不是三聯的全職人員,汪丁丁更不是三聯和《讀書》的人,他們豈不是更不便說話了嗎?那這次評獎的權究竟操在誰的手里呢? 如果汪暉的疑慮是對他自己的,莫非他已預感到著作獎非他莫屬,所以不得不有所考慮?任何人都有權憑自己的水平贏得獎項,如果汪暉有自信,并且希望獲獎,完全可以選擇辭去《讀書》主編,公開聲明遠離評選工作;如果根本不想獲獎,又何疑慮之有?讓別人評就是了。如果工作室和評委懂規則,肯定不會提《讀書》工作人員;如果他們不顧規則,還是將你評上了,只要宣布放棄就是了。 所以我更希望汪暉兄說明有關情況,“以正視聽”。 六、我非常贊賞工作室聲明的態度,“我們深感評獎工作的嚴肅性,也了解自己經驗的不足,所以一直關注著各界的評論,努力從中吸取善意的批評和建設性的意見,并繼續歡迎負責任的批評”。但我希望工作室能對已有的評論和批評作一點具體的反應。 事至今日,為了認真總結經驗,也為了進一步取信于知識界和公眾,工作室應該公布一些基本事實,例如,顧問委員會請了哪些學術界的前輩?他們同意了沒有?他們對對評委的組成表示過意見沒有?有多少人對書面征求意見作出了反應?推薦委員由哪些人組成?哪些人作了推薦?具體推薦了哪些作品,各得幾票?我認為,公布這些內容也是有百利而無一弊,而且已經不會影響評選的結果,更不會對任何個人帶來傷害。 我也希望當事人,如顧問委員、推薦委員和評委在自愿的前提下公布有關情況,以幫助工作室認真總結經驗,也可避免外界不必要的猜測,防止別有用心的人造謠、中傷、誣陷。本著這樣的愿望,我自愿公布我于2000年1月9日通過《讀書》的信箱發送的一封郵件: “長江《讀書》獎”執行委員會: 因只收到過十一月二十日的會議紀要,未見過此前的“計劃草案”,所以對評選范圍和截止時間等尚不大明白,加上年前雜事甚多,未能及時寄回推薦表,十分抱歉。實際上接推薦表后也一直在考慮該推薦哪些書,只是茲事體大,近年我閱讀范圍既小,數量更少,所以始終定不下來。現在已到了非交卷不可的時候了,考慮再三,還是只能推薦兩種: 茅海建著《天朝的崩潰》,三聯書店出版 此書是近年來不可多得的在學術水準和學術規范兩方面都達到很高質量的專著,在學術、“政治”、“傳統”、現實之間,作者義無反顧地選擇了學術,一切結論都建立在充足的史料和嚴格的論證之上。 葛兆光著《七世紀前中國的知識、思想與信仰世界》(中國思想史第一卷,復旦大學出版社出版 作者試圖從新的角度寫出一部中國思想史,盡管沒有完全取得成功,但是學術界一種可貴的探索,也代表了一種方向。 如非學術類著作也是推薦對象,我還要推薦韋君宜著《思痛錄》 作者雖然沒有特別高深的思想,但以罕見的直率如實地記錄了自己的經歷,包括自己曾經為之奮斗或不得不做過的一切,無論是光榮還是恥辱,為歷史留下了真實。 至于文章,我反復重看了這兩年的全部雜志,但還是難以確定。下周三要去美國開會,還有不少事要準備,只能棄權,祈諒。 葛劍雄,元月9日 因為我是在《讀書》編輯部友人的催促下才發出的,并且已過了1999年底,所以不知是否包括在有效推薦中。如果按規定屬無效,那是我自己的責任。在批評這次評獎工作的同時,我應該檢查自己的疏忽。我在收到“會議紀要”和發出郵件時,的確沒有想到應該向執行委員會提出主辦單位工作人員不得參加評獎的意見,因為我以為這是通例,即使沒有寫進章程。事實證明我的判斷是錯誤的,如果我當時明確提出了,至少今天能更加問心無愧。 暫別爭論 自《南方周末》發表有關“長江《讀書》獎”的報道從而引發爭論至今,我在網上發表過兩篇文章(后由一些報紙轉載),此前還接受過《文匯報》記者一次電話采訪。我一直關注著爭論的進展,讀了中華讀書網上的全部文章和旌旗網上前一段時間的文章,我特別注意對我的批評意見,不斷反思,不斷學習。我認為,盡管意見不同,也出現了一些干擾,但大多數人的態度是真誠的,意見是中肯的,所以其意義已經超出了爭論本身。不過由于我從7月底開始接連在國內外參加幾個學術會議,不可能再跟上討論的進程,只能以這篇文章說一些還想說的話。 有人告訴我,北京一些朋友對我很有意見,說我作為《讀書》和三聯的朋友,作為這次評獎的推薦委員之一,不該公開卷入這場爭論,更不該發表對《讀書》和三聯不利的意見。黃平也批評我和雷頤的做法不對。對此,我反復思考過。的確,如果有些意見能在事先溝通,效果會更好,但朋友們應該理解,溝通的不足雙方都有責任,而且當一件事情已經成為公眾話題時,朋友之間的公開討論是不可避免的,因為朋友并不等于沒有不同意見,更不必為親者諱。 在第一篇文章《我的遺憾,我的希望》中,我已說明了我公開發表意見的過程:在接受《文匯報》電話采訪之后、該報道沒有發表之前已經將我的意見打電話告訴了《讀書》的朋友,并希望能獲得朋友們的理解。只是在《文匯報》上只登了我認為“很不妥當”這樣一句話而沒有具體原因時,我才感到有必要寫一篇完整地說明自己意見的文章。 我不否認,我的第一篇文章完全是以《南方周末》的報道為根據的。讀了黃平的文章,才知道還有另一種說法,特別是他表明沒有說過報道中的話。但是,如果沒有《讀書》方面的異議,誰會不相信這差不多整版的內容?這一版上既有這次評獎的前因后果,又有對《讀書》方面的訪談,更有幾位評委對獲獎作品的評論文章。連汪暉也說他是從《南方周末》上得知自己獲獎的,我將《南方周末》的報道和文章視為“長江《讀書》獎”正式授權的公告就更不足為奇了。何況此后一個月才見到工作室的聲明,以后才讀到黃平的文章,我們總不能隨便懷疑《南方周末》的信譽和這篇報道的真實性吧! 從評獎的結果產生,到我的第一篇文章發表,《讀書》和三聯方面本來是有很多辦法與我們溝通的,譬如在正式公布前先向推薦委員們發一個通知,或者在《南方周末》報道后向有關人士和朋友們作些說明,或者在得知我將發表文章或文章發表后直接作些交流。但直到工作室的聲明發表,以至今天,他們都沒有這樣做,那么只怪我不主動溝通就有失公允了。 朋友間有不同意見是否可以或應該公諸于眾,我以為要有區別,屬于私人間的或公開后會給對方帶來傷害的事不應公開,而有關公共事務方面的意見完全可以公開。像甘陽罵沈昌文的話以及《讀書》內部的人事糾紛不宜公開討論,而“長江《讀書》獎”的事完全可以公開發表意見。朋友之間公開發表不同意見不應視為友誼的脆弱,不必大驚小怪,更不要以為一定有什么背景或陰謀。這次討論中,我的研究所還有兩位同人發表了文章,其中曹樹基教授的意見就是針對我的,他引來批評的話就是我對葛兆光書的推薦評語。眾所周知,曹樹基是我長期的合作者.1998年發表在《歷史研究》的書評的共同作者,還是我的師弟和下屬,幾乎天天能見面,隨時能通電話。按照一些朋友的邏輯,他為什么不能直接給我提出,與我私下討論,非要公開寫文章呢?但我認為,這樣的批評絲毫不會影響我們的合作關系,而且這一問題是值得公開討論的。對另一位更年輕的同事寫的文章我也不完全贊成,至少對他的寫法有意見,但我也不以為忤,因為這不是私人間的事,應該尊重他發表意見的權利。 一些文章將這次的爭論定位為“自由主義”與“新左派”之爭,或者是以《讀書》與汪暉為一方,反對者為另一方的爭論。由于我的兩篇文章對“長江讀書獎”持批評態度,所以就將我劃為“自由主義”,或者直截了當將我與徐友漁、朱學勤、雷頤等劃為一邊,對此我完全不能同意。如果僅僅根據是否持批評態度來劃分的話,中華讀書網和其他傳媒上發表的文章中這一類大概是多數(僅就篇數而言),但如果仔細看就不難發現,各人的意見是不同的,批評的角度和程度也有異,更不用說他們在此事以外的立場。我的批評完全限于這次評獎的規則,而網上其他的文章或多或少涉及其他一些問題,對這些我并沒有發表過意見,也未必與他們相同。到目前為止,我從未介入兩派的爭論,沒有發表過這類文章,更不明白我應該屬于哪一派。如果我真屬于哪一派,是隱瞞不了的,因為大家可以根據我發表的言論作出判斷。但老實說,我的學識有限,并且主要是歷史和歷史地理方面的,對專業以外的知識雖不無興趣,卻只是發些議論,而不敢寫文章。我對思想和理論,特別是涉及外國的,一向視為畏途。倒不是謙虛或偷懶,只是沒有這樣的基礎——對朋友們視為經典的外國名著,我一本也沒有認真讀過。我對“自由主義”的觀點有不少共鳴,但認為被稱為“新左派”的意見也有一定的合理性,當然這全是憑直覺,并沒有作過什么理論研究。如果根據這次爭論中的意見就要將我劃入哪一派,未免太簡單、太絕對化了。 有人說我的文章“貌似公允”,言下之意,實際上是不公允的。首先,我認為大家都應該公允,文章的外貌公允沒有什么錯,難道非得寫得傾向性明確,一邊倒,殺氣騰騰才行?其次,要判斷一篇文章是否不公允,得拿出證據來,不能以莫須有的罪狀強加于人。例如有人說我的文章也是對汪暉“圍剿”的一部分,那么就請指出是哪一段或哪一句?除了對“鄭重聲明”中涉及汪暉的一段話表示疑問外,我從未對汪暉有任何批評,倒是希望他能早日脫離這場是非。至于有人說我的文章是挑撥汪暉與評委們的關系,那未免太低估了汪暉和評委們的判斷力,也太低估了讀者們的判斷力。有人責問我,別人“圍剿”汪暉和《讀書》時你為什么不說話?按照這位先生的邏輯,所有參與討論的人都欠了汪暉的帳,要參加討論必須先還掉欠帳才有發言權,或者只有從一開始就介入“圍剿”與反“圍剿”的人才有資格說話,那么天下人豈不是都只能隔岸觀火了嗎?老實說,要不是最近在文章中看到這些話,我還從來不知道有這樣的“圍剿”,也從來沒有讀過汪暉被“圍剿”的論著。將我的文章與這些扯在一起,至少是一種想當然的誤解,或者是非此即彼的偏見,我希望批評者也能聽聽我的意見。 還有的朋友對我后一篇文章不以為然:既然工作室已經發表了鄭重聲明,并且強調這是工作室唯一正式的聲明,為什么還不相信,還要講與這一聲明不同的說法?我想分析問題、作評價都不能離開具體情況。《鄭重聲明》雖然給公眾提供了一種正式的說法,卻沒有消除大家的疑問,主要的原因是《聲明》回避了一些爭議的焦點,也沒有解決存在的矛盾。例如,《南方周末》的報道給公眾的印象完全是讀書獎方面的正式授權,其中的主要內容卻與《聲明》的說法完全不同,也為黃平等人所斷然否定,那么到底是《南方周末》的責任,還是讀書獎方面自己的錯誤介紹,還是事實本來是如此?又如,《南方周末》引述《讀書》編輯部的說法稱汪暉是學術委員會召集人,而推薦委員收到的材料中的確是這樣寫上的,《聲明》予以否認,卻沒有說明原因,這就使局外人不知所從了。現在我相信汪暉在出國后的確沒有擔任本屆學術委員會的召集人,但當時的文件上這樣寫以及《讀書》方面對《南方周末》這樣說如何解釋呢?如果《聲明》能說明一下,譬如原來有過這樣的打算,后來因汪暉出國而沒有實行;或者汪暉根本就沒有與學術委員會發生過關系,只是經辦人員誤將他的名字寫了上去。要是《聲明》中這樣說了,那么至少像我這樣的人就不會再有疑問了,“腐敗”、“丑聞”之說也就不攻自破了。又如原來的規定是凡有作品進入評選的人不能擔任本年度的評委,但后來改為不得擔任“相應獎項”的評委。問題是這樣的改變沒有事先通知有關人員。如果《聲明》能作一解釋,說明一下什么時候、為什么作了改變,或者承認這樣的改變有不妥之處,那么如果再有人揪住不放,就顯得過份了。 不少人主張,在批評和反批評中應該尊重對方的人格,我完全贊成,并且在主觀上一直是這樣做的。如果我的兩篇文章中有任何對汪暉兄、黃平兄或《讀書》方面有任何不尊重之處,大家應該予以嚴厲批評。但我遺憾地看到,還是有人在使用不該用的手段和非理性的詞語。有人將一位“王靜”(我不知道是真名還是筆名,也不知道是男士還是女士,姑且使用“他”吧)批評我的文章發給我,記得是先發在旌旗網上的。不知什么原因,他在文章中將我的名字都寫成“葛見熊”,使我一下子想起了文革中將批斗對象的名字倒寫,打上叉,或者用諧音改寫為惡詞惡義的做法。我想這位王先生一定是義憤填膺,非如此不足以宣泄,或者一時找不出更合適的話來加強自己的立場,只能出此下策。他不會不知道我的名字怎樣寫,這兩個字也不是亂碼所致。我可以一笑了之,熊現在已成了珍稀的、受保護的動物,能見到熊并不是壞事,說明生態環境保護得不錯。不過我還是要奉勸這位先生,要學會尊重對方,也要珍惜自己的形象和歷史,不要在自己的文章中留下這樣的污點。 我在網上讀到過署名“余華”的文章,或許正是作家余華寫的。我以前雖然沒有讀過他的小說,對他的盛名還是尊重的。但這篇文章使我對他很失望,倒不是因為不同意他的觀點,而是他的寫法和用詞。例如,作為獲得過國際獎的作家,余華當然比一般人更了解國際慣例,可以在這方面對大家作些幫助。可惜他完全是盛氣凌人地教訓別人,卻不顧基本的邏輯和事實。他聲稱他得的那個獎就要幾位獲獎者當評委,但我不明白,這些得獎者是在自己當評委這一屆得的獎嗎?難道這個獎真有自己評自己的現象嗎?我相信,實際情況是有些評委在此前曾經獲得過這一獎項,而不是當屆評出的,這與我們主張的原則并而二致。一個最好的例子,是鞏俐當了柏林電影節的評委主席,所以她的作品在本屆只參展,不能入選。但鞏俐以前曾在柏林電影節獲獎,或許就是余華所說的那種情況。如果因為我寡聞陋見,不知道還有余華所說的那種國際慣例,就請他不吝賜教,特別是將事實說明白,讓我開開眼界。但有話好好說,千萬不要像在上一篇文章那樣,連國罵(“他媽的”)都用上,珍惜自己在公眾的形象。 我本來希望將對《讀書》的評價與這次評獎區分開來,一些朋友不以為然,寫文章指出兩者不可分,因為這次爭議是《讀書》評價之爭的延續,對此我不敢茍同。這次爭議不可能不涉及《讀書》本身,但與事件本身是沒有因果關系的。《讀書》向左也罷,向右也罷,進步也罷,退步也罷,不是必然會辦不好“長江《讀書》獎”。即使《讀書》真的成了“新左派”的基地(我不同意此說),只要有一套好規則而又嚴格執行,一樣可以將此事辦得無懈可擊。所以在討論時,還是可以將二者區別開來的。所謂區別,無非是想使問題不要復雜化。我原來還以為可以先易后難——對規則問題不至于有太多的爭議,可以先解決,而對《讀書》的評價見仁見智,不可能也沒有必要統一。 我對《讀書》有特殊的感情,獲得先師譚其驤首肯的評《中國歷史地圖集》的書評發表于《讀書》,悼念先師的文章發表于《讀書》,我的第一本非學術性文集就是以發表于《讀書》的文章為主輯成,沒有《讀書》就不會有這本書。我從來不認為《讀書》是一種學術性刊物,而是一種可讀性、普及性、思想性、學術性兼顧的綜合性刊物,在我接連發表文章時也是如此。所以從《讀書》主編更迭之初,到去年4月17日汪暉、黃平二位在北京重慶飯店請我吃飯這幾年間,無論是在與董秀玉女士有限的交談中,還是與汪暉、黃平等《讀書》的朋友暢敘時,我都曾坦率地表達過我的看法:希望《讀書》不要太學術化,注意兼收并蓄,外國的東西不要太多。我從未對《讀書》作過公開的批評,就是在朋友間私下交談時也沒有超出這樣的范圍。我與黃平兄相識多年,有過共同的學術活動,與汪暉兄則因《讀書》結緣,從他出任《讀書》主編而相識,是他以《讀書》主編身份宴請的第一位作者。在重慶飯店的飯桌上,我聽到他們與一些朋友有矛盾后,曾力勸雙方多作溝通,建議他們到上海來開座談會。這一年多我沒有給《讀書》寫稿,是由于我自己體會到我的文章已不符合《讀書》的要求,所以不愿強人所難。汪暉兄曾邀我寫地理方面的文章,但一直沒有找到合適的題目,辜負了他的一番好意。我認為,一個雜志有自己的個性,主編有自己的傾向,這是很正常的,作者應該尊重,讀者可以自由選擇。我反對從“左”或“右”來評價《讀書》,只是堅持我的三點看法。但即使《讀書》的朋友不以我的意見為然,即使《讀書》今后會變成一種我不大喜歡的雜志,我們還是應該對它充分尊重,你可以不看,也可以批評,但不能采用敵對的態度。 順便說一下,我也反對用“左”或“右”來劃分其他雜志,例如《天涯》。我要求《讀書》兼收并蓄,我對雜志也并無定見,而是具體看它所刊的文章。承蒙《天涯》好意,去年起向我贈閱。在編輯的力促下,我也寄去過長短兩篇文章,但未蒙采用。我以為,這是完全正常的,希望今后能再寫一篇合用的,以答謝《天涯》的厚愛。其中較長的一篇,后來發表于《萬象》和《東方文化》(并非一稿兩投,原因不贅),要說這兩家雜志的宗旨完全相同,卻也未必。要說我厚此薄彼,也是冤枉的。爭論中提到的《南方周末》也發表過我的文章,但我并不贊同這張報紙上發表的另一些文章的觀點,即使其中有我的朋友。 黃平說“長江《讀書》獎”工作室的工作人員都是年輕人,很辛苦,這些我完全理解。但我們不能因為對他們表示同情,就不作批評,何況應該負責任的人并不是這些年輕人!另一方面,既然我們提出意見的目的是為了使以后的“長江《讀書》獎”辦好,我想應該提出一些建議,供主辦者參考。 首先,還是應該明確一些基本的規則。從這次的教訓看,主辦者和有關人員,如顧問委員、推薦委員、評委在正式評選以前都應該對有關的規則認真討論。在上一篇文章中我已經反省了我沒有專門提出“主辦單位的人不得參加評選”這一規則,無論如何,這是我作為推薦委員所犯的一個錯誤,如果今后有機會就應該切實改正。 但一旦作了決定,就不能任意更改。無論是負責人還是工作人員,如果要對規則或有關的文件作修改,那怕只是次要問題或個別文字,都應該有一定的職權規定,有一定的手續,并承擔相應的責任。 應該聘請法律顧問,并對評獎的全過程作法律公證。萬一發生什么問題,或者涉及有關法律問題,應該由法律顧問出面追究或處理,而不必像這次那樣,從三聯的負責人、工作室到汪暉都出來聲明要追究。 推薦委員的推薦意見在評選過程中可以保密,但在結果產生之后應該公布。這是對公眾負責,也是對自己負責。通過這些材料,公眾可以對每位推薦委員的學術評估能力與學術道德作出判斷,也可以了解一種作品何以能獲獎,得到了多少人的推薦。由于最后要公開,推薦委員一定會更加慎重。在此基礎上,也可以考慮公布評委的投票記錄。 評選結果產生并正式公布后,應該有一段異議期,公開聽取公眾意見,然后再由評委或主辦者確認后正式生效。 首屆“長江《讀書》獎”即將頒發,我還是希望主辦者在此前能充分考慮大家的意見,采取必要的改進措施,盡可能彌補前階段的缺憾。具體的爭論總會結束,但新的爭論必定還會產生,或許這正是思想、學術和學者能永葆青春的原因。我更加希望,經過這次爭論,朋友依然是朋友,論敵繼續當論敵,既是朋友又是論敵也未嘗不可。如果做了朋友就不能當論敵,這樣的友誼就太脆弱了。 |
| 新浪首頁 > 財經縱橫 > 滾動新聞 > 葛劍雄 > 正文 |
|
| ||||
| 熱 點 專 題 | ||||
| ||||
| ||||||||||||
|
新浪網財經縱橫網友意見留言板 電話:010-82628888-5173 歡迎批評指正 新浪簡介 | About Sina | 廣告服務 | 聯系我們 | 招聘信息 | 網站律師 | SINA English | 會員注冊 | 產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4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