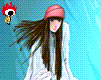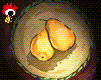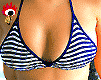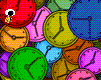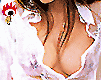| 熊德明們的城市化覓食戰爭 | |||||||||
|---|---|---|---|---|---|---|---|---|---|
| http://whmsebhyy.com 2004年05月11日 08:50 21世紀經濟報道 | |||||||||
|
中國社會保障體系下的“銀色”困境 農民地帶 本報記者 何忠平 成都報道
農民從農村進入城市,必須要有一個培訓的過程。許多農民工掙了錢后,又重新回到農村,因為他們沒有融入城市,在城市沒有歸屬感。 從1996年5月1日起至今年4月1日止,四川立太律師事務所主任周立太總共受理了4698件案子———其中涉及農民工維權的占90%以上。 今年2月,為了追討1.5萬元的律師費,這位聞名全國的“民工律師”將一位身有殘疾、生活困難的重慶籍民工告上了法庭,因為“當事人贏了官司卻拒絕支付律師代理費”。 7年多來,周立太共被拖欠500多萬元律師費。在他所打贏的上千件工傷賠償案件中,勝訴民工“拿了錢就跑掉的幾乎占了一半”。 為此,周立太感慨萬千,“中國農民工的培訓不僅僅是技能培訓,還有法律意識、誠信意識和道德意識的培訓,這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 熊德明們需要培訓 2003年在總理面前說了句大實話引起全國性為農民工討薪運動的重慶云陽縣農婦熊德明,現已是某集團公司的管理人員。進城打工1個月后,她坦承,“轉換角色很難,目前的工作有點不習慣。” 周立太一針見血地指出,“獲得年度經濟人物社會公益獎,又咋樣?從農村進入城市,必須要有一個培訓的過程。” “農民進城務工,并不僅僅是工作和吃飯的問題,要提高他們在城市生活的生存技能。”從事多年城市流動人口問題研究的四川省社科院社會學研究所郭虹所長指出。 四川省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所長郭丹也認為,“讓農民工融入城市生活非常重要。許多農民工掙了錢后,又重新回到農村,因為他們沒有融入城市,在城市沒有歸屬感。” 換句話說,農民工接受城市文化的洗禮和轉型也需要培訓。周立太就處理過農民工上午被招進企業,車間還沒熟悉,下午就發生工傷的案子,也有為了獲得企業內部的工傷賠償費而自殘的極端例子。 現實情況又是如何的呢?往往是企業對文化高的員工培訓,文化越高培訓越多;而一些文化低正需要培訓的,反而得不到培訓———“這是典型的馬太效應,就像銀行貸款貸給有錢人一樣,誰又會為農民工的未來作擔保呢?” “每個農民的培訓費用只有2元” 而地方政府對農民工培訓的資金投入,有時候令人瞠目結舌。 仁壽縣是四川乃至全國赫赫有名的“打工大縣”——全縣160萬人口,常年在外務工人數高達33.2萬人,占全縣人口的1/5,占農村青壯年勞動力的一半多。方加鎮又是該縣外出務工人數最多的鄉鎮之一,據記者了解,全鎮1.2萬名農業勞動力人口中就有8000人常年在外務工。 然而就是這么一個縣,去年政府培訓農民工的投入,“平均下來,每個農民的培訓費用只有2元錢。”縣教育局職業與成人教育股股長陳仲清肯定地告訴記者,“2003年,縣里撥給7萬元‘農村勞動力轉移費’后,就將免費培訓3.5萬農民的任務由勞動就業局轉交給了縣教育部門。” 顯然,這7萬元杯水車薪“還遠遠不夠”。陳仲清給記者算了一筆賬,光教師補助費、培訓材料費、證書工本費、教材編寫費等,按最低支出算,幾乎就要花光這7萬元。“加上安排工作會議、抽查工作等,用錢的地方還多著呢,比如培訓設施上的費用。” 如開辦一個烹飪班,起碼要有鍋碗瓢盆;開一個家電維修班,家用電器和各種維修工具應該要有,更別說電子、機械等培訓了。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表示,如果僅靠7萬元經費,根本沒法完成培訓任務,而且農民工來鄉鎮培訓,要自己掏路費、生活費,“可能很多人就不愿意參加”。 陳仲清也承認很難把農民工組織起來培訓,但他把原因歸咎于勞動準入制度沒有全面實施,“到底需要什么文憑或通過什么培訓獲得的證書才可務工,至今還沒有定論。” 雙流縣的投入似乎要大方一些。該縣副縣長楊東升宣稱:5年內每年將投入150萬使全縣32萬農村青壯年全部接受一次輪訓,掌握一至多門就業生存技巧。但據記者了解,該縣去年培訓了6.4萬名青壯年,但平均算下來,去年每個農民工的培訓費用也25元不到。 很多農民工難免擔心花了時間和金錢,還是找不到合適的工作,干脆就不參加。另外,金堂縣竹篙鎮農民周濤瓊告訴記者,有些培訓缺乏實用性和針對性,“1994年我剛出去務工時,縣里有關部門對我們進行培訓,內容竟是‘向左轉、向右轉’。” 2003年,仁壽外出務工人員創造勞務收入18個億,占全縣GDP的20%;整個四川省農村勞務輸出1370萬人,實現勞務收入達474億元。然而即便如此,現實依然殘酷。 據省農調隊對仁壽、渠縣等縣(市)部分鄉鎮的調查,渠縣51%的農村勞動力是小學以下文化,70%的未受過專業培訓;仁壽縣外出務工農民中85%是初中以下文化。 農民還是移民? 資金投入尷尬的背后,還有培訓什么的問題。 2003年9月,農業部、勞動保障部等六部委聯合頒發了《2003-2010年全國農民工培訓規劃》,并提出培訓任務之一就是“開展引導性培訓”。 何謂引導性培訓?主要是開展基本權益保護、法律知識、城市生活常識、尋找就業崗位等方面知識的培訓。郭虹認為這里暗含了一個信號,“職業技能培訓現在已完全市場化了,但對農民工的引導性培訓———非職業教育,長久以來被忽略,現在終于引起注意了。” 不可否認,目前對農民工的免費培訓很多都是政府行為,但這種培訓其實還沒有關注到真正需要培訓的廣泛的農民工群體,很多還只是局限在城市擴張之后被圈進城市里的城中村的失地農民。” “政府拿錢免費送他們培訓而他們不見得需要。”而那些真正想得到培訓的農民工,因為戶口不在城市,郭虹告訴記者,“就沒法享受到這種待遇。”這樣導致的結果,城市政府只管它所轄范圍內的“農民”,農民工也就是流動人口沒人去為他們考慮,包括農民工子弟的學校在城市里也處于“非國家空間”,出現了“不流動的流動人口,不是農民的農民工”現象。 然而政府也有自己的理由,比如農民工子弟學校,因為沒有哪個部門能夠準確地計算出有多少外來人員子女,“假如花很多錢辦一所學校,但不知道學校的生源能否長期有保障,這顯然政府對投資外來人口子女學校比較謹慎的一個原因。” 另一個原因是,農民工子弟學校收費低,假如教學質量好勢必引來外來人員中的親友子女入學,“這樣,城市就承擔了應該由其他地區承擔的九年義務教育責任。” 一座沒有移民的城市是沒有活力的城市。“對很多舉家遷入城市的流動人口而言,如有固定工作和收入,我認為他們就是移民。”但目前政府普遍表示“管不過來,沒法管”,因為他們認為這是農民工問題,而不是城市問題。郭虹告訴記者,目前她們正努力推動把問題聚焦在移民上。 根據流動人口居住分散、不易集中的特點,郭虹們嘗試對一所招收流動人口子女的非正規學校的學生家長們進行培訓,告訴這些在成都做生意或打工的流動人口“如何做家長”。同時,也幫助這個私立學校開展一些活動,比如討論進入城市后的感受、你有什么要給即將進城的兄弟姐妹的忠告、你遇到最大的困難是什么、后來怎么解決等。 為了這個項目,郭虹本來想在社區先推動———讓社區來接納流動人口,讓流動人口融合到當地居民之中。但社區負責人后來說了句很現實的話,“這個工作雖麻煩瑣碎,但有經費保障,完成應沒問題。關鍵是這個工作沒有納入年終目標考核,我們做了是算白做的啊。” 四川省社科聯的高圭滋表示,流出地對農民工不好培訓,流入地也不好辦,農民工分布太分散,找不到他們,“如果項目能與勞動部門合作,見縫插針,借用政府資源,效果可能會好些。” |
| 首頁 ● 新聞 ● 體育 ● 娛樂 ● 游戲 ● 郵箱 ● 搜索 ● 短信 ● 聊天 ● 點卡 ● 天氣 ● 答疑 ● 交友 ● 導航 |
| 新浪首頁 > 財經縱橫 > 滾動新聞 > 正文 |
|
| |||||||||||||||||||||||||||||||
|
新浪網財經縱橫網友意見留言板 電話:010-82628888-5173 歡迎批評指正 新浪簡介 | About Sina | 廣告服務 | 聯系我們 | 招聘信息 | 網站律師 | SINA English | 會員注冊 | 產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4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