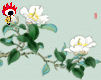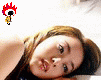| 商幫百年:悲劇不是他們的宿命 | |||||||||
|---|---|---|---|---|---|---|---|---|---|
| http://whmsebhyy.com 2004年05月08日 09:24 21世紀經濟報道 | |||||||||
|
本報記者 楊磊 廣州報道 過去的一段時間內,一個曾經隱諱的詞語“商幫”充斥著媒體和生活。這個詞語背后,馳騁著一群商業騎士,他們的血液里奔騰著商業的力量。而用它所連接起來的,是一個跨度超過150年的經濟轉型歷程。
這是一個地緣性商人群體。他們不怕苦、敢冒險、敢為天下先、求實而樂于探索,他們以其強烈的創業精神與杰出的經營能力抒寫了中國商業史上的百年輝煌,至今仍活躍在海內外。 他們一度呼風喚雨,左右行業經濟;他們曾經官商一體,操控國家財源;他們自創流派,成為中國商人精神的載體;他們亦經歷起起伏伏,但始終在延續商業經濟血脈。 他們的過去是如此顯赫,以至于沒有人敢于平視那個年代,甚至缺少為之作出定義的勇氣。 他們來自潮汕、寧波,來自山西、安徽。過往百年,他們就是國家商業的圖騰。 有人說這是一個人的成功,也有人說這是一群人的成功。更有人認為,這是一個階級的成功。 幾度輝煌 對于一個商業社會中人,即使相信時間可以滄海桑田——比如在暢銷書上記載的豪富場面深信不疑,但也很難相信沒有時間跨度的巨大變化。 正如對曾經被稱為“海內最富”的山西的追憶。當地人頂多就是淡淡地說,過去是這樣的。 在一個美國作家所寫的宋藹齡的傳記中,山西這個以貧瘠著稱的內陸省份的一個小鎮被稱為“中國的華爾街”。承載起這個偉大稱號的是以“晉商”為主體的商業團隊。 資料說,晉商俗稱“山西幫”,亦稱“西商”、“山賈”。在漫長的歷史中,晉商以山西富有的鹽、鐵、麥、棉、皮、毛、木材、旱煙等特產,進行長途販運,設號銷售,套換江南的絲、綢、茶、米,又轉銷西北、蒙、俄等地,其販運銷售活動遍及全國范圍,形成了能與南方徽幫相抗衡的最有經營實力的北方晉幫集團。 由此上溯到更遠的時候,在南方千里之外的安徽,另外一個著名人物胡雪巖已經開始在家鄉大興土木,建造一個現在都堪稱氣勢磅礴的大宅。 對于這個被稱為徽商龍頭的人——后世的記憶是“紅頂商人”——以商業影響力在官商之間左右逢源,最終成為“二品大吏”。 這不是一個人的傳奇。 徽商在南宋崛起之后,到明朝已經發展成為中國商界和晉商并舉的一支勁旅,到清朝中葉,徽商一躍成為中國十大商幫之首,所謂“兩淮八總商,邑人恒占其四”,尤其是在鹽茶業貿易方面,徽商獨執牛耳。康熙、乾隆年間,“鉆天洞地遍地徽”,“無徽不成鎮,無績不成街”。 晉商徽商之后,寧波商人開始沿海而上,在上海、南京等口岸城市扎根,成為繼二者之后“最具戰斗力”的地緣性商人群體。和其他商幫不同,寧波商幫更樂意經營與日常生活密切相關的營生,外向型地緣結構促使他們的經營方向由外至內——善于不斷接納、應用外來先進科學文化技術,發展壯大自己。 寧波商幫獨領風騷的態勢進入上個世紀后發生了改變。隨著口岸經濟的發展,潮汕商幫伴隨著近代海外移民高潮而發跡于海外。 這是一場明顯區別于其他商幫發展的商業經歷。潮汕商人的資源絕大多數來自海外,并主導海外商品在內地的流通,積累自己的財富之后將自己的生活形態放置于海外,并影響當地的商業形態。而這種模式一直貫穿至今。 在更晚的1970年代,潮汕商幫終于走上巔峰。一個名叫李嘉誠的商人在口岸城市香港開始建立自己的商業帝國,并且他終于看到了自己帝國的根基。 作為一個坐標,李氏家族在香港的升騰奠定了潮汕商幫在新經濟時代的影響力和高度。 商幫的邏輯 李嘉誠家族在香港崛起之時,另外一個寧波的家族——包玉剛走上世界船王的寶座。 作為寧波商幫的代表,包玉剛家族用了將近50年的時間來驗證了這個商幫的發展軌跡——利用靠近海洋的優勢進行原始積累,當財富達到一定程度后走向陸地,并將海陸資源整合,從而影響產業走向。 這種邏輯和潮汕商幫非常相似,似乎殊途同歸。 而在包氏從海洋走向陸地的過程中,潮汕商幫的領軍人物李嘉誠成為他的同盟。 在李嘉誠的協作下,包玉剛在數日之內動用數以十億計的現金,收購了老牌英資機構九龍倉的大部分股票,出任九龍倉董事會主席,從而成功著陸。而李氏在收購另一著名英資機構時亦獲得包氏的幫助。二者之間的合作被譽為“香港商業史上最經典的商戰案例之一”。 那是1970年代,商幫之間開始摒棄宗親和地域界限,走向合作道路。這個時期的觀點說,看似水火不容的兩大商幫在共同利益前提下最終走向聯手,這里面暗合著現代商業的必然。 學界的觀點認為,當協作共贏成為現代商業的基礎后,所謂的商幫界限已經不復存在。這實際上體現出一種“以義取利,經世致用”思想。 這種思想的發源地在沿海地區,包括浙江和潮汕——強調個性、個體、能力、功利、注重實際,已經成為當地的主導思想。 共同靠近大海,選擇外向型經濟的寧波和潮汕商幫的合作基礎正在于此。一位學者說,從根本上而言,潮汕和寧波商幫的發跡實際上是對外開放前提下“民本經濟”思路逐漸成為社會主流的必然產物。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商幫都存在這樣的認同。當以民生為基本要素的商業思維決定下的潮汕和寧波商幫開始走向新的階段時,地處傳統經濟腹地的晉商和徽商正在為歷史付出代價,因為他們的價值觀趨向于“官”“商”合一。 這似乎和他們的經濟轉型相關。眾所周知的是,當傳統產業已經不能滿足晉商和徽商的更大愿景后,他們選擇了金融產業作為突圍口。 他們幾近成功。一個數字說,清朝光緒年間,政府財政儲備將近1/3都存放在晉商、徽商的錢莊內。 這是一種近乎商業神話的格局。然而按照商業的邏輯看,神話背后的實質是復雜、脆弱而高風險的融資和同業拆解安排以及粗糙的產業鏈整合,它經不起政府對財政控制所采取的各種手段沖擊。雪崩的到來只是時間問題。 事實是雪崩很快就到來了。社會動蕩、革命將徽商和晉商可能的突圍方向全部打亂,并使之徹底無法翻身。 1914年冬天,山西票號的開山祖師——日升昌終于倒閉。從象征意義上說,這個事件意味著山西商人左右中國金融界近一個世紀的歷史就此終結。晉商和徽商長達百余年的商業哲學就此沉寂并受到質疑。 一位學者在央視論壇上分析說,“學而優則賈”與“賈而好儒”形成晉商與徽商不同的精神文化氣質。而徽商與其他商幫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儒”字。追逐財富只是徽商的手段,求功名做官才是歸宿。而從經濟學的角度看,只有實現商業與產業的結合才有可能使商業傳統延續下來。但“官本位”的徽商卻做不到,因為他們已經沒有財力去投資產業。 一門心思做生意的晉商卻走入了另外的一個極端。“晉商”雖然形成了商業資本和金融資本的兩大勁旅,但最終并未出現商業資本向產業資本轉化的趨勢。 從本質上講,徽商和晉商是傳統經濟的載體,而寧波和潮汕商幫則是現代經濟的萌芽——而這種萌芽暗示出主導此后商幫浮沉的決定性要素——專業分工的高度細化和集中化。 因而,當潮汕商幫和寧波商幫按照外向模式完成產業轉型,并自我進行產業調整和完善時,晉商和徽商卻因為文化傳承的原因沉寂下來。 可惜的是,胡雪巖們沒有辦法認識到這個現實。歷史記載說,胡氏興旺和衰敗皆因“官”字——據山西民間的說法,張嘴的龍代表官,閉嘴的龍代表商。當兩條龍都盤聚在同一座屋頂上時,對院落的主人而言,福禍就在兩可之間。 事實確證了這一點。 文化的力量 2002年,一個名叫謝世東的潮汕年輕人帶著“合生創展”走進京城。在他十分難懂的普通話強調下,很多人知道了這個名字拗口的公司將在天津開發一個占地18000畝的地產項目。 這實際上已經不是一個地產開發項目,而是營造城市。地產大亨王石用“后生可畏”形容了這個潮汕人的沖勁。 而這不過是潮汕商幫新人類突起的標志之一。此前稍早的2000年3月,李嘉誠次子李澤楷在香港開始了香港證券交易史上最大的一宗交易。依借家族的強大背景,李用不到三天時間動用了超過100億港幣(交易額估價為380億美元,)的現金將著名的香港電信收入囊中,并將之改名為“電訊盈科”,從此在潮汕商幫傳奇中刻下自己的名字。 行內人士笑稱:“李澤楷一天就賺了他老爹一輩子的錢。”然而,笑談過后,一場有關文化的反思正在進行。 馳騁社會數百年的商業騎士們,在一個遍地機遇的商業新時代為什么會境遇不同?有人將之歸結為精神內核的影響。比如宗親力量和地緣文化。 一個眾所周知的事實是,雖經數百年來時代變遷,潮汕和寧波商幫從沒有改變過宗親力量對經濟模式的干涉,其中或有消極的因素,但在某種程度上,“因為宗親存在的關系,他們變得更加團結”。 在潮汕和寧波商幫的發家路線圖上,是一連串海外親戚名單以及有如群星燦爛的宗親社團名錄;而在任何時候,以成敗論英雄的商幫內部,提起本地本族的大戶們都是帶著敬畏之情,他們的發家故事被認為是個人和社會的雙重必然。 如果對其發展作出一個詳細的歸納,甚至可以無窮無盡的找出這樣的案例,一個個體在某地的成功可以吸納一個家族的搬遷;一個個體的成功甚至可以導致一個家族、一個社區的轉型——這種思維在事實上延續著潮汕人和寧波人的商業血脈,并指向他們可以借鑒乃至依賴的發展方向。 至少在目前看來,這種力量是不能忽視的。多次聲稱不會對兒子的生意行為進行干涉的李嘉誠在李澤楷生意不利之時動用家族基金“救市”即是宗親力量的確證。 而在地緣特征上,靠近港口和海洋的地理優勢更是在潮汕和寧波商幫血液中烙下痕跡——當他們還是一個幼童時,他們就已經懂得物質需求比空泛的意識形態更緊迫。從骨子里講,外向型經濟主導下的商業團體只能是一個實用主義者,他們知道自己可以達到什么目標以及怎么達成這個目標,“他們更關心看得到的東西”。 沒人否認這樣的文化或許存在一定的缺點,但一個不爭的事實是,在一個經濟模式迅速轉型的華人社會中,潮汕商幫和寧波商幫的成功保持了“商幫”這個商業經濟圖騰的存在以及近一步提升。 而在傳統經濟腹地的商幫們,他們更渴望在官方層面的價值認同,而這種認同需要付出相當的代價,有些時候是一個團隊的犧牲,更加危險的是個體的倒下甚至有可能帶來整個產業邏輯和基礎的分崩離析。 或許正是這種區別導致了在潮汕商幫和寧波商幫開始偉大的復興之時,徽商和晉商內部卻還在進行著一場不休的討論——歷史對于現在,究竟還有什么借鑒意義。 這種討論并非沒有益處,至少它可以幫助曾經輝煌的晉商和徽商尋找出最適合自己的發展線路以及商幫文化。但現在他們要做的其實很簡單,那就是迅速尋找下一個突破口以取代目前自己正在失去的這個。 因為文化的力量,有些人正在失去傳統,有些人則從傳統中獲得力量。這是商業社會的必然,或許更是商幫的宿命。 |
| 首頁 ● 新聞 ● 體育 ● 娛樂 ● 游戲 ● 郵箱 ● 搜索 ● 短信 ● 聊天 ● 點卡 ● 天氣 ● 答疑 ● 交友 ● 導航 |

|
| 新浪首頁 > 財經縱橫 > 滾動新聞 > 21世紀經濟報道:風云商幫 > 正文 |
|
| ||||||
|
新浪網財經縱橫網友意見留言板 電話:010-82628888-5173 歡迎批評指正 新浪簡介 | About Sina | 廣告服務 | 聯系我們 | 招聘信息 | 網站律師 | SINA English | 會員注冊 | 產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4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