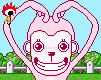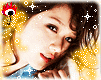| 一個普通農(nóng)民想對全國農(nóng)民說 | ||||||||||
|---|---|---|---|---|---|---|---|---|---|---|
| http://whmsebhyy.com 2004年04月14日 20:14 南方周末 | ||||||||||
|
-當(dāng)周圍的農(nóng)民專心種地和賣菜時,陳軍想的是:“中國由農(nóng)業(yè)化向工業(yè)化轉(zhuǎn)型的過程中,農(nóng)民怎么辦?” -在外在生活上,他和其他農(nóng)民沒有任何區(qū)別,一樣住著棚屋,一樣需要侍弄菜地和討價還價
-他開通電話為農(nóng)民解憂——“一個普通的農(nóng)民想對全國的農(nóng)民說,在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征途中,你們肯定會遇到困惑、煩惱、甚至失敗,煩憂熱線的主人在用他微薄的力量支持著你” -他從此給自己那間小屋起名“恨憂齋”,一個悲恨憂思的地方 □本報駐京記者 趙凌 農(nóng)民 當(dāng)陳軍拿著一張畫著長方形的紙對大家說,“我的理想是為中國農(nóng)民寫本書”時,幾個打工者在下面嗤嗤地笑。 對30歲的陳軍來說,當(dāng)著十幾個人說出自己的秘密,讓他感到有些不自在。他繼續(xù)說,“去年,我們的熊德明大姐在總理面前說了句實話,總理最后為她討回了工錢。我就在想,中國有多少農(nóng)民一生能見上總理一次?我寫書就是想替農(nóng)民發(fā)出自己的聲音。” 沒有人再笑了,有人反而帶頭鼓起掌來。 3月28日,星期天的早晨。在一個NGO的“農(nóng)友之家”里,陳軍說出了他的“野心”。農(nóng)友之家是一個“打工兄弟姐妹們的精神文化家園”,他們的創(chuàng)辦者也全部來自在京漂泊的打工者。 活動在北京北郊肖家河舉行。肖家河屬于北京,卻又像漂泊在北京之外。隨處可見的平房,磚與磚歪斜著隨便搭摞在一起。屋子大多顯得破舊,可門上的春聯(lián)猶在,透露著北京難覓的鄉(xiāng)土氣息。穿著大人的棉拖鞋,小臉臟臟的孩子在揚起塵土的小路上跌跌撞撞。 無數(shù)的農(nóng)民離開家鄉(xiāng)的土地來到這里承包土地,重新開墾。他們種地、賣菜,以此養(yǎng)家糊口。肖家河慢慢成了一個外來農(nóng)民的生活社區(qū)。陳軍的“家”就在這里,他的另一個家在河北張家口的張北縣。 太陽還沒有升起來的時候,陳軍和母親就已經(jīng)下地了。母子倆低頭在黑暗里摸索著摘出油菜和菠菜。再抬頭,已是上午11點,陽光恰好打在塑料大棚上,明晃晃地發(fā)亮。 從早晨五六點開始,陳軍必須留在大棚里,“總有干不完的活”。晚上8時,天完全黑下來。精疲力盡的母親賣菜推車回來,精疲力盡的兒子走出大棚迎上來。 陳軍的家是一間大約6平米的小屋。一鋪炕幾乎占去了它的一半。剩下的家具則一目了然:一個在北京撿的柜子、一臺從老家?guī)淼?4吋黑白電視,還有一個爐子。 30歲的陳軍和54歲的母親只能睡在一鋪炕上,從1997年母子倆相攜來到北京,一直都是這樣。這對背井離鄉(xiāng)的母子,因為共同經(jīng)歷苦難而顯得空前親密,他們保持著母親和兒子人性最初那種沒有隔閡與疏離的距離。 母親睡下后,一天中屬于陳軍最私人的時間才算真正到來。這個時候,他便拿出筆和紙來,一天中的寫作開始了。 星 我是一顆星,在沙漠上空,孤獨而寂寞。用太陽給予的能量,點綴天空 這是陳軍的一首短詩,他覺得自己就是那樣一顆星,微小卻總想照亮蒼穹。這也是陳軍的人生理想。 陳軍一直感覺作為農(nóng)民的自己,身體里潛藏著一種巨大的能量。他不知道這能量來自何處,或許真是“太陽給予的”。 那種無法控制的能量讓他總在思考,總想傾訴,然后寫下來。寫作是他的夢想。他從小就喜歡寫東西,尤其是初中遇到一位語文老師后。不幸的是,語文課只上了幾堂。家里困難,初中沒讀完,陳軍便在1992年輟學(xué)了。 從那時起,這個敏感的農(nóng)村青年便養(yǎng)成了想象的習(xí)慣,靠想象勵志,靠想象滿足自己。在想象中,他看到了自己全部的人生——歷經(jīng)苦難最終夢想成真。他把書名都想好了,就叫“風(fēng)雨同行——我這一生”。 很快,十幾歲的他就開始從自己的不幸里超越出來,考慮“這不幸的根源”。他發(fā)現(xiàn)自己的不幸是所有農(nóng)民的不幸,多少農(nóng)村孩子和他一樣因為家境貧苦無法再踏進(jìn)學(xué)堂,不得不重復(fù)祖輩的農(nóng)耕生活。 農(nóng)村的苦、農(nóng)民的苦就像一根巨大的刺扎在他心里。輟學(xué)后一個月,陳軍在幫家里種地之余,走訪了全村所有農(nóng)戶,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作品”——《丁家梁農(nóng)民現(xiàn)狀調(diào)查》。 這份長達(dá)萬字的調(diào)查報告呼吁政府應(yīng)多為農(nóng)民提供服務(wù),也呼吁農(nóng)民多學(xué)知識——自己拯救自己。當(dāng)年,18歲的陳軍直接把調(diào)查報告拿到了縣政府,希望對領(lǐng)導(dǎo)有所啟發(fā)。 1997年,陳軍和村里很多人一起離開張北來到北京,開始了真正意義上的流民生活。 “時至今日,農(nóng)民獲得的幫助還是那么少。農(nóng)民自己也還是沒有多少知識。村里養(yǎng)豬的那些人,到現(xiàn)在還以為只要多喂飼料就好了。” 12年前讓年輕的他揪心的問題,至他而立之年,依然如故。這讓陳軍時常感到痛苦,這痛苦隱藏在和所有來京農(nóng)民一樣種地、施肥、摘菜、賣菜的每一天里,沒有人知道。 陳軍常常把地丟下,跑出去“找答案”。在一次活動上,他激動地見到了“三農(nóng)”問題專家溫鐵軍。站在講臺上,溫鐵軍表白,“說實話,研究了十幾年的‘三農(nóng)’問題,我現(xiàn)在仍然困惑。”那一刻,陳軍體會到一種深深的震撼。 “農(nóng)民是中國國有資產(chǎn)最大的投資者,從1952年到1995年,中國60%的國有資產(chǎn)是在農(nóng)民身上獲得的。所以我說,中國的歷史是農(nóng)民創(chuàng)造的。”陳軍語氣嚴(yán)肅對記者說,他覺得農(nóng)民是中國最可愛的一群人,在那間陰暗的小屋里,看不清他的表情。 說起農(nóng)民問題,陳軍會完全拋棄羞澀,站在田邊的他像個詩人,揮舞的手上還沾著田間的新泥。那一刻,他不再是個起早摸黑的麥田農(nóng)民,不再是個漂泊北京的打工仔,而是“魯迅”、是“莎士比亞”,是一個讓聆聽者落淚的人。 “我們可以看到,全國累計拖欠農(nóng)民工工資達(dá)到1000多個億啊。當(dāng)然,這個數(shù)值與中國許多數(shù)值相比是微不足道,可它放到農(nóng)民身上,就至關(guān)重要。 “于是,就有了共和國總理為打豬草的農(nóng)民討債,就有了收容遣返制度的廢止,就有了溫鐵軍的困惑,更有了全國人民的呼號。” “恨憂齋”主 “我要用我的筆把農(nóng)民的故事記下來,把他們想說的話記下來。”如今,陳軍已經(jīng)搜集了一些素材,他稍有空閑就去和肖家河社區(qū)的農(nóng)民朋友聊天,聽他們講自己的故事。作為“農(nóng)友之家”的志愿者,陳軍每個周末都要參加那里的活動。在那里,他認(rèn)識了很多打工者朋友。 一次,初次相識的一位打工朋友向他抱怨被老板克扣工資的事,陳軍好言相慰。打工者臨走時隨口說,今天和你聊聊心情好多了。這句話深深觸動了陳軍,“對這些遠(yuǎn)離家鄉(xiāng)和親人的打工者來說,訴說本身就是一種安慰和發(fā)泄。” 去年11月,陳軍自己花錢裝了電話,印了幾十張宣傳單,騎著他那輛破舊的自行車,在肖家河社區(qū)逢人便塞。打工者拿到了這樣一份宣言:“一個普通的農(nóng)民想對全國的農(nóng)民說,在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征途中,你們肯定會遇到困惑、煩惱、甚至于失敗,請不要氣餒、不要回頭,010—62829859煩憂熱線的主人在用他微薄的力量支持著你。他不是圣人、不是偉人,只是一個普通農(nóng)民,作為你們中的一員,他愿和你們一起走出困境,走向成功。” 陳軍從此給自己的那間小屋起名“恨憂齋”,一個悲恨憂思的地方。一起種地的農(nóng)民感到不可思議,笑他,“你懂心理學(xué)嗎?盡給人瞎說”。陳軍回答,“只要聽著,別人就會舒服一點。” 陳軍自創(chuàng)的“心靈雞湯”常用的有兩種:想象法——“別難過,你現(xiàn)在經(jīng)歷的苦都是財富。想想看,若干年后的一天,你和妻子帶著你們的孩子走過這里,你可以無限感慨地說,在這里我度過了人生中最艱難的時光。”另一種是善意的謊言——“我理解你的心情,這樣的經(jīng)歷其實我也有過。” 煩憂熱線里很多農(nóng)民提出的問題陳軍也找不到答案,他所能做的就是鼓舞,鼓舞,再鼓舞。 “我常常覺得很矛盾。”陳軍說,電話多的時候他有一種被人需要的欣慰,但想到這是建立在別人的苦惱之上,這讓他感到“欣慰”得很不道德。“如果有一天,我的電話鈴聲不再響起,那也許才是我最欣慰的時候,說明我們打工者不再有煩憂了。” 喜鵲 陳軍腦子里總在想一個問題:“任何一個發(fā)達(dá)國家,它的農(nóng)業(yè)人口不會超過7%,我們農(nóng)民比率是他們的10倍以上,而在中國由農(nóng)業(yè)化向工業(yè)化轉(zhuǎn)型的發(fā)展過程中,我們中國農(nóng)民怎么辦?”但在外在生活上,陳軍和周圍的農(nóng)民沒有任何區(qū)別,一樣住著棚屋,一樣需要侍弄菜地和賣菜。這種分裂的生活讓他感到內(nèi)心孤獨。 陳軍在談笑里鼓勵別人忘卻煩惱,自己的痛苦卻幾乎將他推向冰谷——妹妹因為意外去年突然離世,母親和自己至今無法停止憂傷。 也許肩上越是沉重/信念越是巍峨/也許為一切苦難疾呼/對個人的不幸只好沉默 詩人的情懷,在陳軍身上常常閃爍。他有一種說不清楚的使命感,盡管身邊或者身后的農(nóng)民沒有任何一個人寄予他這種使命期待。 潛意識里,他似乎在要求自己更加堅強(qiáng)和博大,為自己所深愛的農(nóng)民們樹立一個精神的楷模。在給社區(qū)農(nóng)民的一篇文章中,他寫道: 干部有一個榜樣焦裕祿;工人有“鐵人”王進(jìn)喜;我們的子弟兵有家喻戶曉的雷鋒;就連公交系統(tǒng)也有一個李素麗。可占總?cè)丝诮?0%的農(nóng)民卻沒有一個榜樣。如果是這樣,我們就把我們自己樹為榜樣吧!榜樣意味著什么?意味著希望與力量,意味著可以鼓舞中國農(nóng)民走出困境,走向成功。 當(dāng)村里其他年齡相仿的男人蓋了房子,幾個孩子滿地追逐時,陳軍常常也會覺得凄涼。30歲的他至今單身。有人說,陳軍啊,你有給大家寫那些東西的時間,還不如去討個老婆。 “這一年多來我也常常問自己,奮斗這么多,思考這么多,到底是為了什么?我的理想是否太虛幻了?”母親也說“你能不能好好操心地里的事?” 陰暗逼仄的棚屋里,小學(xué)文化程度的陳軍窗臺上放著他的手稿和一部電話。挨著小屋,是他承包的地,一個寬闊的塑料大棚。“這些是我在北京的全部。”陳軍說。 他無數(shù)次看到睡在身邊的母親因想念故去的女兒而痛哭不止,卻不知該說些什么。悲傷里,他只能把自己比作一只喜鵲—— 如果讓我永遠(yuǎn)變成一只喜鵲,我會在樹上筑巢,白天出去找妹妹,晚上回到巢里眺望,我找不到,還有我的兒子、孫子,一定會找到的 那根從小就扎在心中的刺今天還在那里。對于農(nóng)民的苦,農(nóng)村的苦,苦苦尋找答案的他,覺得自己也好像是這樣一只喜鵲——飛啊,望啊,找啊。
|
| 首頁 ● 新聞 ● 體育 ● 娛樂 ● 游戲 ● 郵箱 ● 搜索 ● 短信 ● 聊天 ● 點卡 ● 天氣 ● 答疑 ● 交友 ● 導(dǎo)航 |
| 新浪首頁 > 財經(jīng)縱橫 > 滾動新聞 > 關(guān)注“三農(nóng)”問題 > 正文 |
|
| ||||||
|
|
新浪網(wǎng)財經(jīng)縱橫網(wǎng)友意見留言板 電話:010-82628888-5173 歡迎批評指正 新浪簡介 | About Sina | 廣告服務(wù) | 聯(lián)系我們 | 招聘信息 | 網(wǎng)站律師 | SINA English | 會員注冊 | 產(chǎn)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4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