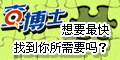|
文/本刊特約記者李利民
用漸進式改革來簡單概括中國的改革,不僅不確切,而且會產生誤導。中國的改革,有時候漸進有時候激進。
錢穎一是國際經濟學界中轉軌經濟學和比較制度經濟學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目前是
伯克利加州大學經濟系正教授。他的博士導師是三位知名人物:研究社會主義國家經濟體制的權威科爾奈教授、研究機制設計和博弈論方面的大師馬斯金教授、研究一般均衡理論的第一高手馬斯-克萊爾教授。
錢穎一的重要研究內容之一是中國的經濟轉軌,正是在錢穎一等人的努力下,中國的經濟改革和轉軌被越來越多的國際主流經濟學家所關注和研究。
日前,錢穎一接受了《經濟》雜志的獨家采訪。他就中國的經濟改革比較系統地闡述了最新的見解。
對中國經濟改革的總體評價
《經濟》:作為公認的當今西方經濟學界研究轉軌經濟學的代表人物之一,請您對中國20多年來漸進式改革作一個總體評述。
錢穎一:首先,我不同意用漸進式改革來簡單概括中國的改革,我覺得這個說法不僅不確切,而且會產生誤導。中國的改革,有時候漸進有時候激進。單用漸進式這一說法,會引出來一系列的問題,比如使人感到這只是時間快慢的差別,同時也使人忽略漸進或者激進方式的形成原因,以及改革中間的豐富內容。
我對于中國改革總的評價,與大多數沒有意識形態偏見的經濟學家是一致的:在過去的24年中,中國的經濟改革盡管存在著問題,也有失誤,但是綜合而論,它是非常成功的。這個成功的標志就是經濟發展了。雖然一直有說法,認為中國的GDP增長率被高估,因為物價增長被低估。但是也有理由認為增長率被低估,特別是在服務業和灰色經濟中。中國的增長作為一個事實是不可改變的。
關于“激進”與“漸進”改革,我想澄清一個誤區:轉軌和改革并不是一個“漸進辦法只能解決表面問題,激進辦法才能解決深層次問題”的過程,通常是反過來的。比如,改革的深層問題之一是建立法治,這能用激進的“全盤照抄”的方式來改革嗎?第一,這在幾乎所有國家,政治上根本不可能。第二,即使在特別例子中可能,比如東德照抄了西德,效果也很不理想。
中國在上個世紀90年代,僅就其立法速度而言,是全世界最快的國家之一。但法制建設中比立法更為重要的是執法,而改進執法在任何國家都是無法立竿見影的,除了東德和西德合并的時候西德可以把法官、警察派到東德以外,任何一個主權國家都不可以這么做。就算是把所有的法律都照抄別國,但執法過程就無法照抄了。法官、檢察官、警察、律師也是不能進口的。
人們有時說日本明治維新就是照抄西方,其實不盡然。日本人研究了許多西方國家,最后選擇德國為主要學習模式,然后根據日本的具體國情,決定什么拿來什么不拿來。即使是日本這樣極端的例子了,都不是像拷貝磁盤一樣地照抄。其他國家更不是這樣。
可能越深層次的東西變得越慢,越表面的東西——比如宏觀穩定,可以來得最快。為什么?淺層次的問題我們對它的理解比較清楚,一劑猛藥下去燒就退了,比如宏觀穩定,治理通貨膨脹,就是個淺層次的問題。對于采用激進的措施解決這種表面層次的問題,大家并沒有異議。而對于深層次的制度改革,往往需要更多的耐心,因為我們的知識有限。
中國特色的“財政聯邦制”
《經濟》:您的很多文章中多次提到了中國經濟改革的特點是具有中國特色的“財政聯邦制”,請您解釋一下這個概念。
錢穎一:“財政聯邦制”(fiscal federalism)是西方財政學里的一個標準用詞。實際上它的含義超出財政學。
中國在改革以前的計劃經濟管理體制跟前蘇聯比有一個重大不同,就是我們是“條條塊塊”中的“塊塊”的力量更強,而前蘇聯是“條條”的力量更強。我們地方政府的權力也好,辦事能力也好,都非常強,這是從1958年后就形成了的。這種行政性分權結構對以后改革的影響,有很多我們原來都不理解的功能,而這些功能甚至可以說對中國的改革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也許這是奠定中國改革路徑的一個基礎。
為什么這么講?我們需要跳出中國。你看東歐改革,看匈牙利,上個世紀60年代末就嘗試改革,各種辦法都試過了,都沒有實質性突破。為什么?一個原因是國有制企業不能突破,軟預算約束問題解決不了。在所有制問題上,只能有兩類,要不就是國有,要不就是私有,而私有在當時的歷史環境中有各種政治障礙,國有企業改革受上面政策的影響太大。一旦上面的政治搖擺,改革馬上就倒退,這是一種非常死板的狀況。
匈牙利當時是前蘇聯的衛星國,改革要看前蘇聯的臉色。而前蘇聯自己也是這種集權模式。戈爾巴喬夫不是不想改革,他確實試了,但沒有成功。當然原因很多,其中一個原因是蘇聯僵化的集權體制使的他無從下手。而中國呢?改革的成功是中央和地方的互動造成的。沒有中央設立特區、放松意識形態的大方向和政策,地方政府不可能致力于地方經濟發展。另一方面,如果沒有廣東、福建先走一步,大膽探索,改革也不可能如此成功。
比如說1992年鄧小平南方視察。鄧小平十分英明,但他再英明,也要有地方可察啊!正是南方的幾塊市場經濟的“特區”,才使得1992年改革從低谷中重新啟動。我1991年從美國回到北京的時候,看到那里很低沉,心里特別難受。吳敬璉對我說,你去南方看看就不會悲觀了。我隨后去了江蘇、浙江、廣東,看到的是完全另一番景象。如果沒有這么大的地域性分權,就不會有蓬勃發展的地方鄉鎮企業,那么中國在1989年后陷入東歐式的改革困境是非常可能的。所以從歷史的回顧來看,我們的分權為地方政府、為鄉鎮企業提供了一個活動空間,正是在這樣一個空間中,市場經濟在一些地區先長出來了。
這樣的情況是我們以前沒有預料到的,而且是任何一個只看教科書上對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描述的經濟學家所不可能想到的。根據這些新的觀察,我們把以前的財政聯邦制的概念擴大到整個的經濟中。傳統的財政聯邦制只講中央和地方之間的財政關系,但這只是一方面,中央和地方的關系還包括了其他經濟權力上的收放。在中國,地區間的競爭非常激烈,省和省之間的競爭,城市和城市之間的競爭,縣和縣之間的競爭,這構成了中國非常重要的一個特色。我們覺得這很自然,但到世界其他地方去看一看,就會發現不都是這樣的。
但是我們不能由此就得出中國的財政聯邦制就是西方式的聯邦制的結論,實際上它不是。有兩點重要不同。第一,中國在法律上不是聯邦制政體和財政體。第二,在中國的體制中,中央在人事任命上權力很大。因此不能把中國的分權的體制等同于西方的聯邦制,雖然有些機制相似。
市場的制度基礎是法制,而不是民主
《經濟》:通常民主與法制總是相提并論,但您特別強調市場與法制的關系,為什么?
錢穎一:我近年來對現代市場經濟的制度基礎這一問題做了比較多的思考,感到法制是最為根本性的。這不僅對發達經濟如此,對經濟轉軌中的中國,法制也指出了改革的方向。
在任何國家,政府都不可能和經濟活動徹底分開,不然的話就不需要政府了。在一個運行較好的現代市場經濟中,政府和經濟雖然有關系,但這種關系通常是一種“保持距離型”的關系(arms length relationship)。用通俗的話講,就是政府在經濟活動中主要起一個裁判者的作用而不是充當運動員。確定這種保持距離型的政府與經濟的關系的制度基礎不是別的,就是法制。這是人類社會至今能找到的最好的制度安排了。
講到市場的制度基礎時,我只講到法制但并沒有提到民主。民主與法制之間通常是正相關的,但并不是一回事。民主與法制在理論上可以分開,有沒有民主的法制國家,也有沒有法制的民主國家。是法制而不是民主對經濟有更基本和直接的影響。當然這不是說民主對經濟沒有影響,法制對經濟發展特別重要。產權保護、交易規則、合同執行、不腐敗的司法對經濟有更直接的影響。我提出好的市場經濟和壞的市場經濟的區別,是為了打消一個通常的誤區,就是以為所有的市場經濟都是好的。看一看全世界的國家,很多市場經濟都不行啊!
怎樣才是一個好的市場經濟?主要是經濟要在法制的基礎之上。法制是兩條。第一條,法制要約束政府,這是許多的政府官員不愛聽的,但是我要先說。政府在法制的約束下是一個有限政府,沒有這種約束就是無限政府、全能政府,這通常是導致壞的市場經濟的原因。第二條,法制要約束經濟人。如果認為自由市場就是不要政府,那就太天真了。市場要運作得好,是要有一套制度來約束經濟人的,要通過合同的形式、法律的形式,甚至監管的形式來約束經濟人。而執行這種約束靠的正是政府。
中國現在把法制建設從政治改革中分出來,是非常明智的。從廣義上講,法制建設當然是政治改革的一部分。
在討論在中國建立法制這一問題時,經常會聽到很多教條式的推理。回頭看看中國走過的路,可以發現不少現實對教條的否定。比如,在企業改革中,教條的觀點是不搞徹底的私有化,中國的經濟就沒有出路。事實是怎樣的呢?中間的可能性有很多,比如非國有非私有的可能性。十年前能大力提倡發展私有經濟嗎?五年前能提出建設有限政府嗎?所有這些都是在有禁區的條件下發生的,至今為止改革仍在向前走。用教條的思維方式,是不可能預測到,也不可能解釋中國的改革走到今天這一步。
金融穩定與改革
《經濟》:您認為中國在未來10年之內發生金融危機的概率有多大?
錢穎一:關于中國將來發生金融危機的概率問題,我有兩點說明。第一,只要加入到國際經濟和金融體系當中,不管你本來的經濟狀況是好是壞,都有可能發生金融危機。特別是比較小的國家和地區,哪怕經濟的基本面是很好的,就像香港,照樣可以出問題。這就是說,基本面有問題的會有金融危機,基本面沒有問題的國家或地區,如果市場是和國際連通的話,也會有金融危機。
第二點,具體到中國,發生金融危機的概率取決于國家的政策以及應付的方法。中國目前的金融體系非常脆弱,這是不能否認的。金融危機發生的概率取決于我們現在做什么和怎樣做。
《經濟》:對中國來說,在金融領域里哪塊發生危機的可能性更大?
錢穎一:雖然金融危機可以有多種,但從以往的經驗來看,真正的危機有兩個,一個是匯率危機,一個是銀行危機。中國當前的情況是仍然有資本管制,即使將來匯率有所浮動,這種浮動也是受限制的。因此,在兩個危機之中,更為可能的危機是銀行危機。
銀行和實體經濟的連接比較直接。銀行有結算功能,這直接影響到每天的大量的交易。銀行儲戶任何時候都可以去銀行取錢,因此,即使是健康的、沒有壞賬的銀行,都具有潛在的擠兌風險,更不要說有壞帳的銀行。以美國為例。1929年美國股票市場大崩潰,并沒有直接引起美國的經濟危機。后來是1932、1933年銀行的危機影響美國的實體經濟,導致大蕭條。最近十幾年的實證研究也表明了大多數經濟危機是由銀行危機造成的。比如那些東亞國家,危機往往是從匯率危機開始,匯率危機導致貨幣貶值,貨幣貶值導致利率升高和銀行危機。當銀行有外債并且很脆弱時,貨幣貶值和利率升高使得銀行資不抵債。銀行一旦出了問題,馬上連鎖反應,實體經濟就出問題。基本上是這么一個順序。
當我們討論人民幣的匯率政策應該更加靈活,資本控制應該逐漸開放的時候,這里面的一個基本的權衡就是效率與風險之間的權衡。金融系統,特別是銀行系統,不同于實體經濟。在實體經濟中,通常是競爭越多越好。銀行業也應該增加競爭,更加開放,但是在考慮這方面問題的時候,要把潛在的金融風險的可能性和成本考慮進去。
《經濟》:如何降低國有商業銀行的巨額不良貸款是銀行面臨的最大問題。1993年的時候您和劉遵義合寫過文章建議中國政府采取資產管理公司的方式解決不良資產問題。1999年財政部組建了四家資產管理公司。但目前國內對于資產管理公司能否解決不良資產問題一直有很多爭論,您現在怎么看這個問題?
錢穎一:我覺得重要的不在于它的形式而在于它的內容。我認為過去幾年的金融改革的進度不令人滿意。在1993年夏我和劉遵義寫過一篇關于銀行的不良資產問題并提出了解決問題的具體建議,可惜的是當時這一問題沒有表現得很急迫,當然也就談不上接受我們的或其他人的建議。一晃十年過去了,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現在的問題要嚴重得多了,到了如今非解決不可的時候了,因為有對WTO的承諾,要對外資開放銀行業。
用資產管理公司的方式來解決銀行的壞賬問題,世界上許多國家都做過,包括美國和東歐國家。美國在上個世紀80年代末就是這樣來解決它的儲貸銀行(S&L)的問題。中國目前的問題是:雖然資產管理公司成立了,雖然不良資產劃過去了或者債轉股了,但是銀行的治理結構沒有改變,企業的治理結構也沒有變。在這種情況下,錢就有可能白浪費了,新的壞賬繼續出現,還要再次剝離。這在其他國家已有教訓。比如匈牙利在上個世紀90年代,壞賬剝離一次以后不解決問題,又再次注資,就是因為沒有更新銀行的治理結構,沒有改變企業的治理結構。這些教訓早就擺在那里。
過去幾年,在亞洲金融危機的險惡環境下,中國保持了金融穩定,這是政府的功績。現在面對WTO,金融形勢面臨新的挑戰,而且時間緊迫。因為從2001年12月10日中國加入WTO開始算,兩年內要允許外資銀行從事企業的人民幣業務,五年內從事個人的人民幣業務,這是一個非常短的時間。金融風險概率有多大,這取決于這幾年的工作。做得好了,可以把風險降低,做得不好,風險是非常之大的,這就叫做金融風險的“內生性”。
首先,它取決于政府部門領導的認識、魄力和做法。我們經濟學家、金融學家經常叫喊金融危機,無非就是想提醒領導們注意這一問題。如果說亞洲金融危機給了我們什么啟示的話,一個很重要的啟示就是,金融危機可以爆發在宏觀基本面沒有問題的國家。以前拉美國家過度消費,導致雙赤字(財政赤字和外貿赤字),宏觀的基本面有問題,發生了金融危機。但是1997年亞洲國家不是這樣的,這些國家不是消費過度,而是另外的問題。這與我們的情況非常相近。中國的幸運在于這些亞洲國家的危機發生在我們的前面,因此我們可以用它們的教訓來引為借鑒。
《經濟》:那么您認為國有銀行的前景是什么樣呢?
錢穎一:這個很難說,因為它們都在改革之中。
我覺得中國的國有銀行有一種傾向,就是容易從技術上找原因,認為銀行業的問題是一個管理的問題。比較重視從技術上找新的指標來監督,比如說研究國外是怎么考核對銀行官員腐敗的監督,用幾個指標來監控,等等。
這些技術性的東西,可以比較快地借鑒,也不觸動高級管理層的利益。但是中國銀行業的改革不僅僅是一個管理問題,不僅僅是一個技術層面的問題,它一定要牽扯到國有商業銀行的制度結構。比如說,現在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行長都是副部級干部,看看他們的前任的職業道路就可知道,今后他們幾乎都要進政府當更高級別的官員。因此,這些銀行的高級管理人員不是銀行家,而是從事銀行工作的政府官員。并不是說政府官員一定辦不好銀行,而是說他們周圍的環境使得他們必須將注意力集中在政治上。政治因素在四大銀行的管理,比如人事安排上,起了非常大的作用。要從根本上解決國有銀行的問題,還是要從銀行的治理結構著手。(詳情請見《經濟》雜志2004年1月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