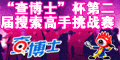|
黃宇
溫鐵軍1983年畢業分配到中央軍委總政治部研究室。1985年末調入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聯絡室從事農村調查研究工作。1987年全國農村改革試驗區辦公室正式組建后調入,1988年任監測處副處長,1993年任調研處處長,1995年任主持工作的副主任,1998年試驗區辦公室機構變動,調任農研中心科研處處長,現任中國經濟體制改革
研究會副秘書長。
主要研究課題與成果包括:國情與增長、農村產權問題、鄉鎮企業與小城鎮發展、農村政治體制與稅費改革、農業的穩定性等問題。曾經獲國務院農研中心、國家體改委、國家科委等中央五單位聯合頒發的“農村改革十周年優秀論文獎”、農業部農研中心優秀科研成果一等獎等多項獎勵,1998年獲國務院授予的“政府特殊津貼專家”證書。
毫無疑問,溫鐵軍得以進入公眾的視野是因為當選了2003年度的CCTV十大經濟人物,進入第三年轉而以企業家特別是民營企業家為主力的央視經濟人物評選,且不論它招致的關于格調和品位的質疑,也許在某種意義上轉向鮮活而有實力的經濟實體,是這歲末年終林林總總舉不勝舉的人物評選活動更為現實而可行的選擇,即便是CCTV也不能例外。
但無論如何,溫鐵軍的學者身份,尤其是一個“三農”問題研究學者的身份,他的入圍和當選總還是有些突兀而引人注目的。令人忍不住想要追問的是,在進入公眾的視野之前,他是如何得以進入CCTV的視野。
以學者的身份
把“中國研究‘三農’問題最權威專家”的帽子戴在溫鐵軍的頭上也許有點言過其實了,但要說“之一”便毫不夸張了。應該承認,在學術領域和溫鐵軍處于同樣高度的研究者總還是有的,但學術的水準和優劣高下難以準確地度量和比較,較之于學術的個性品格,學者的個性人格真實可感且容易突顯得多。溫鐵軍取勝的無疑是后者。
在很多場合溫鐵軍被形容和贊許成一個“用腳做學問”的學者,這容易讓人誤解是對“用腦做學問”的某種顛覆,甚至對碌碌于書齋殫精竭慮的學究們的某種嘲諷,事實上,溫鐵軍一直在努力試圖消除這種誤解,對于“做學問”一詞因人而異的界定,媒體、公眾、溫鐵軍本人以及像溫鐵軍一樣的經濟學者,都是難以評說或被評說的。
溫鐵軍更愿意把自己說成是一個農村問題的調研員或實驗者,在CCTV的頒獎典禮上他有過類似的表述,不過吳敬璉老先生周到而巧妙地化解了他的自謙。溫鐵軍的注重實際,既是研究領域決定,似乎也和他的專業不無關系。從1985年到1991年,溫鐵軍用了很長一段時間在學習統計和調研分析方面的東西,也許這段經歷讓他找到了一種做學問的好方法,他那時未必知道自己會因此而成為一個有代表性的聲音。
除此之外,想要探尋出溫鐵軍對農民及農村問題熱情的來源仍然是一件困難的事。說是他17歲起長達11年的插隊生涯培養起來的“親民”感情未免有些牽強,經驗和常識告訴我們的是更多人因此急于脫離和與農村劃清界限,或至多不過是小心翼翼懷舊般的緬懷。溫鐵軍讀新聞系,參加世界銀行和哥倫比亞大學的課題和培訓,學會的是用世界眼光看待中國的“三農”問題,這是他的獨特之處。
20多年田間地頭的行走,溫鐵軍對于中國農民的要義和處境有超乎尋常的理解。他的大聲疾呼“沒有農民,誰能活在天地間”給人的醍醐灌頂般的警醒,似乎9億農民的無語追問透過一個羸弱知識分子發自肺腑的吶喊,便有了穿越電子機械和光影數碼層層壁障的力量,喚起世人將視線重新投向其實一直張目可及的苦難,也令一度逡巡的決策者找到了果斷的落點。
吳敬璉說,“中國的農民不容易,9億中國農民就像是希臘神廟里的柱子,他們托起了大廈。”溫鐵軍說,“農民頭上‘三把刀’,上學、看病和告狀。”于是吳敬璉又說,“溫鐵軍是中國農民的代言人。”因為肯為農民說話,求告無門而找溫鐵軍解決問題的人之多可想而知,讓我們得出這一印象的是電視熒屏中那些揮舞的手臂,他們寫信,遞條子,或不遠千里去找溫鐵軍北京體改研究會的辦公室。
這些問題不知道溫鐵軍能解決多少,又解決了多少,這畢竟不是振臂一呼那么簡單,后者只需要勇氣和正義而已。溫鐵軍曾說起一段自己在川西某貧困村扶持一個農民養豬互助組織的經歷:一個好不容易建立起來且規模非常小的農民互助合作經濟組織,在它稍有起色時,當地各個部門的人員紛紛找上門來了,有要收費的,有要求辦證的,有要求取締的……幾個老實巴交的農民嚇壞了,他們只好寫信向溫鐵軍求助。
得知此情況后,溫鐵軍說,自己本可以給四川省的有關負責人寫信解決此問題,但他考慮到這種從上往下壓的辦法只能一時奏效。過后,各種麻煩可能還會降臨到那些農民身上。于是,他決定“委曲求全”,親自給當地縣、鄉、村三級組織的主要負責人寫信,解釋這個互助組織的作用、意義,并在信末特別強調:黨中央、國務院對此是支持的!此舉果然奏效,該互助組織至今仍安然無恙。這是溫鐵軍頗感得意的一筆。
做農民的代言人,這和學問無關,而和責任有關;中國農村的改革和建設,這也和學問無關,而與體制有關。溫鐵軍是清醒的,他說,中國的“三農”問題源自兩個主要矛盾,一是人地關系緊張的基本國情,一是城鄉二元結構的基本體制矛盾。這是溫鐵軍切切實實用腳做出來的學問,又是溫鐵軍用腳改變不了的現實。從這個意義上講,溫鐵軍在獲獎感言中說的,也許不僅僅是自謙而已。
以晏陽初的名義
不知道能不能把溫鐵軍的橫空出世看成“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另一種形式的登場。雖然恐怕此前很少有人知道這個偏居河北定州市翟城村一隅的、以著名平民教育家晏陽初的名字命名的鄉村建設學院,但事實上,溫鐵軍出任這所學院的院長,較之于他的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秘書長甚至“政府特殊津貼專家”等頭銜,對于其作為一個經濟人物人格魅力的彰顯,有“過之而無不及”的意義。
盡管晏陽初已經從很多人的記憶中淡出,盡管一度聞名世界的“定縣實驗”的十年一頁已被翻了過去,盡管翟城今天只是中國千萬個鄉鎮當中普通得讓人沒有理由知道或記住的當中的一個,但是,當一段歷史的脈絡被重新梳理出來,溫鐵軍和他的鄉村建設學院,儼然有了某種民族英雄般的光彩。
對關心中國農民及農村問題的人來說,這應該是難以忽略的一頁。1926年,以晏陽初為干事長的中國平民教育促進會選址定縣為實驗區,進行了為期十年的平民教育實驗工作,遺風猶存,口碑尚在。晏陽初針對中國“愚、窮、弱、私”四大問題提出的“四大教育”,即識字(文藝、文化)教育、生計(生產)教育、衛生教育和公民教育,及以此為基礎逐漸發展起來的鄉村建設運動,數十年來吸引了絡繹不絕的參觀者,其中不乏趙元任、俞平伯、張學良、斯諾等著名人士,定縣因此成為聞名世界的鄉村建設實驗區。
1977年后,溫鐵軍選擇在定縣實驗的舊址重開鄉村建設學院,繼承晏氏遺風的心愿不言而喻。溫鐵軍原本就是堅定的實驗主義者,他說,“不做實驗你怎么知道哪個觀點是對的?不做實驗你又怎么知道哪個觀點能夠符合中國國情?”溫鐵軍深信實驗的結果既是做學問的必須,也毫不懷疑實驗的過程對一鄉一地一人一戶的點滴改變。
因為這也許是溫鐵軍也料想不到的事實:今日的翟城村見過晏陽初的人也已寥寥,村支書米金水卻能執著支持著把鄉村建設學院復興起來。2003年2月,米金水征集了村民意見后,作出了一個重大決定,集資40萬元買下當年平教會農業實驗場舊址,豎起晏陽初的塑像,創辦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溫鐵軍決意并相信自己能夠主導這個鄉村建設學院的改革實驗方向。
在學院的招生簡章中,溫鐵軍說,“有機農業本來就是中國農民的傳統,不必追求高價的現代能源,別種‘衛生地’,少使用農藥化肥。在鄉村建設學院的培訓中心,雞鴨牛羊都養,還要種上蔬菜、果樹,要充分利用沼氣,形成生態循環,真正成為可持續發展的樣板。”
這是溫鐵軍一貫的觀點,他向來以為,對一個有9億農民的農業大國來說,城市化解決不了“三農”問題,加快城市化建設的后果,首先是生態環境會付出沉重的代價,而即使實現了55%以上的城市化率,屆時中國仍會有7億至8億人生活在農村。也就是說,中國的城市化率再高,也不會解決農民問題和農村問題。
現實的辦法是,幫助農民了解合作和互助的具體辦法,把農村過剩的勞動力組織起來,用于改變家庭和村社的面貌。通過勞動力的合作,把人力資源轉變為社會資本,溫鐵軍同樣將在鄉村建設學院進行農村社區的實驗。
看溫鐵軍為鄉村建設學院設置的課程:農民學、農村學與農村可持續發展理論;政治經濟學常識與農村(農業)合作社教程;可持續生計/生態、環境保護與生物多樣性;歷史及國外鄉村建設與另類經濟的理論及實踐;現代科學發展概要、文化藝術常識;參與式農村工作方法、傳播與溝通;社會心理學與城鄉二元結構條件下的社會心理現象,等等。這不是定縣實驗的簡單復制。
溫鐵軍的培養對象,是來自全國各地具有建設鄉村、改變鄉村面貌的理想,同時認同鄉建理念的城鄉居民、農民帶頭人(維權、致富、普法等)、鄉村醫生、農技人員、基層農村干部、志愿為鄉村社區服務的青年志愿者,這和晏陽初的治愚、治窮、治弱、治私,也不可同日而語。
1985年9月,旅居海外多年的晏陽初重回定州。耳聞目睹現實情景,老人感慨萬千地說,“中國農村建設的變化出人意料,比較起來,我當年搞的只不過是一種方法的研究。要真正改變廣大農村的面貌,還得有好的制度。”一所鄉村建設學院將晏陽初和溫鐵軍聯系在了一起,但他們最大的不同或許在于,溫鐵軍今天可以說真正為一種鄉村建設制度的開拓進行有益的探索。從這個角度而言,我們是否可以期待一場廣泛深遠的鄉村建設運動的興起?
《國際金融報》 (2004年01月09日 第九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