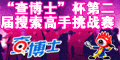|
朱健剛李磊
以社區(qū)的名義
1980年代中期以前,“社區(qū)”這個詞在中國還只是剛剛恢復(fù)的社會學(xué)和社會工作里的一個行話。但是,當(dāng)民政部門在1980年代中期把“社區(qū)”這個頗為“洋氣”的詞匯放進有關(guān)
政策文件的時候,他們或許并未想到,這個詞會在以后的十多年里成為政府高層的最重要決策之一,并從而家喻戶曉。而對于知識界而言,他們找到了新的烏托邦。
社區(qū)話語權(quán)力已是宏大,以至于人們但凡開展有關(guān)鄰里的工作都貼上一個社區(qū)的標(biāo)簽:
以社區(qū)的名義,街道辦事處的權(quán)力整合著條塊,大大小小的單位都被拉到社區(qū)的大旗底下;以社區(qū)為名義建立的形形色色的社會組織像雨后的蘑菇一樣生長,社區(qū)文化中心、社區(qū)服務(wù)中心、社區(qū)行政事務(wù)受理中心,還有例如勞動中介、社會保障、殘疾人等眾多的服務(wù)處所都點綴在居民區(qū)里;房地產(chǎn)企業(yè)也推波助瀾,在那些興建高尚住宅的工地上,隨處都能看到“智能社區(qū)”,“高尚社區(qū)”,“生態(tài)社區(qū)”等字樣。上海的弄堂深處,甚至修鞋的師傅也會用醒目的紅紙在鞋柜上貼上八個大字:社區(qū)服務(wù)、修理皮鞋。
宏觀看來,社區(qū)勃發(fā)力量源發(fā)自兩端:一端是作為改革發(fā)起者的政府,另一端則是在乎鄰里之間。兩股莫測力量的匯涌,就構(gòu)成了微妙卻浩蕩的進發(fā)。
改革者角度而言,這場運動初始的動機是通過動員的方式,自上而下地促進城市基層組織體制的改革,通過建立所謂“社區(qū)制”來替代原來單位制和街居制,加強對城市基層社會的控制。然而對于鄰里,社區(qū)建設(shè)運動是在并不清楚改革者具體目標(biāo)的前提下,依照以前慣習(xí)又結(jié)合著鄰里自身的需要而不斷進行的調(diào)整。
社區(qū)選舉
2003年,是應(yīng)當(dāng)被記住的一年。“如果說去年是社區(qū)黨建年的話,那么今年就可以說是選舉年。”
北京市崇文區(qū)前門街道鮮魚口社區(qū)、長沙市開福區(qū)四方坪街道辦事處四方社區(qū)、南京玄武區(qū)鎖金村街道鎖金四村社區(qū):紛紛在今年以海選的方式選出了社區(qū)的掌門人;而寧波市海曙區(qū)的59個居委會全部進行了直選。
年中在南京舉行的,由全國17個省市的近500名民政、區(qū)街干部和社區(qū)工作者參加的“全國社區(qū)居委會選舉培訓(xùn)班”上傳出消息,我國已有10多個省、自治區(qū)、直轄市開展社區(qū)居委會直選改革試點。而培訓(xùn)班主辦方之一的民政部官員(另一方為聯(lián)合國開發(fā)計劃署)表示,通過“促進中國城市社區(qū)地方治理”的合作項目,類似培訓(xùn)將會每年一次。
隨著選舉的活躍,越來越多年輕的面孔開始閃現(xiàn):7月22日,在位于天津經(jīng)濟技術(shù)開發(fā)區(qū)的華納社區(qū)進行首屆居委會的選舉中,主修社會工作專業(yè)的南開大學(xué)法政學(xué)院社會學(xué)系應(yīng)屆畢業(yè)生、22歲的錢堃經(jīng)過了3個多小時的選舉當(dāng)選為居委會主任;9月24日,在長沙,清華大學(xué)中文系應(yīng)屆畢業(yè)生陳香接過天心區(qū)白沙古井社區(qū)的聘書,25歲的她正式當(dāng)選為白沙古井社區(qū)的居委會副主任。在國際大都市上海,金發(fā)碧眼的杰森·波漢當(dāng)上了“小巷總理”。面對著圍追堵截的媒體,操著一口流利普通話的他發(fā)出預(yù)言:“我是第一個當(dāng)上居委會委員的‘老外’,可不會是最后一個。”
業(yè)主維權(quán)
當(dāng)然,不是所有的進步都會以平和的方式展現(xiàn),2003年,城市化戰(zhàn)略的進一步推進也引發(fā)了規(guī)模不小的業(yè)主運動。如若把前述選舉改革定義為由上而下的推動,那么毫無爭議地業(yè)主運動則為自下而上的沖擊。
2003年的社區(qū)沖突,墻內(nèi)墻外不絕于耳:從業(yè)主維權(quán)到保安毆打業(yè)主,從拆遷糾紛到業(yè)主與市政施工隊的矛盾。“有人頭痛,有人肉痛,有人心痛”,但痛定思痛,痛根何在?按照大海商務(wù)公司總裁王海的說法,痛在社區(qū)治理的現(xiàn)有模式存在著重大的缺陷。
以社區(qū)財產(chǎn)的登記方面為例:業(yè)主買的房屋,他的產(chǎn)權(quán)證只有自己家房屋面積的記載。對于停車場、綠地等配套設(shè)施,都沒有在房產(chǎn)證上進行記錄,這給物業(yè)公司或者開發(fā)商提供了便利。王同時以為,業(yè)主對自己的財產(chǎn)進行處分的活動是一個私權(quán)的范疇,除了公共衛(wèi)生和公共安全的領(lǐng)域內(nèi)的督察,政府不應(yīng)該過多參與乃至進行強制性規(guī)定。
據(jù)深圳的一項調(diào)查顯示,物業(yè)管理目前是比販毒回報都高的生意(投資回報大約是百分之一千到百分之一萬或者更多),“指望既得利益者的覺醒或自發(fā)改進,其天真程度好比指望讓葛朗臺請你吃滿漢全席”。
但歷史大勢,浩浩蕩蕩。隨著《物業(yè)管理條例》的頒布,業(yè)主委員會們接連橫空出世。他們有共同利益訴求所以團結(jié),他們不屬于街道管理所以獨立,他們中不乏中產(chǎn)階級、知識分子所以合作有效。
再接下來,業(yè)主委員會和居委會的關(guān)系問題也成了一種符號性的表征、一個碩大的問號。按中國人民大學(xué)副教授陳幽泓的觀點,社區(qū)的組織和治理模式正是處在變化和發(fā)展之中的。一切由轉(zhuǎn)軌而起,也將在轉(zhuǎn)軌中“解鈴”。
未來力量
中國城市的社區(qū)建設(shè)在理論和實踐中有兩種取向:一種是著眼于基層政權(quán)建設(shè),強調(diào)城市管理權(quán)力的下放和政府權(quán)力在社區(qū)的整合。第二種取向是著眼于社區(qū)共同體的形成,強調(diào)社區(qū)動員、居民參與和社區(qū)自治。
但分析1995年以來社區(qū)建設(shè)的主要資源構(gòu)成(以上海為例)可見,前者還是主流:在政策資源方面,時任上海市委書記的黃菊在1996年3月城區(qū)工作會議上做的《加強社區(qū)建設(shè)和管理,不斷提高城市現(xiàn)代化管理水平》的講話被很多人視作“最初的一擊”;在財政資源上,街道財政主要為財政撥款、財政返回、辦案補助費。此外,街道辦與任何一級政府組織(還有下屬的社區(qū))的不同:它可以自己辦經(jīng)濟實體,收入歸街道。
但也可見,未來的進發(fā)將只可能源于內(nèi)部力量的激發(fā)和體制上的再梳理,而不是外部力量的推動(已近最大限度)。即便世界范圍而言,市民社會的勃興也從來源于內(nèi)生的力量。
改革已開始在最細微處顯示活力。上海有過這樣一個案例:某弄堂狹窄而房屋比連,很容易發(fā)生火災(zāi),但居委會里卻沒有滅火器。原先居委會遇見此類事件都會猶豫再三再和街道辦事處談,生怕他們不高興。但是選舉出居民代表后,情況發(fā)生了變化——居民代表的單位隸屬關(guān)系不屬于街道管,很多比街道的級別高得多,在反映無果之后就把情況直接報告到直管區(qū)長那里,把街道辦事處也嚇了一跳。而滅火器問題也很快得到解決。
(朱健剛系上海綠根力量民間社會研究所研究員,本文部分內(nèi)容轉(zhuǎn)自朱健剛在香港中文大學(xué)就讀時的博士論文《國與家之間》。未經(jīng)允許,請勿轉(zhuǎn)載。李磊系本報記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