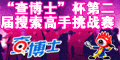|
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中國作為一個經(jīng)濟大國的地位已經(jīng)獲得舉世公認,但中國是否應(yīng)該成為一個文明大國的問題則似乎很少有人提起。具體地說,中國是否僅僅滿足于成為一個單純的經(jīng)濟大國,她是否還應(yīng)該有更高的自我期望,重新確立自己作為一個文明大國在世界歷史中的地位?
“天朝大國”到“民族國家”
對于這個問題,相信一些中國知識分子的本能反應(yīng)是斷然否定,因為“中國文明”之類的字眼,必然會喚起他們關(guān)于近代中國歷史的痛苦記憶。在他們看來,自晚清以降,中國花了一個多世紀的漫長時間才擺脫了“天朝大國”的幻象,完成了從“天下”到“民族國家”的艱難轉(zhuǎn)型,所以任何想要復興中國文明的努力都是開歷史倒車;今天中國人的唯一正確做法,不是要徒勞地復興一個古老的文明,而是應(yīng)該自覺地選擇“國際接軌”,擁抱一個全球化的現(xiàn)代文明。不過在他們心目中,這個現(xiàn)代文明的樣板卻是西方文明,因為他們認定只有西方文明才是世界歷史的真正目標,才是唯一代表全球化潮流的“普世文明”,而中國文明作為一種前現(xiàn)代的地域性文明,只能居于世界歷史的邊緣,或者說在歷史的進程中慢慢地消亡。
細究起來,這種與國際接軌之類的全球化論調(diào)并無任何新奇之處,說到底,它只不過是近世以來一些中國知識分子的一種集體無意識。晚清以降,在西方列強的侵略之下,中國知識分子逐漸喪失了對中國文明的自信。出于一種強烈的屈辱感和自卑感,他們無限地丑化中國文明,把它視為一切罪惡的淵藪,譬如認為幾千年的中國歷史都是“吃人的歷史”,幾千年的儒家文化都是黑暗的封建專制。在他們看來,中國似乎根本沒有任何資格被稱為“文明”,因為中國既沒有自由、民主,也沒有科學、理性,更沒有“上帝”。中國知識分子一方面盡情地顛覆和解構(gòu)中國文明的神話,另一方面卻不遺余力地美化或神化西方,制造了一個又一個的西方文明神話。而所有神話中最大的神話則是認為,西方文明是唯一真正的普世文明,因為它兩千多年來都一直在追求自由、民主、科學、人性、真理或上帝。
五四以來,中國知識分子對中國文明和西方文明的總體理解,正是基于這種不知所謂的“雙重標準”。在它的支配下,中國知識分子真誠地相信,中國走向“文明”的唯一道路就是拋棄自己的文明傳統(tǒng),選擇“全盤西化”,并且根據(jù)西方文明的標準來啟蒙和教育民眾,改造國民的“劣根性”。
不過,一旦面對活生生的歷史和現(xiàn)實,中國知識分子就立刻陷入了智識和道德上的雙重困境:既然西方代表著人類的普世文明,既然它兩千多年來就一直追求自由、民主、人道和進步,那么在面對所有其他非西方的民族時,它又為什么表現(xiàn)得如此野蠻和毫無人性,犯下如此之多的滔天罪行?當西方在瘋狂地殖民、販賣黑奴、滅絕印第安人,可曾有過絲毫的“文明”?一百多年的中國歷史已經(jīng)證明,中國知識分子對西方的美化是多么一相情愿,因為假如西方文明真的如他們想象的那么美好,那么中國就根本不需要任何所謂的“救亡”或“啟蒙”。
復雜的“西方文明”
中國知識分子之所以陷入這種尷尬處境,恰恰是因為他們用一個人為制造的西方文明神話,取代了真實的西方文明。只不過他們沒有意識到,這個神話的真正制造者恰恰是西方自己。換句話說,中國知識分子所想象的西方文明其實不過是一種歷史的產(chǎn)物。幾個世紀以來,西方人不斷地炮制出各種神話和意識形態(tài),其中一個最大的神話就是:只有西方才代表著真正的文明,而所有非西方的一切都是野蠻。因此毫不奇怪的是,近代西方政治思想家在建構(gòu)民族國家觀念時,毫無例外地預(yù)設(shè)了“自然狀態(tài)”和“文明社會”的對立。在他們看來,“自然狀態(tài)”象征著野蠻、愚昧和無序,而“文明社會”當然意味著文明、理性和秩序。隨著歷史的發(fā)展,這個“自然狀態(tài)”的外延不斷地擴大,從十七世紀的美洲印第安民族,到十八世紀的非洲地區(qū),最后到十九世紀的印度和中國等東方文明。一言以蔽之,在西方眼里,所有的非西方文明都變成了野蠻的自然狀態(tài),只有西方本身才是真正的文明社會;既然野蠻狀態(tài)需要理性和文明來“立法”,那么文明對野蠻的統(tǒng)治就是“自然正當”,從而西方對非西方的統(tǒng)治和征服就是天經(jīng)地義。
西方文明的“強大”并非僅僅體現(xiàn)為它的“船堅炮利”,更是依靠這套極端富有欺騙性的神話;它不僅用武力摧毀了其他民族的肉體意志,更是通過這套神話摧毀了他們的精神意志。反過來,一個民族在肉體上被打敗還不可怕,最可怕的是他在精神上被徹底打敗,從而放棄了對自己文明的自信,并且把自己等同于被征服的奴隸,自覺地接受征服者灌輸給自己的奴隸道德。就此而言,一百多年來中國一些知識分子的集體無意識,恰恰就是這樣一種“奴隸道德”。他們打心眼里認為,幾千年的中國歷史只是一個愚昧、黑暗、落后和野蠻的歷史,而西方則從古希臘以來就一直是理性、光明、進步和文明的歷史。
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中國知識界爭先恐后地謳歌一個名叫顧準的自由主義“圣人”。原因不外乎是顧準認為,幾千年的儒家文化只是黑暗的封建專制,而西方在兩千多年前的希臘城邦時代就已經(jīng)有了自由民主傳統(tǒng)。顧準的這套說法當然不是自己的發(fā)現(xiàn),而是取自一位十九世紀的英國歷史學家。其實他根本不知道,歷史學從來就最受政治意識形態(tài)的影響。比如說在十八世紀,同樣是談?wù)撓ED城邦,英國主流的歷史學家卻把希臘城邦罵得一文不值,大批特批后者是專制和野蠻的奴隸制。這當然是為了批判荷蘭和西班牙等國的殖民擴張,并且反過來襯托英國自由和民主的偉大。十九世紀,英國也走上了帝國擴張的道路,需要為自己的擴張尋找合法性,于是乎就要證明它的自由和民主繼承了西方文明的真正傳統(tǒng),同時也是要證明它對東方的征服、殖民和販賣鴉片完全是天經(jīng)地義,因為包括中國在內(nèi)的所有東方民族都是愚昧、落后和專制。在這種情況下,歷史學家當然就不愿意承認希臘城邦是野蠻和專制,而要反過來論證它是英國自由民主傳統(tǒng)的最早源頭。
英國當然不是特例。實際上,幾乎所有的近代西方國家都堅持這種根深蒂固的“自我中心主義”。譬如說,遠在德國完成政治統(tǒng)一之前,黑格爾就建構(gòu)出了一套世界歷史的神話,這個歷史的開端是沒有任何精神內(nèi)容的中國,而歷史的終結(jié)或最后目標則是他本人所在的普魯士德國;美國的聯(lián)邦黨人在建國之初,就堅定地認為美國擔負了一種真正的“天命”。
古老中國文明的現(xiàn)代期望
必須指出的是,簡單地指責和批判所謂的“西方中心主義”,根本沒有任何意義。因為說到底,每個民族都是天生的“自我中心主義”。具體地說,每個民族都有自己關(guān)于善惡、好壞或?qū)﹀e的最高理想,并且依據(jù)這套理想,把自己的人民從野蠻的動物教育成“人”,獲得真正意義的“人性”。物以類聚,人以群分,這本是自然之道。倘若一個民族喪失了對自己文明的信心,那么它離自己的衰亡也就不遠了。歷史上的絕大多數(shù)文明之所以最終衰落直至滅亡,歸根到底是因為它們放棄了“自我中心主義”。中國人講夷夏之辨,希臘人和羅馬人則區(qū)分文明和野蠻。希臘圣賢柏拉圖明確地宣布,他所建立的“理想國”并不是一個四海皆兄弟的“宇宙城邦”,而是一個由希臘人組成的封閉政治共同體。基督教雖然否定文明和野蠻的區(qū)分,但卻承認上帝與魔鬼的對立。近代西方聲稱追求一個理性、自由和平等的普世文明,卻堅決把一切非西方民族排除在這個“普世”文明之外。在這個意義上講,每個文明都注定無法理解、也不可能接受其他文明的最高理想,而在任何文明之間都不存在一個所謂的普世價值,因為任何“普世價值”僅僅對這個文明本身才有普遍意義,一旦超出自己的自然界限,那么它就注定要成為一種尋求擴張和征服的堂皇借口。
因此,中國文明同西方文明的最大區(qū)別,并不在于是否堅持“自我中心主義”,而是在于是否能夠清醒地節(jié)制自己的普世沖動。每個文明都免不了某種程度的自我美化和“神化”,并且用這種神話或詩來教育人民的美德,培養(yǎng)他們對自己文明的認同、熱愛和自信。這一點,中國文明如此,西方文明也是如此。但中國文明的偉大之處,恰恰表現(xiàn)為她更懂得節(jié)制和中庸之道。具體地說,中國文明雖然自居天下的中心,但卻信奉“王者不治化外之民”。《論語》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禮記》云“有聞來學,未聞往教”,這都是表明,中國文明只求自足,不求向外擴張和征服。反過來看,西方文明自始至終都擺脫不了一種擴張性的普世情結(jié),不管是希臘、羅馬、基督教還是現(xiàn)代文明,都極力希望把自己的力量擴張到天地盡頭。
承認中國文明的正當性和優(yōu)越性,并非意味著應(yīng)該無條件地美化中國的歷史。每個文明既然有自己最高的理想層面,那么它就相應(yīng)地包含了自己的最低甚至丑惡層面。就這一點而言,中國文明并不例外。中國文明的幾千年歷史當然不是一個沒有絲毫缺陷和丑惡的人間天堂,相反在《春秋》、《史記》和《資治通鑒》等歷史典籍中,我們也看到了無數(shù)的戰(zhàn)爭、陰謀、血腥和災(zāi)難。所有這些,當然應(yīng)該值得警醒甚至批判。但是,一個中國人倘若真正地熱愛自己的文明,那么他自然應(yīng)該站在這個最高的理想層面,用最高的東西來包容最低的東西,而不是反過來用這些最低的東西來否定自身的最高理想。
有一種非常流行的看法認為,中國文明只知僵化地保守,不知積極地反省和批判。毫無疑問,這種看法完全是對中國文明和歷史的無知。事實上,中國文明恰恰是在無數(shù)次的自我反省甚至批判中,戰(zhàn)勝了一次又一次的危機和挑戰(zhàn),并且煥發(fā)出生生不息的活力,這在孔子的《春秋》、司馬遷的《史記》和司馬光的《資治通鑒》中,體現(xiàn)得再清楚不過了。但必須指出的是,任何對中國文明的批判都應(yīng)該基于中國文明自身的最高理想和標準,而不應(yīng)該用其他文明的最高理想來批判自己的丑惡。換句話說,中國文明的最低層面非但不能成為否定其最高理想的理由,反倒更加證明這種理想的必要性和正當性。
一百多年前,中國文明遭遇了一場“亙古未有之大裂變”。在這種處境下,中國知識分子對中國文明產(chǎn)生某種程度的懷疑甚至失望,原本屬于正常的反應(yīng)。但若據(jù)此否定中國文明的正當性,甚至否定一百多年來中國人民反抗西方的革命歷史,則是極端的荒唐和不知所謂。事實上,近代中國救亡圖存的勝利恰恰表明,中國文明在應(yīng)對任何外在危機時都能煥發(fā)出巨大的生命力。在新中國的建設(shè)中,在改革開放二十多年的偉大成就中,中國文明的生命力得到進一步的體現(xiàn)。因此,要肯定改革開放二十多年的偉大成就,必須首先肯定建立新中國的那場偉大革命,進而肯定近世以來中華民族救亡圖存的革命歷史,最終肯定幾千年中國文明傳統(tǒng)的正當性,而不是反過來大唱什么全球化或國際接軌之類的贊歌。這絕對不是什么狹隘的排外主義,而是一個古老文明對自身正大光明的期望。
(作者系北京大學哲學博士,現(xiàn)任教于北大哲學系。標題為編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