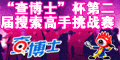|
by符郁
from北京
推開玻璃門是難以描述的混亂場景。到處都是人,不到兩百平方米的辦公室充斥著各種聲音,一不留神就會撞倒擱在椅子邊、墻邊的攝影儀器。“下午有20多家電視臺要在這里
采訪。”工作人員說。他們在現場不耐煩地走來走去,一面不停地通過別在衣襟上的耳邁講電話,就像是在對著空氣喃喃自語。
會議室臨時充當了化妝間,幾個裝扮艷麗的女孩倦怠地打著哈欠,等著造型師為她們弄好頭發(fā),有人跟我說這是一個新出的少女組合。年底是藝人宣傳的密集時段,今天他們對著不同電視臺的鏡頭不斷重復的一句“新年快樂”,也許很快就會借助于大眾傳媒的魔力直達中國最邊遠的城市。
這是中國華納唱片公司在2003年的最后幾天,過道里放著一塊通告板,每個小格里都用記號筆潦草地寫滿了藝人姓名和明年的日程安排,樸樹、老狼、金海心……2004年從1月到12月,連最后一格都已填滿。“這就是一個推廣的過程”
通告板上名字出現次數最多的樸樹今天沒有到場,他在去另一個城市的路上。華納為樸樹的新專輯《生如夏花》安排了一個聲勢浩大的百城行簽唱活動。
兩周賣了40萬張的《生如夏花》已經是一個不折不扣的銷售奇跡,而華納唱片的預計是一年內能超過100萬張。樸樹這種類型的歌手在華納并不是異數,至少汪峰與他有些相似之處,他們的音樂都有很強的個人化色彩,與大眾情歌式的流行樂多少有點格格不入,比較符合“小眾口味”,但唱片悄悄地賣得很好。
1996年,還是大學英語系一名學生的樸樹將自己的作品小樣四處投寄給唱片公司,其中一份小樣落到了剛剛回國創(chuàng)建“麥田音樂”的宋柯手里。盡管這幾首明顯稚嫩的校園民謠風格的歌后來并沒有收入樸樹的專輯,但它們讓宋柯認識了樸樹的音樂才華,麥田公司立刻簽下了樸樹。
兩年后,也就是1998年年底,樸樹發(fā)行了第一張專輯《我去2000年》。宋柯說:“作為主打歌的《白樺林》和《New Boy》其實樸樹自己都已經不喜歡了。”但是這兩首歌,特別是《白樺林》中庸討好的煽情路線為樸樹打開了廣大的歌迷市場。宋柯把主打《白樺林》稱為自己的一個小策略,“現在來看也成功了”,“你知道當年樸樹為什么能上春節(jié)晚會?趙安(當時的春節(jié)聯(lián)歡晚會總導演)非常喜歡這首歌。趙安跟我說,‘哪怕樸樹來了要穿牛仔褲上場,我也讓他唱。’
穿著運動衣、長發(fā)遮臉、一味躲著攝像機的樸樹上了2000年的春節(jié)晚會。有人玩笑般地總結道,雖然他只在春節(jié)晚會上出現了僅僅一分多鐘時間,“但晚會后樸樹的唱片訂單一下多了很多,穴單也多了不少。”
樸樹和葉蓓同時發(fā)售的專輯總共賣了超過60萬張,麥田在音樂制作上顯示了自己的獨特口味,那就是基本上以校園人群為自己的聽眾市場。
“當時麥田出的專輯不多,但是口碑和銷量都很好,引起了華納的注意,尤其是樸樹的成功,他的專輯出來之后,很多公司都跟我談過合作的事情。”2000年初,麥田音樂加盟華納唱片。
宋柯回憶道,很多人不理解他當時的舉動,覺得麥田這么好一個品牌,養(yǎng)活自己也夠了,但是他認為,作為國際五大唱片公司之一的華納,“應該是一個好的平臺,能夠讓我們的音樂更加主流。”他舉例說,像Nirvana這樣暢銷不衰的樂隊,一開始都是由獨立品牌做出來的,然后被賣給大公司,他們?yōu)槭裁磿蔀橹髁鳎斑@都是大公司的功勞”。
當今的超人氣天王周杰倫同樣經歷了從小公司到大公司的過程。也是1998年,臺灣脫口秀主持人吳宗憲在主持一檔選拔新人的電視節(jié)目時發(fā)現了周杰倫和方文山(他是周杰倫大部分歌曲的詞作者),第二年,吳宗憲的阿爾發(fā)唱片公司與周杰倫簽下了一份歌手合約。
2000年11月,周杰倫的第一張專輯發(fā)片,他那“聽不清在唱什么”的獨特唱法一下子風靡了華語地區(qū),“全臺灣都在R&B”,中國內地也開始漸成風氣。2002年,一手捧紅周杰倫的小公司阿爾發(fā)唱片把他拱手讓給了索尼唱片,第二年夏天發(fā)行的《葉惠美》專輯半個月銷量便直逼150萬張。
從小眾到大眾,從另類到主流,華納唱片總裁許曉峰說:“這就是一個推廣的過程。”音樂本身沒有改變,只是當它進入公眾視野,它就變成了主流。華納公司簽約的歌手大多是原創(chuàng)歌手,具有比較強的個人風格,“我們要做的就是把他們風格化的作品盡量按我們的推廣能力和推廣手段去把它變成大眾化的東西”。流行偶像:誰的消費品?
生活在富裕年代的年輕人從樸樹的音樂中聽到殘酷青春的種種表達,對成人世界的拒絕姿態(tài)中雜糅著對青春短暫易逝的哀傷留戀,它不像搖滾樂那樣吵鬧刺耳,也不像大眾情歌那樣淺俗甜膩。華納認為,這種“美好旋律與略帶叛逆的思想相結合”的音樂是比較符合自己主攻“城市有知識的青少年”市場的定位的。
樸樹在青少年中的影響力迅速被廣告商看中。2001年微軟的Windows產品升級,找樸樹唱了一首廣告歌,“微軟當時主打的方向是高速、自由,針對的群體也是知識層面比較高的大學生或白領階層,公司作了調查,樸樹在這個群體中的影響力非常高。”
至于今年四、五月份樸樹為豐田威馳演唱的廣告歌,華納表示不方便透露樸樹收取的廣告酬勞,但與豐田的合作并不只是提供一首廣告歌那么簡單,而是品牌的互動,“其實唱片業(yè)與很多產品是可以互相結合起來做一個市場的,這在國外已經是成熟的模式了”,通過與豐田的合作,“樸樹給華納帶來了兩三百萬的營業(yè)額”。
包括唱片銷售、商業(yè)演出、廣告等收入,樸樹明年的身價應當以千萬計。這個數字當然暫時還不能與周杰倫相比,周杰倫的身價目前大約為4億臺幣(約合9000多萬人民幣),而這中間的過程僅用了短短三年,他為之代言的包括百事可樂、松下、中國移 動等超級大公司的產品。
一些小公司在市場開發(fā)上顯示了更大的靈活性,他們發(fā)現國際化的大公司都十分關注青少年的喜好和流行。樂評人簡巍是北京較早接觸Hip-Hop文化且受影響很深的青少年群的人。當時北京、上海這些迷戀Hip-Hop文化的青少年已經形成了自己的地下網絡,比如誰跳街舞跳得好大家都知道,也經常舉辦自己的活動。通過朋友輾轉介紹,簡巍認識了其中一些人,2002年初,他把一群街舞跳得不錯的孩子叫到三里屯的88號酒吧,當場成立了一個街舞團隊,簡巍自己掏錢給他們聯(lián)系演出,這就是現在的北舞堂文化傳播公司的前身。
現在的“北舞堂”成為一個含意混沌的名稱,它的業(yè)務包括:為街舞團隊聯(lián)系演出和廣告——經紀公司,為大公司策劃青少年文化活動——公關公司,培養(yǎng)Hip-Hop歌手——唱片公司……今年許多國外媒體報道了這家小公司的多層次管理模式,他們感興趣的是,這家公司“是在做整體的青少年文化”。
簡巍的合伙人崔文斗說:“每個時代的青少年都有自己獨特的東西。我們現在做街舞并不代表永遠都是街舞,可能過幾年街舞不流行了,我們又會做別的。”
對于不斷將邊緣文化消費化的強大的商業(yè)力量,星空衛(wèi)視高級經理、樂評人郝舫有著清醒的評述:“真正衷心擁抱六十年代文化、擁抱反抗姿態(tài)的不是聽眾、不是搖滾樂手,而是公司。你現在能看到的反抗精神在什么地方最多?廣告。中國的廣告可能還沒有形成風氣,但你去看國外的雜志,那些在泥漿里打滾的、玩Hip-Hop的、跳街舞的,一定是廣告。六十年代的嬉皮、背包族本來是反文化的,現在也都被旅行社利用來做商業(yè)宣傳了。”“中國出一個世界級的Super Star,超不過20年”
2003年初周杰倫登上《時代》周刊的封面,他的個人榮耀在那一剎那達到了頂峰。大眾不再僅僅將他看作一個唱歌好聽的歌手,轉而視他為這個時代的文化符號。他的音樂,他的處世態(tài)度,他的穿著打扮,都成為在酷文化背景下成長起來的年輕一代的迷人注腳。
為什么內地還出不了周杰倫這樣的超級藝人?
宋柯在唱片業(yè)已經做了七年,他認為除了內地的音樂素養(yǎng)和宣傳平臺還無法與港臺相比之外,另一個重要的原因是與經濟水平有關。
“偶像氣質是與經濟實力有關系的,比如柬埔寨如果有個歌手唱得比邁克爾·杰克遜還好,他也永遠不可能成為大眾偶像。八十年代香港音樂的流行,首先是香港在經濟上說服了我們,香港的生活方式成為我們的向往。”
在與很多外國朋友聊天時,宋柯聽到他們也在預測,可能未來中國內地會出現一個真正世界級的Super Star(超級巨星)。宋柯對中國唱片業(yè)的未來抱有樂觀的態(tài)度,“體育方面我們已經有了姚明,流行音樂這方面現在確實還有距離,但隨著中國經濟的發(fā)展開放,國際化的加深,再加上奧運會、國家地位的提升,我覺得那個時間還真是不遠了。”
“可能10年,可能15年,但我覺得超不過20年,會有像邁克爾·杰克遜、麥當娜這樣超越種族和語言的障礙、單憑音樂吸引世界上各個角落的人的歌手。”
在真正的Super Star出現之前,流行文化還有一段很長的商業(yè)化的路要走,回顧一下這些開拓者的早期個人歷史是有趣的。宋柯和許曉峰,1983級的大學生,校園民謠的第一批逐浪兒;簡巍,樂評人,唱片公司企劃;崔文斗,讀大學時就與別人一起出過校園民謠的唱片,畢業(yè)后進入外企工作,兩年后辭職進入唱片公司做企劃。
他們仿佛是純真年代的最后遺民,但他們并不準備固守那個年代反商業(yè)化的陳舊信條,他們同時也是一個全新的商業(yè)時代的開拓者,但在他們內心深處,仍然保持著對才華的信念與尊敬。他們永遠贊賞年輕人對時代最前沿的東西的追求——因為只有這種文化存在,才有另類成為時尚、流行被消費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