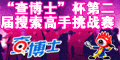|
-仲偉志/文
那些令人暈眩的崇山峻嶺
最大的力量就是使我們學會沉默。
而兩年來更多的這樣的旅行
使我逐漸變成一個悲觀主義者
在中國奇跡造就的新一代浪漫主義者的包圍中,
我的悲觀似乎不合時宜
2001年春天的風暴曾經使我們絕望。但風暴過后,我們很快淡忘了它,就像水分在到達植物的根部之前,迅速被高溫蒸發掉了。我們不愿承認我們的21世紀是在沙塵暴中開始的。我們中的很多人更是拒絕承認他們在這次災難中所起的作用。我們不愿去強調自然機能的相互依賴性,因為我們有著比環境限制更重要的經濟目標。
2001年10月,從貴州的鎮寧、關嶺、晴隆,再到四川大涼山的西昌、喜德和普格,我在中國西南少數民族地區穿行了半月,初衷是考察中國扶貧基金會在這些地方推行的人居工程以及小額信貸項目。為了讓他們學會用小額貸款經營生計,為了把那些在數千米高山上生活的彝族人搬遷到山下,慈善機構和地方政府費盡口舌與心機。晴隆縣的布依族縣長帶著我們翻山越嶺去回收貸款,縣長的誠實敬業和窮人的恪守信用,讓跟在后面的我們唏噓感嘆。
有關方面期待這些扶貧項目能夠改變這些少數民族人民的生活習俗和思想觀念。按照慣例我應該就此寫一篇報道,通過事實告訴大家,少數民族也可以做到吃苦耐勞,并不是像某些人所批評的那樣“自我滿足、自我封閉、因循守舊”,如果有足夠的機會和條件,他們也會像我們一樣創業和生活,參與商品市場的競爭。那幾個縣的縣長一直等著我的報道出來。但我一直沒有寫。因為我感覺到,這些結論只是來自我們固有的價值觀和方法論,是一種所謂的“客位文化量度”。因為在高山大川之中,我看到有更多的人堅持他們自己的生活方式,并且自以為是幸福的——如果他們認為目前樂天安貧的生活狀態是幸福的、合情合理的,那我們為什么還要去改變呢?
對自然的崇拜與敬重是大多數少數民族的文化傳統,這種可以稱得上是信仰的風俗,倒是具有生態意義的,符合可持續發展的精神。傣族人就居住在森林內外,但家家還要另辟薪炭林,不能砍一棵野生樹木。如果按照某些學者所呼吁的那樣建立綠色GDP,在計算國民生產總值的時候把生態環境成本計算在內,這些少數民族地區的社會發展水平并不低,而有些高速增長的所謂發達地區,說不定還是負數。
改變一種生存模式的成本極其高昂,從全人類的層面來說,還有可能是得不償失。因為你付出的不只是一些扶貧與開發資金,還會導致新一輪對資源的強烈渴求與攫取。我們希望用開發帶動消費,用消費帶動增長,因為增長就是我們所理解的社會進步。但是,在這些少數民族地區,以及在更廣大的西部,追求這種意義上的增長就意味著對自然資源的破壞和透支,舍此別無他路,這已經為諸多事實所證實。那么,誰能夠為如此進步的殘酷代價買單?
常常提著行李生活事實是一種自由,但2001年10月的旅行使我感到痛苦。那些令人暈眩的崇山峻嶺最大的力量就是使我們學會沉默。而兩年來更多的這樣的旅行使我逐漸變成一個悲觀主義者。在中國奇跡造就的新一代浪漫主義者的包圍中,我的悲觀似乎不合時宜。
但是我的確看到,許多關于環境保護與社會經濟能夠協調發展的美好假設正在一個個破滅。河西走廊的城市化如火如荼,自然成為必須出賣的資本。地下深井給新一帶農業產業經營者帶來了巨大利潤,公共福利高于私人利益的土地利用原則有可能被視為發展的阻力。紅色沙漠邊緣的土地正在散發著用國際貸款買來的化肥和殺蟲劑的氣味。龐大的礦業社會繼續榨取著脆弱的邊際土地,鋼鐵機械根本不知道對自然的使用應該從敬畏開始。
結果會是什么呢?我們誰也不愿看到,在不遠的將來,我們就可能像1930年代的美國一樣,成千上萬人辛辛苦苦埋設的輸油管道被挪用來向西部送水。但如果我們的擴張始終無視自然的限制,那么在不遠的將來,國家“購買”的就將是一個個巨大的荒漠。
我堅持認為,只有當我們重新確定社會發展模式的評估標準,不再用社會發展階段論來指責或埋怨少數民族的“落后”與“愚昧”,我們的可持續發展規劃才具有了操作的可能,西部大開發才有可能擺脫誤區和歧路。我們完全可以用另外的治理模式和組織結構使西部地區走向進步。
有人認為,將環境危害上升為“亞政治”有可能傷害發展中國家的利益,有可能影響后發國家的經濟增長和效率。而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說,無限期的經濟增長其實是可能的——就像其它商品一樣,如果任何資源逐漸變得稀缺,那么它的價格就會上升,它的消費量就會下降,這就意味著供大于求。他們甚至認為,全球變暖是一種并非由人類活動帶來的自然現象,自然所擁有的自我復制能力遠遠超過了人類對環境可能施加的任何影響。
夠了吧——我不是極端的環境主義者,我深深知道我們的國家必須沿著持續繁榮的道路開拓前行,我們的人民不能總是依靠調節自己的欲望來適應這個自然世界——但是,我仍然反對這種布爾喬亞式的盲目樂觀。
同樣是在2001年,大同成為一座被傳聞籠罩的城市——據說為了支持西部大開發,大同整座城市將搬遷到新疆,從而為城市地下的優質動力煤的開采讓路。這樣的傳聞使許多人的生活態度和生活方式發生了變化,在一座喪失了未來的城市里,人們縱情快樂,得過且過,不再做長遠的打算。在彌漫的疏離氣息與莫名興奮的人群中,賈樟柯很快拍完了《任逍遙》。這部沒有完整劇本的電影,講述了一群失業工人子弟的生活。在山西人賈樟柯的鏡頭中,大同是一座悲觀的城市。
那一年我和我的同事張夢穎在大同采訪。我們看到了更多在電影之外的大同無業青年。即便他們的頭發直立著,并染成了金黃色,也掩飾不住那種滲入到血液中的落寞與脆弱。他們無所適從。
賈樟柯似乎比我更加悲觀。他說,我覺得我們這個社會要鼓勵人們悲觀,它能讓人們慢慢理性。——或許對于有些人來說,最深刻的悲觀是真正力量的源泉,而樂觀主義者往往是那些愿意被人利用和操縱的人。但是,悲觀一定能夠帶來理性嗎?理性就一定擁有未來嗎?
(作者為《經濟觀察報》首席記者,擅長區域經濟報道和研究。)
|